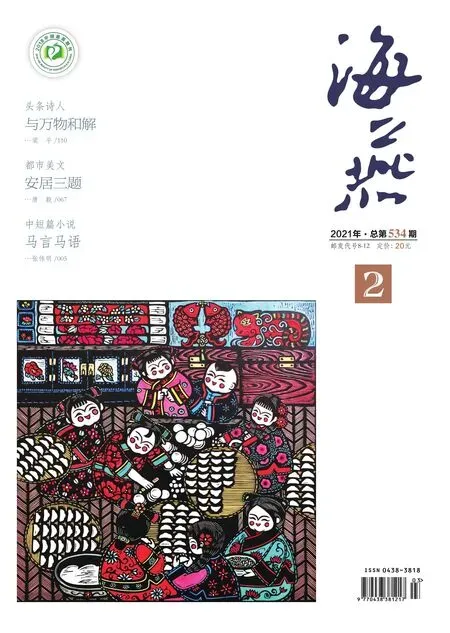草木記
文 吳 藝
一
自從十多年前搬來(lái)這個(gè)小區(qū),窗外的樸樹(shù)就成了我的鄰居。
我家在一樓。樸樹(shù)有兩層樓那么高,半遮半掩著我看外面的視線。我以前并不知道它叫樸樹(shù),每次從臥室或者陽(yáng)臺(tái)透過(guò)玻璃望它,感覺(jué)如同一個(gè)陌生人從眼前緩緩走過(guò),無(wú)愛(ài)無(wú)恨,與己無(wú)關(guān)。忽然有一天我慵懶著醒來(lái),初夏的朝陽(yáng)透過(guò)茂盛的枝葉照射到臥室,同時(shí)傳來(lái)的還有隱匿于樹(shù)枝間三兩聲?shū)B(niǎo)叫。這仿佛大自然的誦經(jīng)聲,讓我從惺忪的睡意中猛然清醒。為何以前我沒(méi)有關(guān)注它?其實(shí),窗外并排長(zhǎng)著三棵樸樹(shù)。原來(lái)它們和我同享著一片陽(yáng)光,相伴左右。它們的外形是那樣的普通,春夏樹(shù)葉逐漸茂盛,秋冬樹(shù)葉逐漸凋落,順應(yīng)時(shí)序,低調(diào)而有分寸地活著。我更喜歡它的名字:樸,樸素意,只有洗凈鉛華的回歸才能擔(dān)得起這名字。關(guān)于它們,我寫(xiě)過(guò)一首《四月五日》——
窗外那棵樸樹(shù)枝繁葉茂了
早起才落的雨淋濕了它
滿(mǎn)樹(shù)的葉子像一個(gè)開(kāi)始
那一整個(gè)冬天的稀疏
在霧霾天里和死去沒(méi)什么兩樣
沉湎于地下的先祖不會(huì)再有茂盛的那天
樸樹(shù)卻做到了
在今天或者明天
滿(mǎn)世界飄飛追思和懷念
它用生命的返青回到自己的世界里
難道不是嗎?樸樹(shù)的茂盛與凋謝與小區(qū)車(chē)嘩人囂是無(wú)關(guān)的,還有山茶、花葉青木、南天竺等綠植構(gòu)成了另一個(gè)世界,存在于日常的生活中,卻往往被忽視。在剛剛過(guò)去的秋天,我就特別迷戀在深夜聽(tīng)草木叢中的蟲(chóng)吟,此起彼伏,更能體驗(yàn)到深夜的寂靜與渺遠(yuǎn),就像來(lái)到一個(gè)久遠(yuǎn)的世界,只有一顆干凈的心才能發(fā)現(xiàn)和到達(dá)的世界。我想,在紛繁的人間,哪怕鮮衣怒馬一朝看盡長(zhǎng)安花,那又能怎樣?終是要無(wú)奈地面對(duì)衰亡。肉體是速朽的,而草木世界里存有永恒的可能,一片與世無(wú)爭(zhēng)的安寧與自由多么讓人向往。
這片草木世界的安寧,更需要一雙隨緣相遇的眼睛,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生活之外的。我從少年時(shí)就特別喜歡草木世界,常常隱身于山林樹(shù)叢中,久久不愿走出來(lái)。曾經(jīng)寫(xiě)過(guò)一篇《遙想》的文章就是記錄爬上故鄉(xiāng)赭山的經(jīng)歷和感受,“我的性格越來(lái)越孤僻,只有置身在山林樹(shù)叢中才覺(jué)得是安全和干凈的……”正如元好問(wèn)《山居雜詩(shī)六首》之一所言:“瘦竹藤斜掛,叢花草亂生。林高風(fēng)有態(tài),苔滑水無(wú)聲。”在荒僻與幽靜中,山野植物自由自在地生長(zhǎng),藤斜掛,草亂生,任性而灑脫。這不就是人生的一種隱喻嗎?對(duì)于有著無(wú)數(shù)煩惱與悲涼的俗世來(lái)說(shuō),草木世界就是清風(fēng)徐徐的精神后花園。
其實(shí),我們每個(gè)人都需要這樣的后花園,讓精神世界日漸充盈。猛然間想起法國(guó)作家安德烈·紀(jì)德說(shuō)的那句話(huà):“你永遠(yuǎn)也無(wú)法理解,為了使自己對(duì)生活發(fā)生興趣,我們?cè)?jīng)付出了多大努力。”紀(jì)德所“付出了多大努力”是解決“生存”與“精神”的問(wèn)題。這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人來(lái)說(shuō),二者的和諧并存似乎能順理成章。回望那不太久遠(yuǎn)的大明朝后期,在浮華與頹敗面前,依然要生活審美化、審美生活化。往日幻渺,那些努力在人類(lèi)漫長(zhǎng)的文明進(jìn)程中或逝去、或風(fēng)化,如流水無(wú)痕,似碑石漫漶,卻一直留存著一片草木營(yíng)造的凈土。
“乃若庭除檻畔,必以虬枝古桿,異種奇名,枝葉扶蘇,位置疏密。或水邊石際,橫偃斜坡;或望成林;或孤枝獨(dú)秀。”這是文震亨的趣味,卻全然是晚明文人們的趣味,他們是離不開(kāi)草木,在遍植草木的園林山水中去完成“出”的熱烈與“隱”的渴望;盡管“出”時(shí)也爾虞我詐,但“隱”時(shí)是干凈的,要不也就愧對(duì)以“詩(shī)、禮、樂(lè)”為準(zhǔn)則的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詩(shī)、禮、樂(l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不爭(zhēng)!但世間只有草木不爭(zhēng)。
二
走在通往山頂?shù)睦鹊郎希钋锏脑绯浚癯巧缴蠋缀鯖](méi)有人跡。木質(zhì)臺(tái)階的兩旁植滿(mǎn)了桂花樹(shù),金黃的花穗全開(kāi)了。腋生在樹(shù)枝間的花蕊仿佛一夜之間冒出來(lái),像是一場(chǎng)醞釀很久的表白。應(yīng)該是喝桂花酒的時(shí)節(jié)了,不是因?yàn)閻?ài)情,只是為了相逢后的喜悅。滿(mǎn)山都縈繞著濃郁的香,這個(gè)季節(jié),注定了桂花樹(shù)是主角。
整個(gè)邱城山并非很大,海拔也不足百米,但登上山頂是瞭望太湖的最佳位置。山南坡十幾畝茶園,環(huán)山有少許竹林和蒼松,山頂建造了一座亭子,叫“吳亭”。至于亭子的來(lái)歷與傳說(shuō)我沒(méi)多大興趣,旅游業(yè)的口號(hào)叫“無(wú)中生有”,眼前所見(jiàn)未必史籍所載,或者更無(wú)從考據(jù)。我喜歡的是滿(mǎn)山草木與空山鳥(niǎo)語(yǔ)組成的“寂靜”。人世間有太多的浮躁,人心有太多的空虛,多少人都是在誤讀人生。
時(shí)常漫步于環(huán)湖大堤,觀瀾聽(tīng)濤,太湖的浩淼闊達(dá)胸襟。臨水沉思,自然就想到屈原的草木世界,讀他的《離騷》雖滿(mǎn)紙憂(yōu)傷與悲憤,但寫(xiě)到草木時(shí),那是濃烈情感與繽紛想象的釋放:美人香草,百畝芝蘭,芰荷芙蓉,方澤衣裳,望舒飛廉……試想這樣一個(gè)滿(mǎn)腹情懷的男人,如果沒(méi)有朝堂的暗無(wú)天日,屈大夫肯定會(huì)繼續(xù)“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但他逃不出身份所帶來(lái)的階級(jí)賦予的責(zé)任和使命,投江也就成了宿命。至今依然潺潺東流的汨羅江水,雖然逝者如斯,但屈原的那般“芝蘭”高潔已經(jīng)融入了時(shí)間長(zhǎng)河,奔流不息……

插圖:李雪琳
我時(shí)常想,飲食男女雖無(wú)需“芝蘭”般的高潔,但要具備些草木精神與情結(jié),讓被俗世喧囂擾亂的內(nèi)心回歸安寧。曾經(jīng)一直想不明白,朱彝尊在撰寫(xiě)《食憲鴻秘》時(shí),通篇幾乎是舌尖上的事情,而末了卻用《黃楊》煞尾,猶如山窮水盡般的突兀。黃楊生長(zhǎng)在千米高山云霧籠罩的巖壁上,以巖縫中的滴水和雨露為養(yǎng)分,吸收了天地之精華而生長(zhǎng);雖生存環(huán)境險(xiǎn)惡,也能安守困境,冬不改柯,夏不易葉。李漁給它取名“知命樹(shù)”,猶如蓮為花中君子,而黃楊則是樹(shù)中君子。但這與“舌尖”有何關(guān)系呢?直到后來(lái)讀到他的詞《解佩令》——“十年磨劍,五陵結(jié)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那年他63歲,以事被褫奪,離京南歸;于是“出其生平才藻之緒余,用著斯篇,永為成憲”。這樣說(shuō)借“黃楊”抒發(fā)胸臆就不足為怪了,盡管隱晦于舌尖味蕾之中,卻依稀可辨草木精神的皈依。
這于我又何嘗不是呢?陽(yáng)臺(tái)上那盆假山十年之前在花鳥(niǎo)市場(chǎng)買(mǎi)回來(lái)的,瘦骨嶙峋,巉巖陡峭,“山坳”處長(zhǎng)著一叢虎耳草,一年四季從不凋謝;春夏之際還能開(kāi)出細(xì)碎的花,外形酷似鷂鷹棲歇在枝頭靜觀一切。每逢雙休日,只要不出門(mén),我就會(huì)搬來(lái)蝴蝶椅放在陽(yáng)臺(tái)上,懶洋洋地躺下,讀著自己喜歡的書(shū),累了就看看眼前的假山,還有“山坳”里的虎耳草;這是假山的靈魂。眼前這方濃縮的山林野趣,讓我感受著怡然自得的閑適,忽然明白精神世界的充盈不在于外,而在于內(nèi)心深處與草木相守的情懷。
三
躺在蝴蝶椅上,感覺(jué)它更像一個(gè)標(biāo)本,靜止在空間里,飛翔只是動(dòng)作,此時(shí)卻是一段傳奇,那樣的花香記不住但常想起。與書(shū)相伴的每日,都覺(jué)時(shí)間如同河流靜靜地流淌,大師們是高聳岸邊的參天古木,“無(wú)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zhǎng)江滾滾來(lái)……”大師已逝,但宏闊的思想依然奔流不息。
我很早就讀過(guò)《愛(ài)彌兒》,仍然記得盧梭呼吁一種親近鄉(xiāng)野自然的青少年教育:“城市是坑陷人類(lèi)的深淵……能夠更新人類(lèi)的,往往是鄉(xiāng)村。”鄉(xiāng)村有什么?那是草木自由生長(zhǎng)的沃野。而在喧囂無(wú)處不在的城市,利益的洪流裹挾欲望泥沙俱下。這也是盧梭經(jīng)歷生活種種爾虞我詐之后漸悟之感,“我離群索居比和他們?cè)谝黄鹕钜腋0俦丁!蹦沁€是個(gè)工業(yè)文明的蠻荒時(shí)代,至少?zèng)]有霧霾,至少還能在藍(lán)天白云下深呼吸。
而盧梭的腳步則不斷邁向毫無(wú)掩飾地向他敞開(kāi)的田疇鄉(xiāng)野,在看到草木凋零的凄涼景象時(shí),他開(kāi)始傷悼自己年華早逝:“精神仍然飾有幾朵小花,不過(guò)已因憂(yōu)傷而凋謝、因煩惱而枯萎了。”顯然,盧梭在自身的命運(yùn)與自然的興衰之間找到了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在草木之間詩(shī)意徜徉,孤獨(dú)沉思,這種生活的目的是“認(rèn)識(shí)自己”;正是在認(rèn)識(shí)自我的心路歷程中,盧梭不斷撥開(kāi)文明的塵埃,讓真誠(chéng)的靈魂直接面向真實(shí)的自然,從中找到了一種全新的內(nèi)在自由。
在《孤獨(dú)漫步者的遐想》里,盧梭用興奮的筆墨講述了他沉迷于草木的經(jīng)歷:盡管他年事已高、記憶力衰退,但還是具有“認(rèn)識(shí)世上所有的植物”的狂熱情感。他把這當(dāng)作一種自?shī)首詷?lè)的消遣,在其中獲得神秘且純真的美好體驗(yàn):“沉思者的心靈越敏感,就越能投入因自然的和諧而產(chǎn)生的心醉神迷的境界。……一切個(gè)別的事物他都視而不見(jiàn);任何事物,他只能從整體上去看、去感受。”在山林之間徘徊游蕩,把感官投向繽紛多彩的草木,是一種“眼睛的休憩,更是心靈的休憩”,因?yàn)椤按笞匀粡膩?lái)不騙人……” 這些又與中國(guó)的“老莊”截然不同,一個(gè)要隱遁山林逍遙游;一個(gè)要認(rèn)知山林,且充滿(mǎn)著熱情。
還有偉大的詩(shī)人歌德也一度癡情草木去研究植物學(xué),并迫切渴望自己的理論得到科學(xué)界的認(rèn)同,但半個(gè)多世紀(jì)過(guò)去了,人們都當(dāng)他是個(gè)詩(shī)人……這是為何?我的理解是,詩(shī)人的植物學(xué)在客觀的觀察中逃脫不掉審美的本性,乃是一種現(xiàn)代人朝向內(nèi)部的靈魂修習(xí)的方式,換句話(huà)說(shuō),詩(shī)中有草木,草木亦是詩(shī)。
思想家與詩(shī)人們的植物學(xué),我想真的是來(lái)自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草木情懷,并在不斷的敞開(kāi)當(dāng)中召喚那一望無(wú)際、草木深翠的莽原鄉(xiāng)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