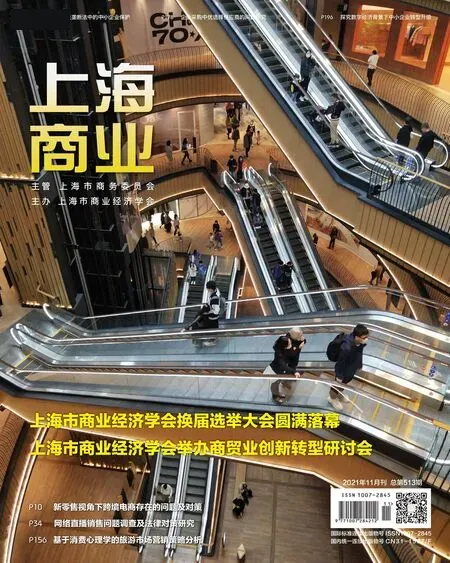網絡直播銷售問題調查及法律對策研究
張曉雪
一、網絡直播銷售的概念界定
1.直播銷售概念
當前,學界和行業對直播帶貨的概念界定眾說紛紜,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直播帶貨是一種新型服務方式,它通過互聯網平臺應用直播技術,從而進行商品的近距離展示、咨詢答復及導購。”還有一些學者把直播銷售等同于網紅帶貨,他們認為:“網紅帶貨本質上是一種以實時直播為媒介,由直播代言人通過聲情并茂地介紹商品外觀、結構、性能等進行推銷,能最大限度地克服一般網絡銷售中單一圖片畫面或文字模式缺陷的簡單銷售模式。”
筆者認為,就目前網絡直播銷售的現狀來看,當前的直播銷售與最初的形式和性質相比已經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不同于以往帶貨的主播僅局限于網紅或者明星,現在的主播來自各行各業,快手上的主播男女老少、年齡大小各不相同,其帶貨的范圍和種類也形態各異。另外,現在的直播平臺呈現出越來越多元化的趨勢,快手、抖音、小紅書、淘寶等均為直播銷售提供了很好的平臺,而且這些直播銷售在很多方面均有細微差異。就價格來說,各個直播平臺上主播銷售的商品價格并不完全相同;就管理方式來說,不同直播平臺的管理方式也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在體現直播銷售行業多元化發展的同時,也加大了對其進行法律規制的難度。因此,應該把直播銷售的概念擴大化,增加其包容性,把各種直播銷售的平臺、形式、主體均涵蓋其中,對直播銷售做一個宏觀的定義。
2.直播銷售模式
結合目前學界學者們的主流觀點和直播銷售的現實發展,本文將直播銷售的模式大致概括為以下三種。
第一種模式為“為他人代言”模式。網絡直播銷售的主播作為廣告代言人,代表品牌方推銷其商品或者服務。如近期Tiffany正式官宣了品牌全新T代言人為易烊千璽,如果品牌方邀請其代言人易烊千璽作為主播,介紹、展示產品,并進行銷售,即為此種直播銷售模式。
第二種模式為“自產自銷”模式。網絡主播銷售自制的或者他人生產的商品,此種模式中的網絡主播即為銷售者。此種模式在快手、抖音等直播平臺較為常見,如南方養蠶的蠶農通過網絡直播銷售自己利用桑蠶絲制成的蠶絲被;內蒙的牧民通過網絡直播銷售自家自制的醬牛肉等都是此種模式。
第三種模式的網絡直播銷售主播為第三方,為其他經營者介紹、推銷、銷售商品,并從銷售額中抽取一定比例作為傭金的模式。這是當前各大網絡直播平臺上最為常見的一種直播銷售的模式,在此種模式中,直播銷售主播即為促銷員。如薇婭和李佳琦等大主播,以及抖音、快手直播平臺上千千萬萬的小主播,大多通過這種模式來獲得傭金。
3.直播銷售與傳統電商銷售模式的區別
在產品或服務的介紹方式上,傳統電商銷售模式只能讓消費者通過圖片加文字的方式來了解商品或服務,其了解到的信息的真實性有待進一步考證。但是網絡直播銷售模式下,商家可以在直播間全方位地展示商品,銷售服裝的主播還可以親自試穿服裝,讓消費者看到穿上身的效果。與傳統模式相比,直播銷售模式更加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在表達上也更加直觀。從消費者的流量來看,傳統電商銷售模式的流量與靈活度遠不及直播銷售模式。并且各大直播銷售平臺還陸續開通了預約直播的功能,提前好幾天為直播活動宣傳造勢。由此可見,直播銷售相比于傳統電商銷售模式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也決定了直播銷售更加需要法律加以有效規制,以推動市場經濟有序發展。
二、我國網絡直播銷售發展的現狀
隨著電商網絡平臺的持續快速發展,以及互聯網的全面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應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使、互聯網娛樂消費觀念的形成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直播銷售這種電商新形式應運而生。起初,直播銷售專指網紅、明星等有一定名氣的主播,利用其流量和影響力來宣傳一些商品,其粉絲基于對主播的喜愛及信任購買商品的一種銷售模式。2020年以來,在疫情防控大背景影響下,許多實體行業不景氣,人流量的減少直接導致商品銷量的直線下降。許多實體門店紛紛關閉,店面轉租。直播銷售迅速發展成為較為主流的銷售模式,其銷售量非但沒有下降,反而大幅度上升。同時,其形式變得多種多樣,主播也不局限在原來的人員范圍內,呈現出“人人皆可當主播帶貨”的現狀。
關于我國網絡直播銷售的相關法律問題,部分學者已進行了一定的研究,這些研究對我國網絡直播銷售的法律規制有很大的推進作用。目前,在網絡直播銷售的法律規制上的研究相對較少,很多方面的規制還不夠完善。而直播銷售的成交數據顯示,疫情過后,其發展勢頭十分迅猛,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系列的法律問題。如:“我國對網絡直播平臺的管理基本上是由政府監管平臺實施,平臺監管用戶,政府一般不直接監管用戶。目前,在法律規制方面,對于網絡直播帶貨行為主要還是通過《電子商務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以及其他相關互聯網規定進行約束。由于規定分散未成體系,在實行監管行為時容易出現權力交叉或監管盲區。”因此,對于直播銷售的法律規制研究有很大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三、分析我國網絡直播銷售存在的問題
由于法律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直播銷售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暴露出許多問題。從本文的寫作目的出發,主要有以下幾個不容忽視、亟待解決的問題。
1.主體責任的判斷問題
目前,部分學者已經意識到從不同主體出發去探究直播銷售形成的法律問題的歸責問題。就監管機關而言,目前對網絡直播的監管部門十分混亂,存在多個權力機關均有權監管的局面。因此,在各個部門的監管機制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自然難以做到對直播銷售行業的有效監管,更談不上形成高效的監管合力。并且各個機關互相扯皮、互相推諉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另外,與網絡直播的暴利相比,網絡直播的違法犯罪處罰數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由于成本較低,導致打擊力度太小,讓直播銷售者存在極大的僥幸心理。
2.消費者維權問題
主要包括消費者取證售后維權困難等問題。目前,很多直播銷售平臺,如快手小店等,其售后和客服都不夠專業。就當前而言,直播銷售主體的違法成本相對較低,而消費者維權成本卻很高。這些現實問題導致一部分消費者維權意識較弱,而另一部分維權意識較強的消費者也缺乏便捷、高效的維權途徑和方式,最終導致消費者維權困難的局面。
3.法律適用問題
由于現在還沒有一部完備的有針對性的法律來規制網絡直播銷售問題,很多情況下,對于直播銷售行為引發的法律問題較難找到完全對應的法條加以評價。在不同部門法存在競合的情況下,該如何適用法律成了不可忽視的問題。
4.直播平臺相關問題
主要包括直播平臺對在其平臺直播的主播監管不到位等情形。以快手直播平臺為例,每天在快手上直播銷售的主播數量巨大,而快手官方的監管人員及監管設備有限,難免存在百密一疏、監管不力的情形。另外,如果平臺監管力度太大,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主播對產品的銷量,進而影響平臺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確保平臺掌握合理的監管力度也有一定的困難。
四、對我國網絡直播銷售的法律規制問題的對策
針對直播銷售呈現的問題,本文參考其他學者的觀點,并結合目前直播銷售發展現狀,以法學知識為理論支撐,提出以下對策建議,以供參考。
1.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強監管
直播銷售各方主體的行為是否觸犯法律的邊界,單獨依靠直播平臺監督其主播的言行,不足以有效避免違法現象的發生。必須有政府相關部門的介入,才能加大監管力度,使看不見的手在看得見的手的推動下穩步前進。
2.加強對直播人員的法律規制
對于網紅主播這一新興主體的責任與義務目前尚不明確,因此,對主播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嚴格規范:第一,熟悉并嚴格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嚴于律己;第二,拒絕不良商家的虛假宣傳邀請,提高個人素質,將品牌和信用看作遠重于利益的自身競爭力;第三,積極承擔法律義務,不逃避責任;第四,可以建立主播親自試用帶貨商品的監督機制,保證主播所帶品牌的商品是主播親身體驗過的,增加商品的安全系數。
3.完善直播銷售的相關立法
盡快明確法律界限,出臺相關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明確在法條競合情形下的法律適用問題。出臺針對性較強的法律,對于網絡直播銷售可能存在的法律問題加以專門規制。
4.增強電商平臺的責任意識,加強行業自律
這一層面可以說是最為治標治本的方法。從行業本身入手,是規制一個行業的最佳方式。
除了以上幾點對策和建議外,筆者認為,完善網購消費者的后悔權也可以納入考量范圍。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網購消費者有7天無理由退貨的權利,以及工商總局公布的《網絡交易管理辦法》對消費者的網購“后悔權”的相關規定,都體現了立法對保護網購消費者合法權益的重視。這與國外的“冷卻期制度”有異曲同工之處。我國可以取長補短,在直播銷售層面綜合形成更加完備的“后悔權”制度,從而使直播間的消費者權益得到更為有力的保護。
五、結語
縱觀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在現在及將來很長一段時期,直播銷售的法律規制問題將會成為法學界的一大重要課題。鑒于其在推動我國網絡直播銷售方面的立法進一步完善,協調各個部門之間的適用沖突,解決目前面臨的立法困境;降低消費者的維權成本,提高直播銷售各主體的違法成本,為消費者維權提供理論依據和法律保障,進一步提高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增加目前法學界對直播銷售問題的關注度,帶動更多學者對該選題進行深入研究,從而彌補直播銷售問題在理論研究層面的空缺等,我們有必要對直播銷售的法律規制問題投入更高的關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