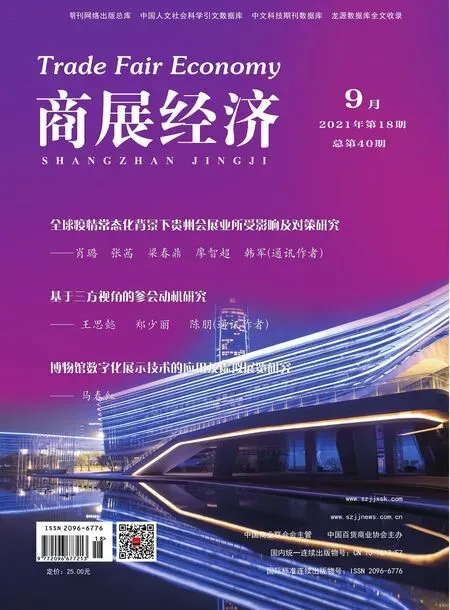消費升級背景下高品質休閑生活的構建研究
山東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柴龍國 毛雪婷
休閑是一個國家生產力水平高低的標志,是衡量社會文明的標尺,是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結晶,是人的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生命狀態,是與每個人的生存質量息息相關的領域[1],也是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好生活的基本含義中包含著勞動與休閑的二重性,強調新時代人民物質與精神生活的自主性、成就感和價值意義。美好生活的實踐路徑上,休閑生活的方式與品質緊密關聯并影響著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
1 消費升級背景下休閑生活的必要性
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其中人民美好生活是一個復雜概念,包含著人民物質生活的充足與精神世界的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自由自主的勞動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創造繁榮的物質文明。勞動之外,人(工人)的休閑更接近人的本質——自由活動的主體。作為一種社會時間的尺度,“自由時間”在馬克思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成為了“對富有的一種測量”[3]。
在消費升級的背景下,休閑生活是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休閑生活是勞動、工作以外的“促進身心愉悅和健康發展的現實生活”[4],社會生活,體現出當人自由支配時間時選擇的生活方式與審美品味。通過休閑,人們釋放勞動與工作中的疲勞,感受勞動帶來的社會進步,也正是通過休閑生活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獲得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其次,休閑生活影響著人民美好生活的主觀感受。美好生活是人民社會生活的整體,既包含了美好生活的結果,又不能缺少美好生活的構建過程,尤其不能忽視過程中人民對美好生活的主觀感受。休閑生活中蘊藏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切實體會,總書記闡釋美好生活時談到的“更好的教育、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5],無不與休閑生活密切相關。
高品質的休閑生活依賴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展示著中華文化源遠流長,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提升人民社會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審美品味,是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必要環節。
2 高品質休閑生活的社會基礎
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已經四十三年,這期間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總體上來說,中國已經實現了“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理想。
第一,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十三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十九大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描述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的需求在升級換代;從落后的社會生產到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了質的提升。
第二,國家經濟實力得到空前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1015986億元,突破百萬億大關,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0.2%,其中城鎮為29.2%,農村為32.7%[6]。這一數據已經接近聯合國20%~30%的富足標準。需要特別提出的是,2019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已經實現了八年連降,2020年出現反彈,是由特殊的情況決定的。這一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錯綜復雜,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沖擊,能夠取得上述經濟發展成績,突顯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厚底蘊。
第三,社會結構更加合理。2020年,近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十三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十億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
第四,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提高。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增長4.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1%。其中,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9037元,比上年下降8.6%,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2.6%。
居民收入水平、恩格爾系數和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三個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進入休閑社會的主要標志。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新時代的中國正昂首闊步邁進“普遍有閑的社會”,休閑日益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長期以來,國內對于休閑生活的認識帶有某種偏見,未能正確把握休閑對于人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價值。然而,只要我們承認生產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礎,那么,生產力的發展一定意味著人類閑暇時間的增加,這是經濟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已經充分證實這一經濟規律的真實性。通過改革開放和艱苦奮斗,我國社會生產力不斷提升,物質條件極大豐富,人民群眾的閑暇時光發生了革命性的增長,旺盛的休閑需要催生了規模龐大的休閑產業,既給人們帶來愉悅,又創造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3 構建高品質的休閑生活方式
但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休閑生活整體上處于較低的發展階段,休閑生活方式比較落后,甚至存在著不健康、不文明、不科學的休閑方式和內容。“惡閑”——指對社會、自然和自己產生不和諧的休閑生活方式——仍然較為普遍。以美食休閑為例,根據國新辦發布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數據顯示,中國居民超重肥胖問題不斷凸顯。18歲及以上居民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體重分別為69.6千克和59千克,與2015年發布結果相比分別增加3.4千克和1.7千克。城鄉各年齡組居民超重肥胖率繼續上升,18歲及以上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別為34.3%和16.4%[7]。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恐怕與百姓暴飲暴食,單純地追求生物本能欲望滿足有關,這不僅對居民身體健康造成了損害,而且浪費了大量糧食,對社會經濟運行也造成了巨大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強調高品質的休閑理念,構建高品質的休閑生活方式。
目前,對高品質休閑生活方式的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對于何為高品質休閑生活方式缺乏有效的理論概括,也未能形成理論共識。對于高品質休閑生活方式的內涵認識,可以從已有的休閑理論中尋找到有價值的思想支撐。在西方,亞里士多德是最早研究休閑的思想家,他把休閑視作“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亞里士多德認為,休閑與思考不可分割,休閑是建立友誼的方式,休閑與幸福緊密相連。這種觀點認為休閑是對意識、精神、個性的開發,其精髓是處于自由時間時的態度與性情,而時間本身不在考慮之列[8]。法國社會學家喬弗里·杜馬澤迪爾認為休閑需要具備三個要素,分別是放松、娛樂和個性發展。亞里士多德和杜馬澤迪爾都堅信休閑和個性提升緊密相連。總體上而言,高品質的休閑生活方式應該具備以下四個特征:
(1)豐富多元。休閑生活是人們對閑暇時光的消耗和消費,是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處于不同社會地位不同生活狀態的人們對休閑生活有著不同的理解和需要,因此高品質的休閑生活體系必須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從不同年齡階段看,要滿足老年、青年和少年兒童的休閑要求;從休閑類型看,要大力發展旅游、健身、美容、體育、藝術、時尚、閱讀、節慶等傳統休閑方式,更要注重發展電子競技、沉浸傳播、網絡社交等新型休閑方式;從勞動和休閑的關系看,新技術革命導致傳統勞動和休閑的概念已經模糊,兩者呈現出融合的趨勢。休閑在未來社會中將成為一種建制化的存在,延伸工作的領域和范疇,發展出“工作式休閑”或者“休閑式工作”,這類情況將進一步豐富休閑的概念,拓展休閑的邊界。
(2)綠色健康。人類的生命活動直接或間接地以自然為活動的對象。過去,由于對綠色發展理念認識不到位,人類在勞動實踐中破壞了自然環境,教訓慘痛。現在,提倡高品質的休閑生活方式,是強調人類的休閑生活不能給自然環境造成負擔,更不能破壞自然環境,這是綠色休閑的基本要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發展理念,是構建高品質生活方式的重要理論指引。休閑的目的是為了再生產勞動力,更是為了社會個體的自由全面發展,因此,休閑活動應該是健康可持續的。健康的休閑生活能為個體帶來愉悅,促進其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相對而言,不健康、不文明和不科學的休閑生活方式,應該被取締。
(3)文化引領。于光遠先生早就提出,要有文化地休閑。休閑應該有法度、有技巧、有規則、有節制。有文化地休閑是對社會個體發展的本質要求。首先,休閑活動是創造性活動。有文化的休閑要求人們在休閑活動中發揮積極能動性,發揮創造力,在閑暇中創造高品位的生活質量,擺脫生物本能的束縛。其次,休閑活動是改造自身的活動。成思危先生認為,工業革命以來的幾百年時間里,人們致力于改造世界,在新的世紀,人類將會更多地致力于改造自身[9]。這就要求人們的休閑方式具備“以文化人”的功效,彰顯文化價值,因此,高質量的休閑生活方式,應該是“雅閑”,具有超越性和發展性,最終指向精神的愉悅和自我的提升。
(4)中國氣派。中國人民不僅勤勞質樸,更是熱愛生活懂得休閑的行家里手。衣食住行、琴棋書畫、詩詞歌賦、花鳥魚蟲、閑情偶寄、漁歌唱晚、長物伴身,在五千年歷史中形成了獨具魅力的休閑文化特色,是世界文化的瑰寶,是當今休閑文化繼承與發展的重要內容。吳自牧在《夢梁錄》中詳細記載了北宋時期中國人休閑生活的基本內容: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高品質的休閑生活方式,應該傳承中華文明的休閑文化成果,彰顯本土文化氣度,揚棄式地復現中國生活,別開生面地創造出休閑生活的中國氣派。
美好生活是奮斗出來的,奮斗的目的是為了更美好的生活,休閑是奮斗的根本目的之一。隨著國內大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建立,構建高品質的休閑生活方式,無論是對個體自由全面發展還是對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必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