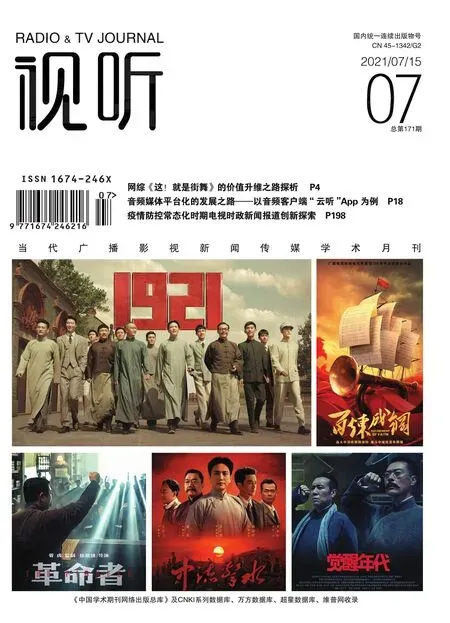國產(chǎn)青春片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敘事探究
成 錦
國產(chǎn)青春片備受大眾歡迎,在電影市場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縱觀近十年的國產(chǎn)青春片,主要可以分為三種類別。一是以《致青春》拉開帷幕的“校園青春片”,這類影片以對校園青春的懷念為主,但在類型探索過程中由于過度迎合市場而帶來內(nèi)容的重復(fù)和創(chuàng)新的停滯,屢屢遇冷后,最終在觀眾的審美疲勞和市場飽和中遠(yuǎn)去。二是以《閃光少女》《快把我哥帶走》等為代表的“精準(zhǔn)青春片”,這類影片以展現(xiàn)青年亞文化為主,觸及時(shí)代命題,但更多面向青少年,無意深入探討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問題。三是以《狗十三》《過春天》《少年的你》等為代表的利用現(xiàn)實(shí)主義手法創(chuàng)作的青春片(以下簡稱:現(xiàn)實(shí)主義青春片),這類青春片將原生家庭問題、水客走私、校園暴力等社會(huì)問題與青少年的個(gè)體成長相連接,重新解讀“年輕個(gè)體”與“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力圖在銀幕上呈現(xiàn)出“現(xiàn)實(shí)感”。影片中的青少年也不再是原子化的個(gè)體,而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青春的滋味從甜膩淺薄豐富為一言難盡,推動(dòng)了國產(chǎn)青春片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主題從單一走向多元。
一、多維人物塑造,關(guān)照個(gè)人成長
(一)鏡像比對,尋求認(rèn)同
現(xiàn)實(shí)主義青春片采用鏡像手法展示人物成長歷程,無論是《七月與安生》中的七月和安生、《狗十三》中的李玩與愛因斯坦,還是《少年的你》中的陳念與劉北山,當(dāng)下青少年的迷茫不安、自我認(rèn)同的匱乏及其現(xiàn)代性人格的形成過程都能在鏡像中有所窺探。
《狗十三》中,寵物狗“愛因斯坦”的到來與失去影響著李玩的“誤認(rèn)”與“認(rèn)同”,再現(xiàn)了青少年現(xiàn)代性人格形成的過程。李玩開始不接受“愛因斯坦”,但長期缺愛帶來的不安全感與匱乏性的欲望召喚,使她慢慢實(shí)現(xiàn)對“愛因斯坦”的“誤認(rèn)”。指鹿為馬的換狗后,李玩的自我與他者生硬割裂,直至“假愛因斯坦”與同父異母弟弟為敵,李玩的潛意識(shí)才認(rèn)同“假愛因斯坦”,實(shí)現(xiàn)第二次“誤認(rèn)”,不久“假愛因斯坦”被送去狗肉店,李玩的自我與他者再次割裂。在不斷驗(yàn)證自己的“認(rèn)同”都是“誤認(rèn)”的過程中,李玩吃下狗肉,實(shí)現(xiàn)了與其說是自我主體性建構(gòu),不如說是自我妥協(xié)式的成長。
相比于反復(fù)“認(rèn)同”與“誤認(rèn)”建構(gòu)起被馴化的主體,《少年的你》則將兩個(gè)極為相似的少年并置在一起。陳念和劉北山擁有相似的年紀(jì),同樣破碎的原生家庭和被欺凌的社會(huì)地位,雙方是彼此的他者,負(fù)載著同樣的堅(jiān)定與不妥協(xié),建構(gòu)起想象中的主體,實(shí)現(xiàn)自我的歸屬與認(rèn)同。
(二)二律背反,對話共情
現(xiàn)實(shí)主義青春片在塑造人物時(shí)關(guān)注人物性格內(nèi)部的多重形態(tài),從多角度展現(xiàn)青少年性格的矛盾化發(fā)展,塑造飽滿立體的人物形象。
《狗十三》清晰展示了典型中國式成長語境下青少年性格形成的矛盾過程。遭受家暴的李玩,一面抗拒父親的專橫跋扈,一面又痛心于父親的歉意無奈,任性又乖巧的李玩學(xué)會(huì)沉默著倔強(qiáng)。指鹿為馬的換狗,接受又失去狗后,一系列的傷痛讓李玩向成人世界一步步妥協(xié)。最后在街角偷偷失聲痛哭,是單純懵懂的李玩實(shí)現(xiàn)了自我意志的完全剝落,在無奈與不甘中扮演毫無鋒芒的乖孩子。
《過春天》中通過對單非學(xué)童性格成長過程的細(xì)膩勾勒,體現(xiàn)青少年對自我歸屬的追尋。單非學(xué)童的身份、原生家庭的缺席,佩佩帶有天然而鮮明的孤獨(dú)與迷茫,渴望被認(rèn)同,就要攢錢和閨蜜去北海道賞雪,本是為了賺錢卻在水客組織中收獲了虛假的溫暖,以為那里便是歸屬;面對母親時(shí)的沉默、倔強(qiáng)、叛逆,與面對一窗之隔卻無法相認(rèn)的父親時(shí)的隱忍、成熟、心酸,勾勒出佩佩成長中矛盾的性格。
在自我認(rèn)同的尋求與探索中發(fā)現(xiàn)矛盾化的性格,是人類普遍擁有的青春經(jīng)歷。影片采用二律背反的方式呈現(xiàn)人物性格發(fā)展,更能引發(fā)觀眾的共情,同時(shí)也增強(qiáng)了影片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力量。
二、多元視點(diǎn)選擇,聚焦青春共性
(一)視覺聚焦,塊莖文本
若斯特在《什么是電影敘事學(xué)》中提出零視覺聚焦,是指“任何人物之外,采用一種未強(qiáng)調(diào)的機(jī)位,只展現(xiàn)場面而最大限度地使人忘記攝影機(jī)”,“鏡頭因此歸屬于大影像師”。國產(chǎn)現(xiàn)實(shí)主義青春片采用零視覺聚焦方式,從大影像師的角度呈現(xiàn)故事,以一種去中心化的敘事方式,形成“塊莖文本”,將成長問題與社會(huì)問題安靜客觀地滲透到敘事中。
青春的成長過程即青少年社會(huì)化的過程,影片中的成長總是伴隨失望與傷痛。無論是佩佩前一秒被花姐叫干女兒,下一秒就被逼迫走私槍支犯罪,還是陳念面對居高臨下的女警“被拍了裸照還能安心復(fù)習(xí)”的質(zhì)問,成長的過程總被社會(huì)的危險(xiǎn)與惡意裹挾,逼迫這些孩子們收斂鋒芒,小心前行。
影片在人物、情節(jié)、場景的選擇呈現(xiàn)上也都別有深意。《狗十三》中大量出現(xiàn)的酒宴情節(jié),暗示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群體認(rèn)同需求,孫子的生日宴是“母憑子貴”的主權(quán)宣示,父親的工作飯局是典型的中國式成人游戲,李玩保送的慶功宴是成人世界的儀式化認(rèn)同,父權(quán)的強(qiáng)勢、職場的虛偽、傳統(tǒng)的誤讀都囊括于飯局中。“塊莖文本”如同一張大網(wǎng),將社會(huì)問題與成長問題相互勾連,達(dá)成對現(xiàn)實(shí)的多維透視。
(二)聽覺聚焦,成長回歸
“在話語陳述中,陳述者有別于說話者,是采取視角的人”,若斯特在《什么是電影敘事學(xué)》中提出內(nèi)聽覺聚焦概念,表示通過敘事中某一人物的聽覺聽到的聲音。國產(chǎn)現(xiàn)實(shí)主義青春片中經(jīng)常采用內(nèi)聽覺聚焦方式展示主人公的成長與回歸,使他們在傾聽中宣泄青春的壓抑,理解成人世界的不易和父母錯(cuò)位的愛。
《狗十三》中愛因斯坦丟后,鏡頭進(jìn)入李玩的房間,從隔著一面墻的悶聲音樂到震耳欲聾的嘈雜爆裂,采用的是李玩的內(nèi)聽覺聚焦,將她內(nèi)心的無助、焦躁、痛苦外化宣泄。狗肉宴后,李玩坐在父親的副駕駛上,與母親通完電話,打開收音機(jī)是《再回首》的音樂,父親終于忍不住伸手捂住李玩的眼睛痛哭起來。李玩不知所措地聽著這一切,成人世界的不易在這一刻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再回首曾經(jīng),父親也許也像李玩這樣長大;再回首曾經(jīng),父親也許并不真正愿意與母親分開,只是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無奈與艱辛,讓父親別無選擇,李玩在這一刻也聽到了父親的不易。
三、多層空間敘事,揭示現(xiàn)實(shí)主題
加布里爾·佐倫將空間敘事分為三個(gè)層面:地志空間、時(shí)空體空間和文本空間。影像敘事是時(shí)空的敘事,空間在敘事中占據(jù)重要地位,國產(chǎn)現(xiàn)實(shí)主義青春片從地志空間和文本空間共同出發(fā)深化現(xiàn)實(shí)感。
(一)文本空間,青春痛感
文本空間是“通過言語文本中所表示的內(nèi)容作用于空間,這個(gè)層次包含在言語文本中形成的影響空間的結(jié)構(gòu)”。國產(chǎn)現(xiàn)實(shí)主義青春片中,文本空間表現(xiàn)為鏡語修辭和象征性意象的呈現(xiàn)。
影片大量采用冷色調(diào)表現(xiàn)疏離冷漠,甚至殘酷的暗示。《嘉年華》和《少年的你》中小文與陳念的衣服始終以冷色調(diào)藍(lán)白灰為主,表達(dá)壓抑的同時(shí),暗示了小文和陳念面對無法抗拒的傷痛時(shí)的無助與孤獨(dú)。影片中大量的快速剪輯和晃動(dòng)鏡頭,表達(dá)出青少年面對成長時(shí)的焦慮不安。《少年的你》中,陳念在胡同被霸凌時(shí)的快速剪輯,放大了陳念的恐懼,暗示了青少年施暴時(shí)的失控;《過春天》中大量擁擠街道的畫面,迅速走過的人群,無不面目模糊,在熙熙攘攘的大社會(huì)里,佩佩顯得更加無助渺小。
除了畫面,影片還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某個(gè)地方或空間意象作為青少年壓抑成長中的棲息地。無論是《過春天》中的日本,《狗十三》中的宇宙,還是《少年的你》中的大學(xué),都表達(dá)出青少年成長歷程中對于當(dāng)下的不滿不安和渴望逃離的心境。
(二)地志空間,現(xiàn)實(shí)矛盾
地志空間是指靜態(tài)實(shí)體空間,相比于以往的青春片,國產(chǎn)現(xiàn)實(shí)主義青春片不拘泥于校園,將大量的情節(jié)段落放置在家庭與社會(huì)環(huán)境中,從社會(huì)的角度重新觀看青少年成長,進(jìn)而凝視現(xiàn)實(shí)問題。
地志空間支配和影響著心理空間的形成與發(fā)展,心理空間“關(guān)注個(gè)別的、本能的情感和欲望轉(zhuǎn)換為普遍意義的倫理文化的機(jī)理”。影片將大量矛盾沖突放置在復(fù)雜的家庭空間中,探討了原生家庭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狗十三》中李玩的成長便是原生家庭對她的馴化過程,奶奶以溺愛者形象出現(xiàn),打著“為你好”的旗號不容反抗地要她喝下不能接受的牛奶,父親作為強(qiáng)勢父權(quán)的角色以暴力規(guī)訓(xùn)李玩,反復(fù)出現(xiàn)的窗欄是家庭如牢籠般將李玩囚禁其中,馴化為“懂事”的孩子。影片對原生家庭的探討,也體現(xiàn)出對當(dāng)下社會(huì)中國式離婚和家庭教育的觀照。
除了家庭環(huán)境,大量的情節(jié)段落發(fā)生在社會(huì)場景中,將觀眾的視野拉入社會(huì)環(huán)境中重新審視現(xiàn)實(shí)問題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少年的你》中陳念遭受校園霸凌的重要情節(jié)在窄小胡同中發(fā)生,探討的是離開校園,青少年在面對暴力傷害時(shí)該如何自保與反抗,以及在嚴(yán)密的社會(huì)規(guī)則下如何有效保護(hù)弱者。《過春天》的故事發(fā)生在深圳和香港,單非學(xué)童佩佩每日往返于兩地,深圳有家卻沒有心靈的棲息,香港有朋友卻沒有歸屬的家,港深兩地的發(fā)展產(chǎn)生跨境群體生存的焦慮與迷茫,本土文化與國際性文化交融帶來群體性歸屬感的缺失。
四、結(jié)語
國產(chǎn)青春片對青少年真實(shí)成長問題與社會(huì)現(xiàn)象的深耕挖掘,體現(xiàn)了影視創(chuàng)作的社會(huì)責(zé)任與擔(dān)當(dāng),通過敘事層面的人物、視點(diǎn)和空間的多重發(fā)力,將類型敘事與現(xiàn)實(shí)主題相結(jié)合,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創(chuàng)作特點(diǎn)的新型表達(dá)路徑,促進(jìn)了國產(chǎn)青春片在新時(shí)代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轉(zhuǎn)型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