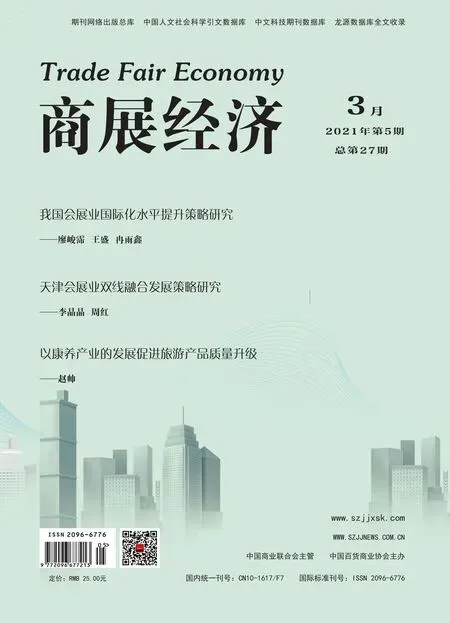我國金融科技監管政策研究及建議
——以“暫停螞蟻集團上市”為例
江蘇師范大學科文學院 姜夢悅
經過十余年的發展,金融科技已經成為推動我國金融轉型升級的新引擎、服務實體經濟的新途徑。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將金融科技定義為“技術帶動的金融創新,依托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進行金融模式、業務、流程和產品的創新升華,進而影響金融市場所能提供的服務與模式”。
金融科技不斷創新的同時,也在不斷觸碰現有監管體制的界限,如何實現及時有效的監管,如何在金融創新與金融安全中取得動態平衡,成為監管部門面臨的主要問題。面對金融科技的日益創新,我國的金融科技監管制度也在不斷改革。從最初側重于對商業銀行網絡支付業務的監管,到對金融科技機構網絡借貸、支付業務的監管,我國監管部門逐步推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同時結合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實現了監管成本的降低和監管效率的提升[1]。
2020年10月31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會議,會議強調當前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快速發展,必須處理好金融發展、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的關系。2021年1月3日晚,上海證券交易所對外宣布暫停螞蟻集團上市的決定。“暫停螞蟻集團上市”事件,反映出在當前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監管制度沒能建立與金融科技發展相對應的監管制度,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仍然存在亟待解決的諸多問題。
1 金融科技隱含的金融風險
在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同時,新興金融業務也在不斷涌現。相較于傳統金融業務的風險,新興金融科技業務的風險更加具有互聯網特征。
1.1 網絡安全風險加大
金融科技以互聯網為平臺提供金融服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服務成本,提高了服務效率,但也由此帶來了具有互聯網特征的金融風險。在金融科技市場的混業格局下,金融交易對網絡的攻擊愈加敏感,可供黑客攻擊的金融業務也在不斷增加。另外,也出現了金融數據公司濫用抓取金融消費者的個人數據,形成販賣數據的產業鏈現象,造成客戶信息泄露[2]。監管部門如果不能形成及時有效的監管體系,可能會帶來數據安全的問題。
1.2 加劇技術性風險
金融科技對于技術依賴性高,由于技術漏洞、系統缺陷、技術失靈等原因都可能發生技術性風險[3]。傳統金融業務結合線上線下操作,從某種程度上能夠避免部分技術風險,但金融科技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容易造成更為特殊和復雜的技術風險。技術上的漏洞和失誤將會快速反映在實時交易中,進而發生連鎖反應,甚至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發生[4]。
1.3 風險傳染性更高
金融科技業務普及性強,風險傳染性高。在支付、信貸方面,使用移動端APP進行線上支付、借貸現象已十分普遍,相比傳統金融業務,金融科技拓寬了客戶群,導致風險傳播性更強。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更加降低了客戶的服務門檻,打破了原有金融服務的生態圈。金融科技使得客戶關系更為廣泛,市場環境更為復雜,一旦發生金融風險,加上互聯網的擴散效應,進而導致金融風險的進一步加大。
2 我國金融科技監管存在的問題
我國監管部門雖然在金融科技監管領域已經實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比如開展“監管沙盒”試點工作,拓展金融科技監管應用場景等,但總體來說,目前我國的監管工作仍處于被動地位,監管水平依然不能滿足金融科技產業的飛速發展,現有監管制度急需進一步改革。
2.1 金融科技監管未能標準化
以螞蟻集團為例,螞蟻集團是一家金融公司還是科技公司目前還沒有明確的判定標準。從螞蟻集團選擇在科創板上市來看,螞蟻集團應該是一家科技類公司。但從螞蟻集團的招股說明書中不難發現,螞蟻集團核心業務主要包括數字支付與商家服務、金融科技平臺業務以及創新業務。其中數字支付與商家服務業務的收入主要來源于收取境內外商業交易、個人交易中的服務費,從本質上看,這與傳統金融機構提供的支付業務并無區別,該業務在2020年上半年的收入結構中占比35.68%。金融科技平臺業務主要通過提供代銷服務來收取代銷費,比如向客戶代銷理財產品、保險產品等,這部分業務收入占2020年上半年收入結構的63.39%,而真正的金融科技創新業務只占比不到1%。從數據可以看出,目前螞蟻集團大部分的收入來源于傳統金融業務,因此,螞蟻集團更多的還是一家具有金融屬性的公司[5]。由此反映出,目前監管部門對金融科技企業的商業屬性并沒有形成標準化的認知,造成監管對象分類困難,金融科技公司定義模糊等問題。
2.2 金融監管模式滯后
當前我國金融監管主要實行事前審批、事后懲罰的監管理念[6]。金融科技作為一種復合型新興產業,并沒有形成與之相對應的監管法律法規。例如,螞蟻集團的招股說明書中顯示,公司平臺促成的貸款中主要由金融機構合作伙伴獨立發放,這些合作伙伴包括約100家政策性銀行、大型商業銀行、農商行等。在公司平臺促成的信貸余額中,有98%的信貸由金融機構合作伙伴進行實際放款,螞蟻集團提供信貸占比約2%。在這種聯合貸款的模式中,對螞蟻集團或銀行都存在諸多風險,一是螞蟻集團杠桿率較高,但自身風險管理水平、風險承受能力較弱;二是銀行雖然作為貸款的主要債權人,但主要依靠螞蟻集團提供的渠道獲得客戶,容易過度依賴科技平臺,忽略對于客戶信息的詳細掌握。監管部門在發現聯合貸款中的潛在風險后,于2020年11月2日,由中國銀保監會出臺網貸新規,在新規中規定,單筆聯合貸款中,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不得低于30%,由此限制了科技公司在聯合貸款中最低出資比例。這反映出我國在金融科技監管方面行動滯后,欠缺發現潛在風險的意識,以及缺少與之對應的監管法律法規,這樣既不利于金融市場以及秩序的穩定,容易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更不利于監管部門樹立專業權威的社會形象。
2.3 金融科技與金融安全的動態平衡問題
在由中國人民銀行印發的《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19-2021)年》中,明確提出到2021年要增強金融業科技應用能力,推動我國金融科技水平,促進金融科技產業繁榮發展。根據規劃中的要求,螞蟻集團作為金融科技領域的佼佼者,如果能在科創板上市,無疑會促進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但在促進金融科技發展的同時,監管部門也要堅決維護金融穩定,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那么面對金融創新與監管法規的邊界,監管部門如何在金融科技創新與金融安全中取得動態平衡,如何在鼓勵金融科技企業技術創新的同時,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同樣是監管制度需要改革的方向。
3 我國金融科技監管政策建議
雖然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也在不斷地進行改革和完善,但螞蟻集團事件的發生,仍反映出我國現有監管制度存在的短板。針對金融科技的發展,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應建立切合發展需要、防范金融風險、促進金融創新的成熟監管體系。
3.1 建立分類監管制度
在重視金融科技發展,認可金融科技重要性的同時,面對金融科技日新月異的變革與創新,相關監管部門應盡快建立有別于傳統金融機構監管的法律法規,對金融科技公司及其業務進行分類監管,設置金融科技準入門檻和退出機制,針對不同金融科技業務制定相應的法規,實現監管過程的標準化、穩定性和合理性,這樣既有利于促進金融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同時也能夠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與安全。
3.2 加快推廣和深入“監管沙盒”制度
英國于2015年提出“監管沙盒”制度,該制度用來測試金融創新產品、服務、商業模式、營銷方式,可由監管機構自主選擇監管松緊度的“安全空間”[7]。目前我國已逐步開展中國版“監管沙盒”的試點工作。在試點工作的基礎上,要確定統籌管理機構,建議由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領導,強化宏觀層面的審慎監管以及微觀層面的行為監管。在監管過程中,監管部門要幫助企業及時了解監管政策,還要鼓勵企業進行金融技術創新,在試點過程中,進一步深化完善“監管沙盒”機制,構建符合中國國情及發展需要的“監管沙盒”制度,逐步實現向全國推廣。
3.3 建立與金融科技企業的信息溝通機制
監管部門應加強與金融科技企業的溝通交流。首先,監管部門要及時掌握金融科技產業最新發展動態,提早介入監管,并進行政策引導,嚴控潛在風險。其次,監管部門要為金融科技企業提供適宜的科技創新環境,就要了解金融科技企業的需求和問題,才能及時給予政策層面的指導。最后,監管部門也應向相關金融科技企業學習,培養自己的金融科技人才,提高金融監管的專業性和有效性。
3.4 提升金融科技監管技術水平
在金融科技發展的同時,監管科技也應進行改革。監管部門應以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現代科技手段為基礎,逐漸提升監管技術水平,使監管具有智能化和前瞻性。區別于傳統金融模式中的經驗監管、事后監管,監管科技要能夠迅速發現監管漏洞,快速形成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有效提升監管質量和監管水平,及時發現潛在風險,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發生,降低監管成本。
3.5 構建監管科技生態體系
金融監管不應只涉及監管部門和被監管機構,應將消費者、司法機構、科研院所等多方聯動起來,實現利益共享、目標多元的監管格局,這樣才能在垂直監管層面實現可行性監管,在水平監管層面實現良性互動,充分發揮監管資源的有效配置,使監管流程更具前瞻性、包容性、多元性,構建和諧共融的監管生態體系。
4 結語
本文以“暫停螞蟻集團上市”為例,分析了當前金融科技產業迅猛發展的同時,我國監管制度所暴露出的問題。在充分肯定金融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意識到金融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潛在風險,我國要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就要從法律層面、管理層面、技術層面不斷完善我國金融科技監管制度,構建和諧發展的金融監管生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