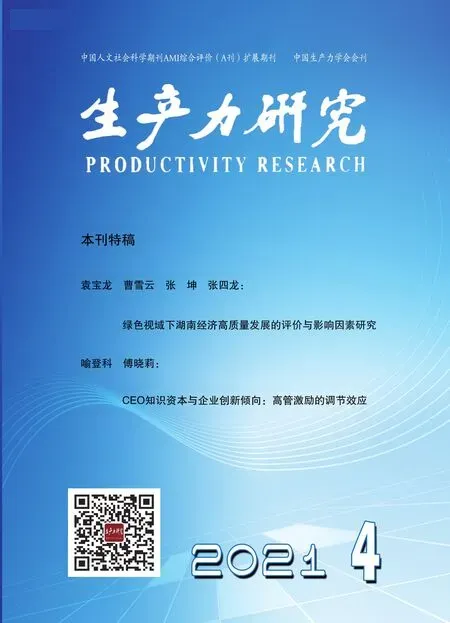股權(quán)激勵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關(guān)系研究綜述
(上海理工大學(xué) 管理學(xué)院,上海 200093)
一、引言
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院發(fā)布的《國家創(chuàng)新指數(shù)報告2018》中,中國在全球40 個創(chuàng)新活動活躍的國家中排名第17 位[1]。同時,歐盟委員會在其發(fā)布的《2019 歐洲創(chuàng)新記分牌》中將中國列為中等創(chuàng)新國家,在非歐盟國家中排名第6 位。
通常而言,研發(fā)活動是企業(yè)創(chuàng)新最主要的體現(xiàn),但由于其高投入、高風(fēng)險、周期長等特點,在沒有足夠激勵的情形下,公司管理層主動進行研發(fā)活動的積極性不高。現(xiàn)有研究證實,對高管進行股權(quán)激勵是一種長久有效的激勵行為,能在一定程度上統(tǒng)一企業(yè)股權(quán)持有者與管理層間的利益關(guān)聯(lián),從而減緩代理矛盾,進而促使管理層愿意進行研發(fā)項目。但是其具體作用機制如何,不同因素如何在股權(quán)激勵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間構(gòu)建起聯(lián)系還并不明晰。本文從常用理論、激勵方式、激勵對象、企業(yè)類型四個方面對已有文獻進行分析,旨在大致了解股權(quán)激勵的創(chuàng)新促進效應(yīng)方面的已有結(jié)論。
二、常用理論
(一)委托代理理論
在股份制企業(yè)中,由于所有權(quán)和控制權(quán)的兩權(quán)分離,容易出現(xiàn)委托代理問題。理論上,股東作為企業(yè)所有者,對于創(chuàng)新這一可以長期維持企業(yè)生命力與市場競爭力的行為,會愿意接受高風(fēng)險高投入的代價以追求長期利益。但是作為實際執(zhí)行者的管理層則傾向于規(guī)避風(fēng)險,這大多是因為將其收入和穩(wěn)定性置于最優(yōu)先考量位置。研發(fā)創(chuàng)新固然有助于長遠發(fā)展,但是一旦研發(fā)失敗,企業(yè)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擔(dān)血本無歸的風(fēng)險及不確定的最終收益。在這種前提下,管理層很可能會出現(xiàn)短視行為,通過選擇相對穩(wěn)妥的短期項目來回避損失。且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公司所有者很難對管理層行為進行有效全面的監(jiān)督。與此同時,股權(quán)激勵將股東長期利益與管理層短期利益相結(jié)合,使得管理層短期利益與企業(yè)長遠利益掛鉤,促使其重視未來發(fā)展,提高研發(fā)投入。
(二)管理心理學(xué)理論
根據(jù)美國學(xué)者Alderfer 的ERG 理論,人的需要可以分為三種:生存需要、關(guān)系需要和成長需要。這一理論用來分析中層管理人員和核心員工等更為合適。首先,對于底層員工而言,公司滿足的只有最低的生存需要;此時當(dāng)股權(quán)被給予這些對公司決策并無過大影響的員工時,公司所有權(quán)會讓其激發(fā)出自身責(zé)任感,對公司未來收益產(chǎn)生心理所有權(quán),進而表現(xiàn)出額外的創(chuàng)新行為,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監(jiān)督管理者,加強了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其次,對于表現(xiàn)優(yōu)異的員工,當(dāng)公司給予其一定股權(quán),會讓其感覺被自我肯定,希望在未來做出相應(yīng)價值回報的心理,進而調(diào)動其積極性并增強其忠誠感,更努力地工作從而表現(xiàn)出額外的創(chuàng)新行為,這一層次滿足的則是關(guān)系需要。最后,對于中層管理人員和核心技術(shù)人員這些創(chuàng)新最重要的執(zhí)行者和實施者,股權(quán)激勵可以更好地滿足其成長需要,有助于企業(yè)留住人才并提升其對公司未來發(fā)展的關(guān)注,進而提高其創(chuàng)新行為。
三、不同股權(quán)激勵方式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
現(xiàn)階段股權(quán)激勵方式主要有兩種,分別是股票期權(quán)和限制性股票,且其創(chuàng)新激勵效應(yīng)也不盡相同。依據(jù)姬怡婷和陳昆玉(2020)[2]的定義,股票期權(quán)是一種行權(quán)權(quán)利,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激勵對象可以自主選擇是否行使權(quán)利來影響自身收益,在股票價格低于期權(quán)持有人事先購買價格時,持有人將不會行使權(quán)利,從而降低受損的可能性。而限制性股票則是事先規(guī)定授予及出售條件,公司先授予激勵對象相當(dāng)數(shù)量的股票,持股者可在適當(dāng)情況下出售股票,進而從中獲益。
兩種激勵方式在權(quán)利義務(wù)的對稱性及收益曲線特征上也存在一定差異。一方面,限制性股票是激勵對象自發(fā)利用個人資金進行購買,因而其收益或損失均隨股價線性波動,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激勵對象對風(fēng)險的擔(dān)憂與厭惡。可見,持有限制性股票的高管屬于風(fēng)險厭惡者,因而為減少或避免損失,他們有可能會選擇放棄對公司長久發(fā)展有利的高風(fēng)險項目;而股票期權(quán)則避免了高管承擔(dān)在投資決策失誤時所帶來的損失。另一方面,兩種激勵方式在發(fā)揮作用的過程中也不完全一致,例如,會計準則中對兩種激勵方式的記賬要求存在差異,公司會更傾向于選擇規(guī)定更為寬松的股票期權(quán)。
已有文獻的研究結(jié)論基本類似:(1)股票期權(quán)比限制性股票的激勵效果更好。田軒和孟清揚(2018)[3]發(fā)現(xiàn),股票期權(quán)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限制性股票的激勵效果相對不顯著。宋迪等(2018)[4]也指出,對比限制性股票,實施股票期權(quán)的公司的業(yè)績規(guī)劃與其創(chuàng)新投入、產(chǎn)出的關(guān)系更顯著。姬怡婷和陳昆玉(2020)[2]發(fā)現(xiàn),在混合制上市公司中,股票期權(quán)很有效地提高了創(chuàng)新產(chǎn)出,限制性股票則效用不大。更進一步地,股票期權(quán)的實施方式也會影響到其對公司創(chuàng)新的促進作用,郭蕾等(2019)[5]指出,較長有效期或授予范圍較廣的股票期權(quán)更能促進創(chuàng)新產(chǎn)出,特別是發(fā)明專利,且業(yè)績考核并不是越嚴格越好,適度嚴格能促進創(chuàng)新產(chǎn)出,一旦過于嚴格還會抑制創(chuàng)新。(2)不同股權(quán)激勵方式的效應(yīng)并無太多不同。郭蕾等(2019)[5]指出,激勵差距越大,其對創(chuàng)新產(chǎn)出的促進效用越明顯,與激勵模式為何無關(guān)。同時,李雪婧等(2020)[6]也發(fā)現(xiàn):在不同激勵方式下,員工的風(fēng)險承擔(dān)意愿、離職傾向和創(chuàng)新行為并無顯著不同,僅在認同程度上有顯著差異,且具體表現(xiàn)為實施股票期權(quán)比實施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內(nèi),員工對組織互惠的感知更低。(3)在不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下股權(quán)激勵方式對創(chuàng)新績效的影響。舒文燕等(2018)[7]發(fā)現(xiàn),同樣以高管為對象,在國有企業(yè)中僅有一種激勵方式即限制性股票更有助于增進企業(yè)創(chuàng)新產(chǎn)出,但在非國有企業(yè)中兩種激勵方式都能促進創(chuàng)新績效。
四、不同股權(quán)激勵對象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
目前文章大多是對高管進行激勵,因為高管作為企業(yè)決策者,對創(chuàng)新投入和發(fā)展方向有更大話語權(quán)。但是考慮到核心技術(shù)員工等才是創(chuàng)新活動的真正執(zhí)行者,也有少部分文章對核心技術(shù)員工甚至所有員工的股權(quán)激勵效應(yīng)進行研究。現(xiàn)有文獻可以從核心技術(shù)員工(可同時包含高管)、僅高管和所有員工三個角度考察不同股權(quán)激勵對象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
(一)核心技術(shù)員工(可同時包含高管)
所有文章幾乎都肯定了對核心技術(shù)員工進行股權(quán)激勵的積極作用。楊華領(lǐng)(2018)[8]發(fā)現(xiàn),對越廣泛的骨干員工實施激勵,該上市公司的發(fā)明專利越多,即便控制其研發(fā)費用依然如此。劉紅等(2018)[9]也指出,對核心技術(shù)員工實施股權(quán)激勵可以有效提升創(chuàng)新績效,且其持股比例與公司技術(shù)創(chuàng)新績效成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并且在國有企業(yè)中,對核心技術(shù)員工實施股權(quán)激勵,其對技術(shù)創(chuàng)新績效的促進作用更顯著,股權(quán)激勵效果更好。
同時,有些文獻也同時肯定了對高管進行股權(quán)激勵的正向影響。馬莉莉等(2020)[10]指出,對高管和核心員工實施股權(quán)激勵,技術(shù)董事與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效率都受到促進作用,且激勵幅度越大,促進作用更明顯。國勇(2020)[11]也指出,特別在股權(quán)較為集中的情況下,對高管和核心技術(shù)人員實施股權(quán)激勵,能夠顯著促進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效率提升。但是,黃新建和尤珊珊(2020)[12]對高管股權(quán)激勵的作用則提出了相反的結(jié)論:對核心員工和高管進行股權(quán)激勵,其技術(shù)創(chuàng)新投入及產(chǎn)出的促進作用正好相反,對高管實施股權(quán)激勵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公司創(chuàng)新投入及產(chǎn)出。這是因為相較于高管,核心員工對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影響更加直接,而高管擁有資源配置的決定權(quán),權(quán)利更大時有可能出現(xiàn)利己行為,例如通過操縱業(yè)績目標,使得行權(quán)條件容易滿足反而對公司利益形成侵害。
(二)僅高管
基本上,文獻都認為高管的股權(quán)激勵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間并非單純的線性關(guān)系。馬瑞光和溫軍(2019)[13]研究證實,高管持股比例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之間是顯著的倒U 型關(guān)系。具體而言,當(dāng)持有公司股票的高管人數(shù)較少時,隨著持股人數(shù)的增加,會不斷促進公司創(chuàng)新;而當(dāng)持有公司股票的高管超過一定比例后,高管進行研發(fā)創(chuàng)新的動機減弱,對著持股比例的繼續(xù)增加,其創(chuàng)新效應(yīng)開始變得不顯著。同時,馬桂芬(2020)[14]加入內(nèi)部控制這一變量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三者存在正向的遞進促進關(guān)系,具體而言,股權(quán)激勵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成正向關(guān)系,當(dāng)激勵越大時,創(chuàng)新產(chǎn)出得到提升,進而高管有意愿改進內(nèi)部控制;除此之外,恰當(dāng)?shù)膬?nèi)部控制可以引導(dǎo)股權(quán)激勵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方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管理層創(chuàng)新決策失誤的可能,進而減緩股權(quán)激勵創(chuàng)新效應(yīng)的不完美。此外,姬怡婷和陳昆玉(2020)[15]還針對不同類型國有企業(yè)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在競爭類國有企業(yè)中,對高管實施股權(quán)激勵,會弱化混合主體深入性對創(chuàng)新投入的促進效應(yīng),而在公益類國有企業(yè)中其促進效應(yīng)不顯著。
(三)所有員工
孟慶斌等(2019)[16]考察了實施員工持股計劃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實施員工持股計劃通過將員工利益與企業(yè)利益相綁定,提升其在創(chuàng)新過程中的努力積極性、團隊協(xié)作能力和穩(wěn)定性,進而促進了其創(chuàng)新產(chǎn)出。特別地,員工持股計劃的創(chuàng)新產(chǎn)出促進作用來自持股員工而非管理層,并且持股員工數(shù)的擴大可能會引發(fā)“搭便車”行為,并不能持續(xù)促進企業(yè)創(chuàng)新。
五、股權(quán)激勵對不同類型公司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
在不同類型企業(yè)中,股權(quán)激勵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也不盡相同,本文通過對現(xiàn)有文獻的歸納梳理,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創(chuàng)新效應(yīng)進行分析,即不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股權(quán)集中度和特殊類型企業(yè)。
(一)不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
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不同的產(chǎn)權(quán)方式導(dǎo)致的話語權(quán)問題會直接影響股權(quán)激勵的效果。田軒和孟清揚(2018)[3]研究發(fā)現(xiàn),在民營企業(yè)以及股價信息含量較高的企業(yè)中,股權(quán)激勵的創(chuàng)新正向影響更加顯著。同時姬怡婷和陳昆玉(2020)[2]發(fā)現(xiàn),同樣是采用股票期權(quán)的激勵方式,相較于完全民營化的企業(yè),部分民營化的企業(yè)中股權(quán)激勵的創(chuàng)新促進作用不夠顯著。特別地,楊慧輝等(2018)[17]通過研究國企改民營的上海家化三次股權(quán)激勵的效果得出結(jié)論:(1)國有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下的所有權(quán)缺位問題會導(dǎo)致管理層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且股東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監(jiān)督,股權(quán)激勵契約容易成為其自謀福利的工具;(2)非國有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下管理層與控股股東的權(quán)力制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管理層的風(fēng)險厭惡和短視行為,進而引導(dǎo)其加大創(chuàng)新投入,但同時股權(quán)激勵契約也容易成為股東與管理層合謀進行利益侵占的工具。
究其根源,或許是相較于國有企業(yè),民營企業(yè)實施股權(quán)激勵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留住企業(yè)人才,核心人員對報酬的敏感度更高;而國有企業(yè)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問題,公司治理結(jié)構(gòu)先天不足,且受行政干預(yù)較強,資金軟約束也會導(dǎo)致研發(fā)投資的效率較低。
(二)股權(quán)集中度
現(xiàn)有文章對不同股權(quán)集中度下股權(quán)激勵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進行研究。張玉娟和湯湘希(2018)[18]研究發(fā)現(xiàn),股權(quán)集中度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有抑制作用,且消極影響在民營企業(yè)中更顯著。而陸國慶(2019)[19]恰恰持相反的觀點:在股權(quán)集中而非分散的企業(yè)中,實施股權(quán)激勵更能調(diào)動企業(yè)投資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特別地,楊慧輝等(2020)[20]從終極控股股東控制權(quán)與現(xiàn)金流權(quán)匹配角度考察不同股權(quán)的股東推行股權(quán)激勵的動機,發(fā)現(xiàn)在兩權(quán)匹配的環(huán)境中,實施股權(quán)激勵更能提升公司的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且兩權(quán)匹配的控股股東的控制權(quán)越大,股權(quán)激勵對公司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的促進效應(yīng)越明顯。
(三)特殊類型公司
廖戎戎等(2018)[21]選取了銀行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其管理層持股對創(chuàng)新能力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管理層持股與城市商業(yè)銀行的創(chuàng)新能力有顯著促進作用,且以銀行風(fēng)險為變量,管理層持股對城市商業(yè)銀行創(chuàng)新能力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具體表現(xiàn)為當(dāng)風(fēng)險較低時,管理層持股的創(chuàng)新促進效用會顯著增加,但當(dāng)風(fēng)險較高時,管理層持股對城市商業(yè)銀行的創(chuàng)新能力沒有影響。
除此以外,徐寧等(2020)[22]分析了有無高管股權(quán)激勵的中小企業(yè)間創(chuàng)新能力的差距,指出在自主研發(fā)投入水平、突破性創(chuàng)新與漸進性創(chuàng)新水平等方面,對高管實施股權(quán)激勵的中小企業(yè)均明顯優(yōu)于未實施股權(quán)激勵的中小企業(yè)。
六、結(jié)論
通過對股權(quán)激勵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文獻進行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首先,股權(quán)激勵作為有效調(diào)節(jié)所有者股東和代理人管理層之間矛盾的長期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管理者的道德風(fēng)險和短視行為,將其自身利益與企業(yè)長遠發(fā)展相連接,進而提高其進行創(chuàng)新活動的積極性,從而提升企業(yè)創(chuàng)新投入和產(chǎn)出。其次,股票期權(quán)由于其非對稱的收益曲線更加收到員工的青睞,因為可以同享收益并規(guī)避虧損,也更能體現(xiàn)公司的關(guān)懷。最后,相較于國企中復(fù)雜的行政代理問題,民營企業(yè)進行股權(quán)激勵能更有效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提高管理者和員工的風(fēng)險承擔(dān)水平,提升其歸屬感與忠誠度,進而激勵其進行創(chuàng)新行為,在行動上提升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產(chǎn)出。除此以外,現(xiàn)有研究仍有不夠完善的地方,學(xué)者們在今后研究股權(quán)激勵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時應(yīng)關(guān)注以下方面:
(一)拓展研究股權(quán)激勵契約的設(shè)置方法
股權(quán)激勵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已基本得到肯定,只是在不同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或激勵方式下促進作用存在差異,因而如何締結(jié)促進效最大化的股權(quán)激勵契約才是企業(yè)最需獲得的信息。因此,未來的研究應(yīng)對契約設(shè)置有所側(cè)重,例如對多少比例員工實行激勵以及實施何種程度的激勵等。
(二)深化研究股權(quán)激勵促進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作用機制
現(xiàn)有研究達成共識的是,企業(yè)可以通過適度合理的股權(quán)激勵契約來減輕管理層的代理問題,加大創(chuàng)新投入并激發(fā)員工的創(chuàng)新行為,進而提高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產(chǎn)出,但是具體股權(quán)激勵契約是通過何種變量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投入產(chǎn)生作用的仍結(jié)論不一。雖已有一些文獻加入全要素生產(chǎn)率、內(nèi)部控制質(zhì)量或企業(yè)價值來考察作用機制,但仍需更多實證研究來進一步驗證。
(三)關(guān)注特殊類型企業(yè)中股權(quán)激勵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關(guān)系
現(xiàn)有研究大多是依據(jù)上市A 股公司信息來研究股權(quán)激勵的企業(yè)創(chuàng)新效應(yīng),但特殊類型企業(yè)如新興科創(chuàng)板企業(yè),公司規(guī)模小且人員等級相近,傳統(tǒng)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區(qū)分不能有效印證該類型企業(yè)中的激勵效應(yīng)。所以,在未來的研究中,特殊類型的企業(yè)如銀行、軍工企業(yè)、科創(chuàng)板企業(yè)等也可以成為研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