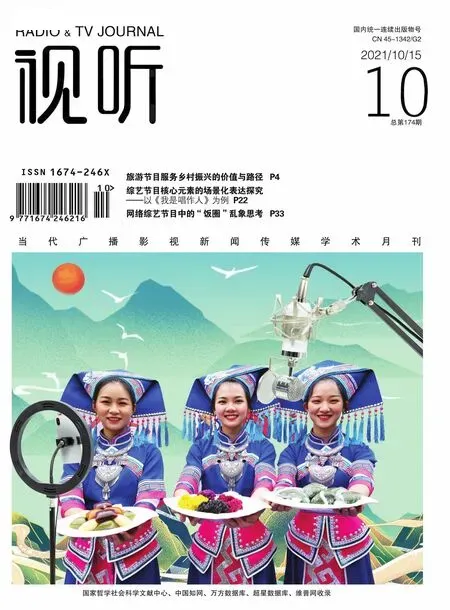媒介融合對傳播觀念的重構(gòu)
吳晗月 周德倉
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xué)者施拉姆創(chuàng)立傳播學(xué),使傳播形成一套理論體系。作為傳播的物質(zhì)平臺與手段,有關(guān)媒介的研究逐漸成為傳播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研究的地位也隨著自身的發(fā)展革新而不斷提升。縱觀歷史長河,每一次媒介的發(fā)展都促使了人類交流與傳播方式的變革,也為媒介與傳播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研究帶來了新的理論視角。
1983年,傳播學(xué)者伊利契爾·索勒·普爾在其《自由的科技》一書中提出了“傳播的形態(tài)融合”這一概念,并將這一概念定義為各種媒介呈現(xiàn)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在此理念下,以互聯(lián)網(wǎng)、手機為代表的數(shù)字媒介迅速發(fā)展,把人類帶進了信息社會,同時,又讓人不禁產(chǎn)生反思,原有的傳播觀念是否仍適用于新的媒介?如果不適用,那么這種媒介給交流與傳播帶來了哪些變化?這種變化又如何以概念化方式表達?
媒介是信息的載體,是傳播的渠道,還是行為的方式,這是傳播學(xué)研究的傳統(tǒng)論述,那么數(shù)字媒體的產(chǎn)生給傳統(tǒng)的信息、傳播和行為理論帶來了哪些沖擊?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信息即差異
(一)包含意義的信息
信息概念的提出對于媒介與傳播研究而言具有非凡的影響,它直接解決了媒介傳播什么的問題。1948年,數(shù)學(xué)家香農(nóng)提出關(guān)于信息的定義,即“信息是用來消除隨機不確定性的東西”。這一定義被廣泛應(yīng)用于各個學(xué)科領(lǐng)域。但是對于傳播研究而言,媒介的作用到底是傳遞信息還是傳播意義?從產(chǎn)生效果與指導(dǎo)行為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后者。香農(nóng)的定義似乎沒有將意義的觀點包含在信息的概念之中。例如以聲音符號為介質(zhì)的口語傳播,人們面對面進行交流,不單是為了聽取這一系列的聲音符號,獲得感官的刺激,更重要的是為了認識這些符號背后的意義,從而指導(dǎo)行為。所以信息不僅包含符號,更應(yīng)該包含意義。
在此論述基礎(chǔ)上,我們可以從實用主義角度去理解信息。經(jīng)典的實用主義很早就預(yù)言了關(guān)于信息的最新定義,即信息是產(chǎn)生影響與變化的差異①。這種差異不僅包含了作為信息形式的符號,更包含了關(guān)于信息的意義。這類似于索緒爾提出的“二元符號理論”。他認為每一種符號都具有“能指”和“所指”兩方面含義,能指為所指代的物質(zhì)實在的符號形式,而所指是指這個符號所代表的意涵。索緒爾的能指和所指不僅體現(xiàn)出符號對于物質(zhì)實在象征的表達,更將視角放在符號所指代的物質(zhì)實在的具體意義上,并且這種能指與所指在索緒爾看來是隨機組合的,即符號具有任意性和不確定性,符號和它表達的意涵之間的關(guān)系沒有內(nèi)在與自然的聯(lián)系。這就將信息從物質(zhì)層面引向了精神層面,對于信息的生產(chǎn)者而言,無論是以宣傳為目的的信息還是作為普通交流的信息,其本身都是更加關(guān)注“內(nèi)容”,而非作為意涵形式的符號。
(二)從信息到行為
同時代的另一位符號學(xué)家皮爾士所提出的“三元符號論”則逐漸有取代“二元論”的傾向。皮爾士提出了一個廣延的符號闡釋過程,他認為這一過程包含了理解、認知和行為符號類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符號體系。皮爾士沒有將聚焦點完全放在符號本身及其意涵上,而是放在作為“實踐”的詮釋符號及其產(chǎn)生的效果上。在皮爾士的觀點中,符號的詮釋連接了主體與客體,并且這種詮釋包含著主體自身的經(jīng)驗。皮爾士引入了“解釋項”(符號的闡釋過程)這一概念來表示詮釋過的符號,這就使得主體不是對符號本身進行詮釋,而是對符號的“解釋項”進行詮釋,這一詮釋過程也可以看作是意義的再生產(chǎn)過程,而“差異”已經(jīng)包含在多次的詮釋活動之中。后結(jié)構(gòu)主義哲學(xué)家德里達對“差異”的內(nèi)涵進行了重構(gòu),并且創(chuàng)造出了“分延”的概念,即差異的實現(xiàn)或發(fā)生②。他將時間維度納入概念之中,強調(diào)實現(xiàn)的過程同時也是差異作用的時間延緩和時間積蓄。這個論述與皮爾士的三元符號論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他們都強調(diào)了符號產(chǎn)生的實踐行為,或者具體為讀者對于符號的解釋所產(chǎn)生的“效果”。意義使得符號之間存在一種差異,字母的排列順序使得每個單詞都具有各自意思,同時對于符號的詮釋行為也因為不同的語境與認知條件而產(chǎn)生差異。這種從認知到行為層面的上升不僅為哲學(xué)發(fā)展帶來轉(zhuǎn)向,也為媒介與傳播研究帶來新的視角。
(三)數(shù)字媒介對差異的傳播
“差異”的傳播自媒介誕生之日起就存在,口語傳播的“差異”產(chǎn)生于人際交往中,以聲音這種單一符號為內(nèi)容的面對面交流限制了意義的外延,從而形成了有限制的“差異”。以模擬信號復(fù)制技術(shù)為支撐的大眾傳媒促使了符號形態(tài)的多樣化,尤其是電視媒介的影像符號形態(tài),在塑造場景化和加深感染力方面超越了之前的任何媒介。場景化增加了信息內(nèi)容,而這也進一步加深了受眾詮釋符號所帶來的“差異”。以電視機為對象進行的效果研究一直是媒介與傳播領(lǐng)域的熱門,但是電視機仍然沒有擺脫之前媒介符號形態(tài)單一化的缺陷。雖然電視機在產(chǎn)生差異上遠遠超過報紙、廣播,但仍被看作是有缺陷的大眾媒介。
從第一臺計算機誕生到如今智能手機普及,數(shù)字媒介的發(fā)展不僅克服了之前大眾媒介符號形態(tài)單一的缺陷,其引以為傲的互動傳播形式還徹底將自己與傳統(tǒng)大眾媒介分隔開來。以比特(bit)為單位的數(shù)字媒介融合了過往多種符號形態(tài),使得文字、圖片、聲音和視頻匯聚于同一媒介平臺,并且融于同一文本之中,通過相互組合來實現(xiàn)對于現(xiàn)實的表征。而這種形態(tài)的隨機組合性也增加了詮釋行為的不確定性,從而加深了“差異”的程度。同時,數(shù)字媒介的傳播速度與便攜性大大超越了傳統(tǒng)的大眾媒介,各種信息的實時更新也加大了用戶對周圍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用戶渴望通過傳播從媒介營造的“差異”中獲得共識,他們不停地對接收到的信息進行詮釋,但是這種行為往往又造成了新的“差異”,使用戶處于充滿“差異”的社會中。數(shù)字媒介的互動性特點改變了受眾被動接受信息的地位,使傳受雙方朝著平等化方向發(fā)展。去中心化的傳播形式使意義的詮釋逐步多元化,用戶每一次的接收、編輯和再次發(fā)送都是“差異”的生產(chǎn),這種差異中也必然包含著新的意義與影響。差異的裂變級增長也對信息的傳輸模式帶來了挑戰(zhàn)。
二、傳播:超越5W
(一)傳播的傳輸觀
1948年,美國學(xué)者拉斯韋爾在《傳播的過程與模式》中提出了著名的“5W”模式,他將傳播的過程定義為:誰(who),說了什么(say 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說(to whom),產(chǎn)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這一模式同時也奠定了傳播研究的五個領(lǐng)域,并且成為美國主流媒介與傳播研究的基礎(chǔ)。雖然這一模式有明顯的缺陷,即缺乏必要的反饋渠道,后來的學(xué)者也對傳播模式進行了探究,但無論是施拉姆-奧古斯德模式,還是香農(nóng)韋弗的數(shù)學(xué)模式,以及之后出現(xiàn)的“兩極傳播”甚至多級“傳播”模式,都無法跳脫出“5W”的影響。美國學(xué)者詹姆斯·凱瑞把這些模式統(tǒng)稱為傳播的傳遞觀。
以“5W”模式為代表的傳播的傳遞觀展現(xiàn)了信息從傳播者抵達受眾的過程。這一過程清晰地體現(xiàn)了信息的流動軌跡,單向的傳播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自上而下的命令傳遞,詹姆斯·凱瑞認為傳遞觀中傳播一詞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擴展信息③。傳播者作為信息生產(chǎn)者有權(quán)利決定傳播什么內(nèi)容或者差異,這極大地限制了受眾對于差異內(nèi)容的想象。對于傳播者而言,其目的就是為了傳播而進行傳播,就是傳播信息而非作為行為的“差異”。雖然拉斯韋爾加入了“效果”這一環(huán)節(jié),但這一效果更多關(guān)注到受眾心理層面的變動,而無法指代實踐層面的具體行為。對于效果本身的研究也證明了這個觀點,基于有限效果論的理論,無論是諾依曼的“沉默的螺旋”還是戴維森的“第三人效果”,都是從社會心理學(xué)角度入手研究的。這種經(jīng)由大眾媒介帶來的信息僅僅給予受眾一個對或錯、是或否的簡單判斷并不能體現(xiàn)作為行為的“差異”,并且有時這種效果也并未對受眾的心理層面帶來任何實質(zhì)性的影響。正如延森的論述:“傳輸模式的隱喻之一是,某種程度上而言,媒介是與社會相互分離的機制——它是積極目的與消極目的的實現(xiàn)方式;媒介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④。在延森的觀點中,傳輸模式更多把媒介作為一種社會信息流通的工具,是一種以將信息傳達到受眾為目的的工具。這也與大眾媒介自身的傳播單向性有關(guān)聯(lián),而由此引申出來的傳播背后的控制問題歷來也是媒介與傳播研究的主流。
(二)詹姆斯·凱瑞的儀式觀
以“5W”為代表的傳播模式,是拉斯韋爾根據(jù)二戰(zhàn)中廣播這一大眾媒介的宣傳研究而得出的結(jié)論。盡管該模式與大眾媒介不謀而合,但是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讓人們不禁質(zhì)疑,這種傳播模式在數(shù)字媒介時代是否還具有與大眾媒介時代可媲美的強大生命力。如果沒有,那么應(yīng)該用什么樣的模式來描述數(shù)字媒介的信息傳播?詹姆斯·凱瑞在其著作中引述約翰·杜威對傳播的評價:“社會不僅因傳遞(transmission)與傳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確切地說,它就存在于傳遞與傳播中”⑤。杜威將社會置于傳播中,社會不僅發(fā)布信息,其本身正是靠傳播與交流才得以形成,傳播不再是社會信息流通的中介工具,而是有成為社會組成部分的傾向。在此基礎(chǔ)上,凱瑞定義了傳播的兩大類別——傳播的傳輸觀(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并對這兩大類加以區(qū)別。傳播的傳輸觀一直以來都是媒介與傳播研究的主流,數(shù)字媒介獨特的超越時空的互動性使我們可以將視角轉(zhuǎn)向“儀式觀”。詹姆斯·凱瑞從古代宗教儀式中受到啟發(fā),認為這些宗教活動并不僅僅為了說教與傳道,而是更看重祈禱者、圣歌的外在形式,這也進一步闡述了儀式觀所表達的分享與參與的意涵。傳播的儀式觀并不在于信息的獲取,而在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在這種戲劇行為中,讀者作為戲劇演出的旁觀者加入了這一權(quán)利紛爭的世界⑥。很顯然,凱瑞的這段論述將讀者(受眾)的行為也作為傳播的一部分,這不僅彌補了傳輸缺乏互動的缺陷,也強調(diào)了信息“差異”所帶來的實踐行為——分享。這種分享類似于S.霍爾提出的編碼——解碼理論,分享實質(zhì)上是一種解碼與再次編碼的過程,同時這種再次編碼將“差異”包含其中。處于社會中的用戶正是通過無數(shù)次的編碼與解碼將社會構(gòu)筑于傳播網(wǎng)絡(luò)中。凱瑞的儀式觀于上世紀70年代末提出,而這個時期正是傳播效果研究的輝煌時期,再加上儀式觀對于大眾媒介的闡述遠遠比傳輸觀更為抽象,造成了儀式觀在兩種觀念的對立爭斗中毫無優(yōu)勢,但是數(shù)字媒介的出現(xiàn)讓人們重新審視這種被學(xué)界冷落的理論。
(三)數(shù)字媒介塑造的信息論壇
數(shù)字媒介的出現(xiàn)使受眾不只是對信息進行單純的接收,而且讓受眾也參與到了信息的生產(chǎn)中,這與凱瑞在儀式觀理論中反復(fù)強調(diào)受眾的“分享”(sharing)與“參與”(participation)不謀而合。正是交流雙方高頻率的信息生產(chǎn)與傳遞才形成了“分享”,而數(shù)字媒介恰恰為這一過程提供了物質(zhì)條件。我們把現(xiàn)實中的交流移植于虛擬的網(wǎng)絡(luò)空間,現(xiàn)實的交談需要一個特定的場景,網(wǎng)絡(luò)中的虛擬交流也同樣需要一個場所,就如同宗教活動需要在教堂中進行一般。當(dāng)下,數(shù)字媒介不僅僅成為信息傳播的工具,更是意見匯集的集中地。各種意見觀點的匯集將數(shù)字媒介塑造成如論壇一般,這個論壇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空間的塑造不再依賴于物質(zhì)條件,而依賴于作為信息生產(chǎn)者的用戶,當(dāng)人們想發(fā)表觀點或意見時,無論身處何地,只要通過數(shù)字媒介發(fā)送信息,這一論壇就能存在。同樣,這一論壇也超越了時間限制,數(shù)字媒介的存儲功能使觀點和意見得以保存下來。論壇同樣被用戶塑造,用戶完全占領(lǐng)了信息生產(chǎn)的主導(dǎo)權(quán),這也部分得益于作為傳播行為的“分享”。
三、傳播與行為
(一)作為傳播的行為
分享和參與的傳播過程使我們把視角轉(zhuǎn)向傳播行為。我們不禁會思考這種“分享”是如何發(fā)生的,或者說用戶通過什么樣的操作實現(xiàn)了分享和參與。延森認為,行為通常被認為引發(fā)了(input to)傳播,或者是傳播過程的產(chǎn)物⑦。他通過闡釋傳播與行為的關(guān)系,致力于將行為置于理論發(fā)展的中心。通過對媒介技術(shù)史的回顧不難看出,新媒介技術(shù)的出現(xiàn)往往會引發(fā)傳播行為的改變,數(shù)字媒介使信息的傳播更加依賴于行為。過往的大眾傳播行為僅限于傳播者一端,無論是口語表達、書寫、拍攝還是剪輯,都帶有一定的目的,力圖去表達現(xiàn)實世界的行為。數(shù)字媒介的出現(xiàn)使這種行為變?yōu)槿巳怂鶕碛械模⑶颐浇檫€賦予了行為本身獨特的含義。如果說數(shù)字媒介包含了過往一切媒介的符號形態(tài),那么它也必將包含過往一切媒介的符號生產(chǎn)方式,我們可以將這種行為的集合統(tǒng)稱為“交互”。通過闡述交互性的概念,可以考察用戶如何使用數(shù)字媒介來完成對于現(xiàn)實的表征,并且這種行為又如何對現(xiàn)實世界產(chǎn)生影響。
(二)人機交互
交互性一詞起源于計算機的誕生,指技術(shù)人員對電腦程序進行檢查后,通過一系列操作對程序進行修改。而數(shù)字媒介的交互性,通常指用戶通過程序化方式操作媒介,對一系列預(yù)設(shè)選項的持續(xù)操作,這其中包含著用戶的主動性。在大眾媒介時代,受眾也會有一些對于媒介的操作,比如收音機和電視機的頻道切換,但是無論怎樣切換頻道,受眾依舊處于傳播的末端,其行為也未對其他受眾產(chǎn)生任何影響。數(shù)字媒介的交互性具有更大的復(fù)雜性和支配性。以手機為例,初代手機的按鍵讓人們可以隨意編輯消息,并且將消息發(fā)送給其他用戶。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用戶僅僅通過一塊顯示屏就可以完成交互,在聊天框里輸入信息,點擊超鏈接或者在游戲中完成一系列動作等。人與機器之間產(chǎn)生了緊密的聯(lián)系,用戶在網(wǎng)絡(luò)營造的虛擬空間中通過媒介操作實現(xiàn)自我的自由。不僅如此,數(shù)字媒介的人機交互背后其實隱藏著社會間的協(xié)商與談?wù)摗?/p>
(三)社會交互
在探討人機交互如何達成社會交互之前,我們可以回顧吉登斯關(guān)于交互引入的兩個概念——能動和結(jié)構(gòu)。吉登斯認為無數(shù)的個體構(gòu)成了社會,在網(wǎng)絡(luò)上同樣如此,人們通過人機交互展開跨越時空的交流從而達到社會互動,使得用戶的個人行為逐漸成為具有社會性的整體行為。口語時代的面對面交流也可以稱作社會交互,人們表達信息,接收他人信息,從而達到修改自己觀點的目的,這其中也包含著社會結(jié)構(gòu)層面的互動。眾所周知,數(shù)字媒介囊括了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兩種過往的傳播形式,并且史無前例地實現(xiàn)了去中心化的網(wǎng)絡(luò)傳播。而網(wǎng)絡(luò)傳播正是通過一次次的人際傳播編制而成。人們通過人機交互,將包含差異的信息散播出去,與他人包含差異的信息進行碰撞,從而在反復(fù)的修改中達到共識。無論是經(jīng)濟、政治還是文化層面的沖突,都可以通過人機的超時空交互達到平衡,從而達成社會結(jié)構(gòu)的穩(wěn)定。
四、結(jié)語
從印刷媒介誕生到新聞理論體系的確立經(jīng)歷了大約400年的時間,數(shù)字媒介這一新生事物在對現(xiàn)有的媒介傳播理論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為學(xué)科范式重構(gòu)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而要想真正了解數(shù)字媒介,不僅應(yīng)該立足于媒介特點,更應(yīng)該回溯傳播理論的源頭,從而更好地開辟一條適合數(shù)字媒介發(fā)展的理論道路,讓數(shù)字媒介能真正服務(wù)于人。
注釋:
①④⑦[丹麥]克勞斯·布魯恩·延森.媒介融合:網(wǎng)絡(luò)傳播、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三重維度[M].劉君 譯.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8:44,54,55.
②[法]雅克·德里達.聲音與現(xiàn)象[M].杜小真 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85.
③⑤⑥[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M].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