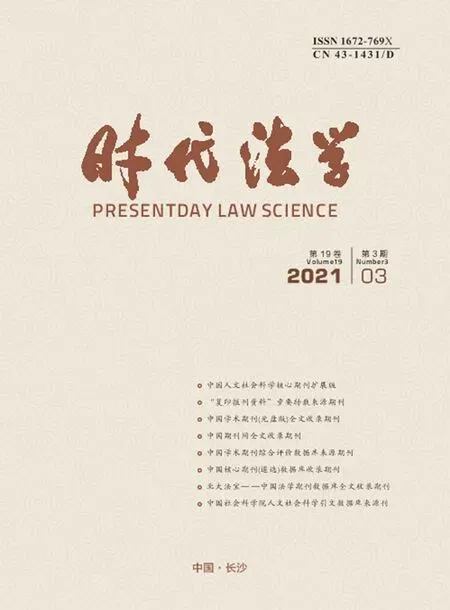專屬經(jīng)濟區(qū)海洋科學研究與測量活動的國際法分析*
余敏友,周昱圻
(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引言
海洋科學研究非常重要,人類生存和發(fā)展日益依賴海洋,合理利用海洋資源、保護海洋環(huán)境都與海洋科學研究密切相關(1)Alfred H. A. Soons,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Law of the Sea, Kluwer Law Press, 1982, pp.11-15.。海洋科學研究的重要性還體現(xiàn)在:一方面,人類對于海洋的認識遠遠不夠,海洋科學研究是人類認知海洋、獲取知識的重要來源;另一方面,海洋科學研究是人類進一步開發(fā)利用海洋資源的基礎實踐,有助于人類解決陸上問題(2)ZOU Keyuan, Govern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34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 1(2003).。國家開發(fā)自然資源的能力與海洋科技水平密不可分,海洋科技水平也一度對于其所主張的大陸架(3)《大陸架公約》第1條規(guī)定:“本條款稱‘大陸架’者謂:(a)鄰接海岸但在領海以外之海底區(qū)域之海床及底土,其上海水深度不逾二百公尺,或雖逾此限度而其上海水深度仍使該區(qū)域天然資源有開發(fā)之可能性者;(b)鄰接島嶼海岸之類似海底區(qū)域之海床及底土。”第5條第8款規(guī)定:“對大陸架從事實地研究必須征得沿海國同意。倘有適當機構提出請求而目的系在對大陸架之物理或生物特征作純科學研究者,沿海國通常不得拒予同意,但沿海國有意時,有權加入或參與研究,研究之結果不論在何情形下均應發(fā)表。”有著非常重大的關系。
現(xiàn)代意義的海洋科學研究始于1872年至1876年英國海軍“挑戰(zhàn)者號”(the H.M.S Challenger)科學家在航行中對海底與水體進行取樣研究(4)Satya N. Nandan, Introduction to Office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 Guid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1991), at vii.。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第一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開啟了國際條約規(guī)范海洋科學研究行為的征程(5)U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The Law of the Sea: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A Revised Guid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2010), para.1。1958年《大陸架公約》確定了沿海國對大陸架上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享有管轄權(6)1958年第一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并未形成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彼時“領海之外即公海”,沿海國依據(jù)1958年《大陸架公約》可以對領海之外的海床底土主張權利。1982年第三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創(chuàng)設出了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將領海之外的一定范圍內水域作為沿海國可以主張的專屬經(jīng)濟區(qū)。一般情況下,大陸架和專屬經(jīng)濟區(qū)的關系是海床底土和上覆水域的關系。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存在高度爭議的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測量活動與海洋科學研究。。第三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通過的《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第十三部分專門規(guī)定了海洋科學研究制度。《公約》由于沒有明確界定“海洋科學研究”,易于引發(fā)如何具體規(guī)范科研/測量活動的爭議。
實踐中,各國由于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軍事測量活動、情報收集活動而產生的爭議屢見不鮮。從EP-3型偵察機撞擊事件,到鮑迪奇號事件、斯科特號事件、無暇號事件,美國一直在挑戰(zhàn)所謂的他國“過度海洋主張”(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受挑戰(zhàn)的沿海國主張測量活動和情報收集活動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的范疇(7)See ZHANG Haiwen, Is It Safeguard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r Maritime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 Comments on Raul (Pete) Pedrozo’s Article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 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1, 36, 38 (2010); Sam Bateman, A Response to Pedrozo: The Wider Utility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10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77, 179 (2011); XUE Guifa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ydrographic Survey in the EEZs: Closing up the Legal Loopholes?, in: Myron H. Nordquist, Tommy T. B. Koh& John Norton Moore (eds.), Freedom of Seas, Passage Rights and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2009), 205-225; S. Kopela, The ‘territorialisation’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mplications for maritime jurisdiction, 6, available at: https://www.dur.ac.uk/resources/ibru/conferences/sos/s_kopela_paper.pdf.,外國在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進行此類活動須征得該沿海國同意。美國認為,從《公約》第19條、第40條等條款看來,測量活動是明顯與海洋科學研究并列的活動,屬于《公約》第58條“其他國際合法用途”的范圍。美國自1979年推行“航行自由計劃”以來,派遣軍艦、軍機進入其他沿海國專屬經(jīng)濟區(qū)活動,挑戰(zhàn)沿海國的海洋主張(8)余敏友,馮潔菡.美國“航行自由計劃”的國際法批判[J].邊界與海洋研究,2020,(4):6-31.。因此,厘清海洋科學研究的概念、確定其內涵對于明確海洋權利及義務非常重要。
一、海洋科學研究的定義及內涵
雖然第三次海洋法會議討論過海洋科學研究的界定問題,也曾有過幾個版本定義條款(9)UNDOALOS, above n.5, pp.4-6.,但是《公約》最終沒有對海洋科學研究一個明確的界定。許多國際法學者試圖從學理上對這一概念予以定義,并分析其內涵,但分歧較大。實踐中,水文測量(hydrographic survey)、軍事測量(military survey)和軍事信息收集(military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等與海洋科學研究緊密相關的活動,是否應該屬于《公約》第十三部分海洋科學研究的范疇,從而接受沿海國的管理與規(guī)范,也存在爭議。
首先,對于海洋科學研究的定義,主要分歧聚焦于海洋科學研究的目的,即是否須以增進人類對于海洋環(huán)境的知識為目的,海洋科學研究是否包括基礎性海洋科學研究與應用性海洋科學研究。部分國際法學者認為(10)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Martinus Nijhoff Press, 2012, p.414; Raul (Pete) Pedrozo, Preserving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The Right to Conduct Military Activities in Chin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 21 (2010).,海洋科學研究須以增進人類的科學知識為目的,從而將海洋科學研究限縮在一個比較小的范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來自美國海軍軍官學院的Roach和Smith(11)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p.413-414.,他們認為海洋科學研究是隸屬于海洋數(shù)據(jù)收集(marine data collection)的下位概念。他們通過對于海洋數(shù)據(jù)收集體系的構建,將海洋科學研究與測量活動(包括水文測量與軍事測量)并列。由此一來,測量活動不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的范疇,因而通過主張《公約》第58條第一款的“其他國際合法用途”,將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測量活動認定為不受沿海國規(guī)范的海洋自由。也有部分國際法學者認為(12)R. R. Churchill & A. 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00; P. K. Mukherjee, The consent regime of oceanic research i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5 Marine Policy 98, 99-100 (1981); 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p.6-7;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433-434.,海洋科學研究應該是廣義的概念,包括了基礎性海洋科學研究與應用性海洋科學研究。宋斯(Soons)將海洋科學研究定義為:“以海洋環(huán)境為對象的任何調查,不論其以何種方式在何地進行”(13)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124.。他認為海洋科學研究分為基礎性海洋科學研究與應用性海洋科學研究,前者專指為增進知識而進行的研究活動。持此類觀點的人中,又可以是否將水文測量和軍事測量并入海洋科學研究作區(qū)分。
以Mukherjee為代表的學者主張將測量活動并入海洋科學研究。他認為海洋科學研究包括三大類:基礎性海洋科學研究、應用性海洋科學研究、軍事研究。他將基礎性海洋科學研究細分為五類:海洋物理學研究、海洋化學研究、海洋生物學研究、海洋地質和地球物理研究以及水文測量(14)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9-100.。與之相對應的,以宋斯為代表的學者不主張測量活動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理由主要是基于《公約》上下文(context)的考慮,認為海洋科學研究應與測量活動(水文測量)并列(15)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p.124-125.。他還認為水文測量符合《公約》第58條第一款的“其他國際合法用途”,因而不受沿海國的規(guī)范(16)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157.。
同時,部分學者認為測量活動的產出(主要指其收集到的數(shù)據(jù)信息)有經(jīng)濟價值(17)Sam Bateman, Hydrographic surveying in the EEZ: differences and overlaps with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29 Marine Policy 163, 169(2005); Moritaka Hayashi,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 in the EEZ: definition of key terms, 29 Marine Policy 123, 131(2005).。水文測量對于沿海國管理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直接影響沿海國對于專屬經(jīng)濟區(qū)的勘探與開發(fā),以及沿海國對于專屬經(jīng)濟區(qū)海洋環(huán)境的保護(18)Sam Bateman, above n.7, 180-181.。因此,Bateman提出沿海國可以規(guī)范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測量活動,其理由不是基于測量活動可以歸屬于海洋科學研究,而是因測量活動伴隨的經(jīng)濟價值(19)Sam Bateman, above n.7, 180-181; Sam Bateman, above n.17, 172.。盡管美國學者也承認水文測量對于沿海國的經(jīng)濟價值與環(huán)境保護重要性(20)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16.,但是他們仍然認為測量活動應屬海洋自由,而非沿海國的管轄范圍。
盡管《公約》未直接將海洋科學研究分為基礎性與應用性,但結合現(xiàn)代國際海洋法的發(fā)展歷史,基礎性/應用性海洋科學研究的概念從1958年《大陸架公約》開設就得到了體現(xiàn)(21)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Article 5, 499 UNTS 312; 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8-100, 102.,在第二、三次海洋法會議中也得到了充分討論。第二次海洋法會議中,加拿大提出“海洋科學研究應定義為:旨在增加海洋環(huán)境知識,包括海洋資源和生物,并包括所有相關科學活動的任何基礎或應用研究。”(22)UN Doc A/AC.138/SC.III/L.18 (Canada), Preamble, para. 2, and principle 2.第三次海洋法會議期間,關于海洋科學研究定義的提案從1973至1976年一直不斷。英美學者所廣泛援引的定義就出自1975年非正式單一協(xié)商案文(ISNT)中的“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means any study or related experimental work designed to increase man’s knowledge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23)UNCLOS III, Informal Single Negotiating Text (ISNT), Part III, MSR Part, Article 1.。1977年非正式綜合協(xié)商案文(ICNT)與《公約》,沒有海洋科學研究的定義,在此需要探討《公約》是否已經(jīng)將海洋科學研究限定在基礎性海洋科學的范圍之內。
《公約》第246條第三款明確了“在正常情形下,沿海國應對其他國家或各主管國際組織按照本公約專為和平目的和為了增進海洋環(huán)境的科學知識以謀全人類利益,而在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或大陸架上進行的海洋科學研究計劃,給予同意。為此目的,沿海國應制定規(guī)則和程序,確保不致不合理推遲或拒絕給予同意。”這一條款被普遍認為是對于基礎性海洋科學研究的規(guī)定(24)P. K. Mukherjee, above n.12, 102.。根據(jù)《公約》第246條,對于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沿海國應該采取有限同意制度(qualified consent regime)(25)P. K. Mukherjee, above n.12, 104.,同意合格的研究國家在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進行基礎性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依據(jù)《公約》的上下文解釋:首先,根據(jù)《公約》第246條第一款、第二款,沿海國有權管轄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在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應該得到沿海國同意,且沿海國應同意研究國家進行基礎性海洋科學研究。其次,根據(jù)《公約》第246條第五款,沿海國有權拒絕同意對涉及該款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該條款便包含了與資源勘探開發(fā)相關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可見,《公約》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不僅包括純粹基礎性科學研究活動,也包括與資源勘探開發(fā)有關的應用性科學研究活動(《公約》第246條第五款)。
因此,《公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應該是有廣泛內涵的活動,而不是美國學者主張的純知識性研究活動。Soons、Churchill、Tanaka等人認為海洋科學研究應被定義為“以海洋環(huán)境為對象的任何調查,不論其以何種方式、在何地進行”,更符合《公約》的目的與宗旨。 Mukherjee認為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本質都是一樣的,區(qū)別只在于目的、動機,因此他在廣義的“海洋科學研究”之下進一步區(qū)分,其中,水文測量和軍事研究都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的范疇(26)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8-100.。但在實踐中,測量活動與海洋科學研究活動的關系一直是爭議的熱點。還需要進一步厘清兩者之間的關系,對海洋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清晰的界定。
二、海洋科學研究與測量活動辨析
海洋科學研究與測量活動之間是否實質一致、逐漸趨同(27)ZHANG Haiwen, above n.7, 36; Sam Bateman, above n.7, 179-180.,還是存在明顯差異以致互斥排他(28)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14, 21-22;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p.414-416.,抑或存在某種程度的重疊(29)Sam Bateman, above n.17, 172.。下文先分析水文測量與海洋科學研究的關系,而后分析軍事測量與海洋科學研究的關系。
(一)海洋科學研究與水文測量的關系
水文測量與海洋科學研究的關系,無外乎兩種觀點:第一,對立互斥,持這種觀點以英美國家學者居多,他們認為水文測量活動應是“為航行安全及制作航海圖而進行的信息獲取活動”(30)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1-22;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16.,而海洋科學研究以增進海洋科學知識為目的,兩者目的不同,因此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行為。第二,實質一致且逐漸趨同。Bateman在2005年主張,雖然兩者使用的方式方法存在重疊,但水文測量和海洋科學研究是可以做區(qū)分的不同行為(31)Sam Bateman, above n.17, 168.,2011年他卻認為這兩類活動不斷趨同難以區(qū)分(32)Sam Bateman, above n.7, 180-181.。部分國際組織如國際海道測量局(IHB)也支持其觀點。下文進一步分析這兩種觀點。
能否進行以航行安全為目的海洋科學研究?正如美國學者所述,海洋科學研究目的不同于水文測量活動。后者以航行安全為目的,而前者并非如此,能否進行以航行安全為目的海洋科學研究是關鍵。Churchill與Lowe認為,海洋科學研究有各種各樣的目的(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serves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33)R. R. Churchill & A. V. Lowe, above n.12, p.400.,其中包括對波浪、洋流、海床和天氣的研究,以便使航行更加安全(34)R. R. Churchill & A. V. Lowe, above n.12, p.400.。聯(lián)合國海洋事務與海洋法司制定的《海洋科學研究指南》(2010)認為,海洋科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促進航海事業(yè)進一步發(fā)展(35)UNDOALOS, above n.5, para. 9.。認為海洋科學研究不包括以航行安全為目的研究活動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海洋科學研究活動的目的可以包括為航行安全利益,與水文測量的區(qū)別也不在于目的的不同。
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是否與水文測量活動實質一致且逐漸趨同?Bateman教授的主張有一定的說服力,但也存在明顯的問題。第一,他認為嚴格區(qū)分(水文)測量活動與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是對《公約》的過度解讀(36)Sam Bateman, above n.7, 179.。《公約》區(qū)別列舉海洋科學研究與測量活動,只是為了將此類活動一并作為被禁止活動或者需要獲得沿海國授權之活動。而且,這種區(qū)分只涉及通行制度而不涉及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37)Sam Bateman, above n.7, 179.。然而,這只是可能性,畢竟《公約》談判過程沒有特別聚焦水文測量活動(38)Sam Bateman, above n.17, 165.,從而體現(xiàn)其與海洋科學研究之不同。因此,很難說Bateman教授的主張有足夠的理據(jù)。第二,Bateman列舉了相關國際組織專家意見,認為區(qū)分海洋科學研究與水文測量非常困難(39)Sam Bateman, above n.7, 181.,2005年他主張雖然可能存在手段重疊,但這兩種活動仍是可分而非不可區(qū)分的(40)Sam Bateman, above n.17, 168.。他的主張自相矛盾,水文測量活動是否區(qū)分于海洋科學研究,難以定論。因此,水文測量與海洋科學研究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分析。
首先,需要從溯源的角度對水文測量與海洋科學研究進行分析。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局(NOAA)認定第一次水文測量是在1843年(41)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 (NOAA), History of Hydrographic Surveying, available at https://nauticalcharts.noaa.gov/learn/history-of-hydrographic-surveying.html.。這個時間早于英國“挑戰(zhàn)者號”進行的世界范圍內第一次海洋科學研究的時間(1872年),水文測量明顯早于海洋科學研究,從源頭上來說,兩者并不是同一個行為。其次,需要從采取的方式方法分析海洋科學研究與水文測量。水文測量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沿線測量、線拖測量、回聲測量與多波束聲吶技術四個階段(42)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 (NOAA), History of Hydrographic Surveying, available at https://nauticalcharts.noaa.gov/learn/history-of-hydrographic-surveying.html.。目前水文測量主要采用的聲學探測方式與海洋科學研究是一致的(43)Sam Bateman, above n.17, 166.,國外學者也普遍承認海洋科學研究與水文測量使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44)Sam Bateman, above n.17, 166;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50; 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2.。最后,《公約》第19條、第21條及第54條等,將(水文)測量活動與海洋科學研究活動并列。這也是英美學者大多主張水文測量活動不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的主要依據(jù)之一(45)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11.,這點不容忽視,也難以推翻。即使Bateman主張這是對于《公約》的過度解讀,也不能直接認定這兩類行為完全一致,從而輕易地將水文測量納入《公約》第十三部分的管轄范圍。
綜上,水文測量與海洋科學研究是不同的兩類活動,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手段、方式,也可以有相同的目的——均以航行安全利益為目的。如前所述,海洋科學研究是一個廣義概念,即“以海洋環(huán)境為對象的任何調查,不論其以何種方式、在何地進行”。由此,很可能存在既符合海洋科學研究又符合水文測量的活動。《公約》第19條、第21條等以通行權為依據(jù),從而對無害通過及過境通行予以認定,而不是以船舶類型為依據(jù)。在這樣的上下文(context)中,《公約》調整的是具體的行為活動,如果僅以概念不同進行區(qū)別,將水文測量活動與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之交集排除在《公約》第十三部分之外,從而主張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測量自由,是不符合《公約》的,甚至會導致海洋科學研究制度的瓦解(46)See XUE Guifang, above n.7, p.222.。因此,如果相關的活動既符合海洋科學研究,又符合水文測量,那么理應屬于《公約》第十三部分的范圍,從而受到沿海國的規(guī)范。
(二)海洋科學研究與軍事測量的關系
《公約》沒有明確提及軍事測量活動(47)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37.,且其概念非常模糊(48)Sam Bateman, above n.17, 172-173.。根據(jù)《公約》第19條與第21條關于無害通過的規(guī)定,第19條所指的“測量活動”直接指向了第21條的“水文測量”。水文測量是《公約》締約過程中討論較少的議題,軍事測量這一概念都不在《公約》商議范圍之中。軍事測量是“在領海、群島水域、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公海以及大陸架,為軍事目的而進行的海洋數(shù)據(jù)收集活動”(49)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17.。
軍事測量包括海洋學、水文、海洋地質、地球物理、化學、生物、聲學等相關數(shù)據(jù)(50)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417.。從軍事測量范圍可以看出,與公認的海洋科學研究范圍(51)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6; 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9-100;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p.414-415.具有高度一致性。后者同樣包括海洋物理學、海洋化學、海洋生物學、海洋地質和地球物理研究。因此,在中美關于軍事測量的爭端中,美方主張軍事測量是伴隨軍事目的的測量行為,因此不同于海洋科學研究(52)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2.。國內學者(53)ZHANG Haiwen, above n.7, 36;鄭雷.論中國對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他國軍事活動的法律立場——以“無瑕號”事件為視[J].法學家,2011,(1):143;管建強.美國無權擅自在中國專屬經(jīng)濟區(qū)進行“軍事測量” ——評“中美南海摩擦事件”[J].法學,2009,(4):55;楊瑛.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與軍事活動的法律分析[J].社會科學輯刊,2017,(5):123-124;萬彬華.論專屬經(jīng)濟區(qū)“海洋科學研究”和“軍事測量” 的法律問題[J].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07,(5):59;宋云霞.海洋科學研究法律制度解析[J].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11,(2):75-76;鄒立剛,王崇敏.國家對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外國科研活動的管轄權[J].社會科學家,2012,(11):14-15.則普遍認為軍事測量活動與海洋科學研究沒有本質區(qū)別,因此軍事測量活動應該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的范疇。通過分析軍事測量與海洋科學研究所采取的手段與技術,這些學者主張,兩者并無本質不同,而差異僅在于進行海洋科學研究/軍事測量的目的,存在區(qū)分不能的情況,應該將軍事測量活動納入海洋科學研究之中。
首先,軍事測量活動概念極其模糊,不易識別(54)Sam Bateman, above n.17, 173.。英美學者的軍事測量活動/軍事數(shù)據(jù)收集活動(Military Data Gathering)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即一切以軍事為目的的海洋數(shù)據(jù)收集活動。在此基礎上,軍事測量活動不僅區(qū)別于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也區(qū)別于水文測量活動。然而,水文測量活動本身就可以包括兩類,一類是國家主導的,可以用于軍事的水文測量;另一類則是國防之外的民間機構如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局(NOAA)主導的水文測量。前者正是軍事測量所覆蓋的范圍,屬于兩種測量活動的交集。海洋科學研究活動作為一個開放的概念,并不必然不能以軍事為其目的,軍事研究也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的范疇,與基礎性/應用性海洋科學研究相并列(55)P. K. Mukherjee, above n.12, 98-100.。因此,美國所主張的分類,人為地割裂了概念,并沒有很好地考慮到這幾類活動的本質特點。
其次,對于軍事測量來說,軍事活動應是其合適的上位概念。這也是爭議雙方共同承認的(56)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above n.10, pp.436-437; Zhang Haiwen, above n.7, 31-32.。需要考慮爭議相關的軍事測量是否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的范圍,以判斷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軍事測量活動是否應該受沿海國的規(guī)范。對于發(fā)生在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同時屬于海洋科學研究的軍事測量活動,沿海國享有管轄權。對于一些未必以海洋環(huán)境作為研究、數(shù)據(jù)收集對象的軍事活動,例如情報收集活動(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必須著重考慮其合法性問題。
三、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測量活動的合法性
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測量活動,包括水文測量與軍事測量(作為軍事活動的一種),其合法性是有爭議的(57)Proelss ed., United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C. H. Beck Press, 2017, p.453.。2002年至2009年先后發(fā)生了鮑迪奇號與無暇號事件,中美學界紛紛討論沿海國是否有權規(guī)范專屬經(jīng)濟區(qū)的測量活動(以軍事測量為主)。下文先分析兩類測量活動是否是符合《公約》第58條第一款之“其他合法用途”,再從《公約》第59條的角度探究兩類測量活動是否屬于剩余權利(residual right)的范疇。
(一)《公約》第58條第一款
《公約》第58條是英美等海洋大國主張測量活動自由的主要依據(jù)。英美等國主張《公約》提供了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測量活動的法律基礎,其主要依據(jù)是《公約》第58條第一款,即“在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所有國家,不論為沿海國或內陸國,在本公約有關規(guī)定的限制下,享有第87條所指的航行和飛越的自由,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以及與這些自由有關的海洋其他國際合法用途,諸如同船舶和飛機的操作及海底電纜和管道的使用有關的并符合公約其他規(guī)定的那些用途”。測量活動正屬于此種用途,是《公約》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賦予非沿海國的權利。為分析這一問題,下文先探討《公約》第58條第一款的解釋,再分析該規(guī)定對水文測量、軍事測量的適用。
首先,什么是《公約》第58條第一款中的“與這些自由有關的海洋其他國際合法用途”,如何認定測量活動是否與“航行和飛越的自由”有關。“其他國際合法用途”指的是“航行和飛越自由”所依賴的一些海上活動。《公約》列舉“諸如同船舶和飛機的操作以及…有關的并符合公約其他規(guī)定的那些用途”。正如宋斯指出的那樣,“一艘船(無論是否是研究船)在通行中為船舶航行安全而收集數(shù)據(jù)的行為 (如測深和風速和風向的觀察),不能被視為研究”(58)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149.,而應當被視為與船舶操作相關的正常活動(normal activities)(59)Alfred H. A. Soons, above n.1, p.149.。Bateman在此基礎上提出,這類行為既不能被認定為海洋科學研究,也不能被認定為測量活動(60)Sam Bateman, above n.17, p.165.。這兩位學者所指的正常活動正是《公約》第58條第一款的“與這些自由有關的海洋其他國際合法用途”。一方面,這類活動與航行、飛越自由有著直接的、緊密的聯(lián)系,可以認定其中的相關性聯(lián)系;另一方面,這類活動不構成海洋科學研究或測量活動,也就是說不存在沿海國可以規(guī)范這類正常活動的可能性,這類活動屬于沿海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之自由。與之相反,如果這類活動被認定為海洋科學研究或是測量活動,那么極有可能受到沿海國的規(guī)范,從而不能被《公約》第58條第一款所適用。盡管公約并沒有予以解釋,但這類“其他國際合法用途”應是一個小范圍的概念,不能擴大解釋。尤其是與沿海國主權性權利、管轄權相關的活動(61)See The M/V ‘Virginia G’ (Panama v. Guinea-Bissau), Merits, Judgment, ITLOS Case No. 19(2014), p.69, para. 217.,不宜認為是他國之自由。
其次,水文測量活動是否屬于《公約》第58條第一款所規(guī)定的“其他國際合法用途”?據(jù)前所述,如果水文測量作為一種數(shù)據(jù)收集活動,被視為宋斯所主張的在通行中為船舶航行安全所進行的那種數(shù)據(jù)收集行為,那么這類活動應被視為合法用途下的正常活動,水文測量卻是為航行安全及制作航海圖而進行的信息獲取活動。這類活動與船舶本身為航行所做的數(shù)據(jù)收集活動有明顯區(qū)別。因此,水文測量活動與“航行、飛越的自由”沒有足夠充分的相關性。他國難以直接依據(jù)《公約》第58條,在沿海國專屬經(jīng)濟區(qū)主張水文測量自由。另外,從國家實踐來說,目前15個以上國家要求進行水文測量活動之前須通知沿海國并獲得同意(62)Kopela, above n.7, 5.。中國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第8條規(guī)定:“外國的組織或者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從事測繪活動,應當經(jīng)國務院測繪地理信息主管部門會同軍隊測繪部門批準,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無論從學理上還是從國家實踐中,都難以認定水文測量就是符合《公約》第58條第一款的“其他國際合法用途“。水文測量是對海洋的合理、合法利用,然而這種合法用途并非《公約》賦予的不受沿海國規(guī)范的自由。因此,需要進一步考慮水文測量是否屬于《公約》第59條所規(guī)定的剩余權利的范疇。
最后,分析《公約》第58條第一款對軍事測量活動的適用。軍事測量活動被認為是軍事活動的一種,必須從軍事活動的角度考慮軍事測量是否屬于“其他國際合法用途”。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海洋軍事活動違反了和平原則,這項原則貫穿于《聯(lián)合國憲章》及《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聯(lián)合國憲章》第2條以及《公約》第88條、第301條都闡釋了這一原則。而在他國專屬經(jīng)濟區(qū)進行海洋軍事測量,以軍事用途為目的,旨在支持軍隊登陸及對沿海國作戰(zhàn),構成了對沿海國的威脅,不能視為和平利用海洋的合法用途(63)宿濤.試論《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和平規(guī)定對專屬經(jīng)濟區(qū)軍事活動的限制和影響[J].廈門大學法律評論,2003,(6):83;鄭雷.論中國對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他國軍事活動的法律立場——以“無瑕號”事件為視[J].法學家,2011,(1):144; 楊瑛.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與軍事活動的法律分析[J].社會科學輯刊,2017,(5):122;萬彬華.論專屬經(jīng)濟區(qū)“海洋科學研究”和“軍事測量” 的法律問題[J].西安政治學院學報,2007,(5):60-61;丁成耀.從國際法角度看美國測量船闖入中國專屬經(jīng)濟區(qū)事件[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3,(2):81.。美國學者Pedrozo則主張,《公約》并未禁止軍事活動,而只是禁止了“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活動。與中國學者的主張相反,《公約》第19條第二款明確列舉了一系列軍事活動。這意味著《公約》在區(qū)分軍事活動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64)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5.。因此,非侵略性軍事活動符合《聯(lián)合國憲章》與《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65)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5.。
軍事活動(包括軍事測量)是否違反了“和平目的”,不能一概而論。不能僅僅因為軍事活動伴隨著軍事戰(zhàn)略目的,而將其定性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從而認定其違反了一般國際法。“一些可能發(fā)生在公海的海軍演習和常規(guī)武器試驗是可以被接受的”(66)Alexander Proelss, Peaceful Purposes, MPEPIL, para. 15.。《公約》第88條也適用于專屬經(jīng)濟區(qū),不能一概禁止軍事活動。否則,如果采取嚴格解釋,無論是沿海國還是其他國家都無法在專屬經(jīng)濟區(qū)或公海上進行軍事活動。但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處于國際局勢緊張,可能發(fā)生武裝沖突、武力使用的區(qū)域,這類軍事活動可能被認定為違反和平目的的行為。
綜上,軍事活動并不必然就是《公約》第88條與第301條所禁止的活動,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排除其合法性,即便“合法用途”的軍事活動,也不能認定是與航行、飛越等活動有關的“其他合法國際用途”,從而通過《公約》第58條合法化,需進一步分析軍事測量活動是否屬于《公約》第59條的“剩余權利”范疇。
(二)《公約》第59條
《公約》第59條“解決關于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權利和管轄權的歸屬的沖突的基礎”規(guī)定:“在本公約未將在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權利或管轄權歸屬于沿海國或其他國家而沿海國和任何其他一國或數(shù)國之間的利益發(fā)生沖突的情形下,這種沖突應在公平的基礎上參照一切有關情況,考慮到所涉利益分別對有關各方和整個國際社會的重要性,加以解決”。根據(jù)前文分析,在不與海洋科學研究活動競合的情況下,測量活動不屬于《公約》第56條與第58條的調整范圍。下文擬分析測量活動與《公約》第59條之關系,進一步探究測量活動的權利歸屬問題。
《公約》第59條作為一個候補條款(backup clause)(67)Proelss, above n.57, p.460.,針對的是《公約》沒有分配權利或管轄權的活動。盡管前文論述了測量活動并不是《公約》第58條第一款的“其他國際合法用途”之范圍,但是對于軍事活動(軍事測量)是否屬于“剩余權利”還存在著廣泛的爭議。下文先分析“合法用途”的測量活動,尤其是軍事(測量)活動,是否屬于《公約》第59條的“剩余權利”。
從國家實踐而言,包括巴西、印度、中國、伊朗、孟加拉國在內的十個國家都對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軍事活動提出主張(68)Kopela, above n.7, 4.。其中,大部分國家要求在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進行軍事活動前須獲得同意。伊朗1993年《海域法》禁止一切不符合其權利和利益的軍事活動與演習、信息收集及其他一切活動。但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意大利、德國等國家則反對這類主張(69)D. R. Rothwell & T.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2016, Hart Press, p.280.。海洋強國認為,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軍事活動應屬于海洋自由的范疇;即使屬于“剩余權利”,也必須考慮到沿海國以外國家的利益,而不能只考慮沿海國安全利益(70)See Proelss, above n.57, p.462.。發(fā)展中國家則認為,沿海國基于國家安全利益方面的理由,有權管轄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軍事活動。
就目前研究而言,主張軍事活動屬于“剩余權利”范疇者,沒有很好的理據(jù)(71)Guilfoyle認為主張剩余權利更加公平,See Douglas Guilfoyle, The High Seas, in Donald R. Rothwell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14; 易顯河認為《公約》第59條是為資源以外的權利所創(chuàng)設,而軍事活動正是屬于這類權利,See Sienho Yee, Sketching the Debate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 An Editorial Comment, 9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3 (2010).。認定剩余權利具有一定的困難性,因為其證明的標準是公約并沒有對這類權利決定歸屬。但是《公約》第56條與第58條,前者規(guī)定沿海國的主權性權利與管轄權,后者賦予沿海國以外的他國許多公海自由。要證明軍事活動不在以上兩個條款之中,方能證明它屬于《公約》第59條之下。
Pedrozo主張中國和美國可以簽訂協(xié)定專門針對專屬經(jīng)濟區(qū)的軍事活動的雙邊協(xié)定,其模板是美蘇《美蘇預防公海事故協(xié)定》(72)Raul (Pete) Pedrozo, above n.10, 27.。這類協(xié)定需承認專屬經(jīng)濟區(qū)的軍事活動的合法性,并加以規(guī)范。Pedrozo這類主張實際上是在承認軍事活動就是《公約》并未分配權利的活動。理由如下:
1.如果《公約》將軍事活動的權利分配給了沿海國,則完全不需要由軍事活動國與沿海國以協(xié)定方式對相關活動予以規(guī)范。依據(jù)《公約》第56條第三款,沿海國可以制定國內法,且其他國家必須遵守。
2.如果《公約》已將軍事活動的權利分配給沿海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認定這類活動為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自由。那么,其他國家也無必要再和沿海國締結協(xié)定處理此事項。其他國家完全可以主張軍事活動自由,不受沿海國的規(guī)范。
Pedrozo、Roach等人均帶有美國軍方背景,他們對于海洋權利的主張與美國國家立場一致。因此,軍事活動作為專屬經(jīng)濟區(qū)上的“剩余權利”是可以通過爭議各國的法律立場主張加以推斷的。
綜上,軍事活動(包括軍事測量)是屬于《公約》第59條的范圍之內的活動,但具體如何主張、如何使其受到規(guī)范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依據(jù)《公約》第59條,“這種沖突應在公平的基礎上參照一切有關情況,考慮到所涉利益分別對有關各方和整個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加以解決”。因此,實際如何處理關于這類活動的矛盾,取決于各方利益以及國際社會利益的平衡,這個平衡是以公平為其判斷基礎的,所以不得不進行個案考慮(73)See Proelss, above n.57, p.459; Tommy T.B. Koh, Remark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Myroon H. Nordquist, Tommy T.B. Koh& John Norton Moore (eds.), Freedom of Seas, Passage Rights and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Martinus Nijhoff Press, 2009, p.55.。沿海國的安全利益與外國軍事活動的利益(74)See Proelss, above n.57, p.459; Tommy T.B. Koh, Remark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Myroon H. Nordquist, Tommy T.B. Koh& John Norton Moore (eds.), Freedom of Seas, Passage Rights and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Martinus Nijhoff Press, 2009, p.55.甚至領袖型國家確保國際秩序安全的利益(75)Sienho Yee, above n.71, 5.,其間必須有基于全面考慮的平衡。
從現(xiàn)代國際海洋法的發(fā)展路徑看,隨著人類科技水平進步,認識海洋、利用海洋是一個不斷向前推進的過程。因此,沿海國必然會對于其鄰近海域提出越來越多的權利聲索與主張(76)XUE Guifang, above n.7, p.223。這種權利主張也在逐步固化,原有的海洋區(qū)域法律地位屬性也會隨之而轉變。1945年9月,美國發(fā)布兩份《杜魯門公告》主張了國家對于大陸架、公海自然資源享有權利。這一行為也直接影響了后來的三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對于大陸架與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的建立。
《公約》確立領海的寬度,確認國家可以主張12海里的領海,解決了前兩次海洋法會議未能解決的重要問題。《公約》第五部分創(chuàng)設性地規(guī)定了自成一體(sui generis)的專屬經(jīng)濟區(qū),賦予了沿海國兩類主權性權利及三類管轄權。專屬經(jīng)濟區(qū)制度創(chuàng)設以來,許多沿海國開始通過國內立法或者提交聲明等方式,主張對于專屬經(jīng)濟區(qū)上的事項享有權利,目前甚至有專屬經(jīng)濟區(qū)“領土化”之勢(77)Kopela, above n.7, 1-15.。許多沿海國主張對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的系列活動享有權利,這些活動包括軍事活動、水文測量、建造使用設施結構、海關管理、水下文化遺產相關活動等等(78)除前文對于水文測量和軍事活動之規(guī)制以外,中國、阿根廷、比利時、巴西在內的十三個國家已經(jīng)主張了對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一切設施結構享有管轄權;古巴、海地、納米比亞等七國主張在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享有《公約》未明確授予的海關管轄權;中國、澳大利亞、冰島、葡萄牙、西班牙等十三國主張對于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水下文化遺產的管轄權。。“領土化”趨勢不可避免地會推動國際法的發(fā)展,沿海國對于權利的固化,很有可能產生習慣國際法,使得其對測量活動的權利進一步為國際社會所認可。
結語
綜上所述,海洋科學研究活動與測量活動,概念非常模糊,但應用非常廣泛。本文認為,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是以海洋環(huán)境為對象的調查、研究活動。測量活動(包括水文測量與軍事測量)都與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有交集,對于同時屬于海洋科學研究活動的測量活動,應該受《公約》第十三部分的約束。因此,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測量活動受沿海國的管轄。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那些確實有別于海洋科學研究的測量活動,不符合《公約》第58條規(guī)定的“與航行、飛越自由相關的其他國際合法用途”,沿海國之外的測量國,不得主張海洋科學研究自由。那些符合“和平目的”的測量活動,屬于《公約》第59條“剩余權利”的范疇,因此沿海國與其他國家均可以主張權利,但是在專屬經(jīng)濟區(qū)“領土化”趨勢下,沿海國更有意愿且有能力去規(guī)范其專屬經(jīng)濟區(qū)內的測量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