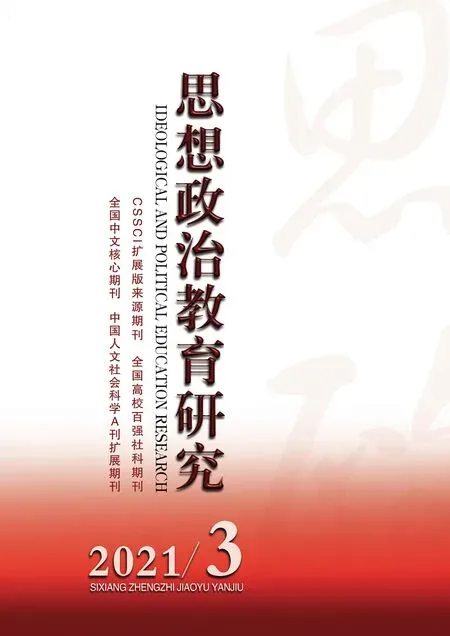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價值形態
褚鳳英
(天津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87)
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理論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礎理論的核心內容,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形態問題亦是學界比較關注的重要理論論域。迄今為止,按照主體標準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價值形態劃分為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是學界公認的定論。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是人,思想政治教育是關切人的價值追求的人類實踐活動,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從根本上來說反映的應是思想政治教育與人之間的意義關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應當成為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形態問題的基本維度。
一、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形態研究的方法論之反思
近年來,在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研究領域,不少學者都強調要推進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研究的人學轉向,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研究要遵循馬克思主義人學的研究范式。人學范式強調,要在社會哲學范式取得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更加側重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與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價值關聯。按照這個研究理路,研究者緊緊抓住“人”這個核心,按照價值主體的分類標準,從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這兩個層面來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形態,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問題,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對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的效用和意義問題”;[1]以價值主體作為區分標準,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可以分為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兩種基本形態。其實,按照不同的標準和從不同的角度,思想政治教育價值也可劃分為其他不同的形態,如理想價值與現實價值、正面價值與負面價值、直接價值與間接價值、絕對價值與相對價值,等等。[2]但是,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性特點來看,按照個人與社會這個主體標準區分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形態最具有操作性和實際意義,也符合人們分析問題的一般思維習慣,也更能體現人學范式的特色。另外,主體標準的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形態也能夠基本涵蓋其他標準的價值形態。因此,按照主體標準劃分的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是被學界普遍公認的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兩種形態,這應該是學界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形態研究的一個基本共識。
人學范式強調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人的價值的根本性,認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理性視野中,人才是終極目的,人是各種努力的終極關懷”,[3]這也是人學范式下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與立足點。這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人”。 從已有研究來看,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人的價值一般被歸結為個人價值。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依據主體的社會形態,主體可以劃分為個人(個體)主體、集團(集體)主體、社會總體主體和人類主體這幾種形態,其中個人主體是主體的一種重要形態,是其他幾種主體形態的前提和基礎。人類活動就是由處于各個層次上的不同主體形態構成的統一的活動系統。[4]那么,從人作為個體的人、群體的人、社會總體的人以及人的類存在來看,這四種形態的人都應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主體,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人的價值實際上是包含個人價值、群體價值、社會總體價值以及人類價值在內的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形態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個人價值只是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人的價值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的認識結果,是因為研究者往往把“個人與社會”這一對哲學中的范疇直接運用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這一具體現象,甚至有學者認為,個人與社會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基本范疇。[5]眾所周知,“個人與社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表達人的存在形態的一對范疇,強調“人類社會是由人在活動中相互之間發生的關系構成的系統,構成這種社會的是具體的、現實的個人”,[6]這對范疇對于研究人類生活中的各種具體現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由于人總是具體的、歷史的和現實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和虛幻的人,具體的、歷史的和現實的人總是生活和活動于一定的時空中,存在于每個時代個人的實際生活境遇和活動過程中,那么在研究人類的具體現象時,就必須將總體性的“社會”具體化,即必須明確現實的個人處于一定的群體、集團以及一定的社會總體等社會關系中,這樣才符合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個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7]的思想。這樣,人的群體、人的社會總體和人的類就構成了個人的集合體,它們是人的不同于個人形態的另外存在形態。因而,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這種具體的社會現象之于人的價值時,同樣也必須將個人所處的社會關系具體化為一定的群體集團以及一定的社會總體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等社會關系,因而個人、群體、社會總體乃至人類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主體。
另外,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價值這個概念,也往往容易出現歧義性認識:要么是把它理解成思想政治教育在社會實踐活動領域的價值,即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等社會生產和發展方面的價值,正如研究者明確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價值就是為人類社會發展尤其是精神文明的進步的效用和意義問題”,[8]是與人類的其他社會活動領域如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生態活動等發生作用而產生的經濟價值、政治價值、文化價值和生態價值等;要么是理解為思想政治教育對作為人的主體形態之一的社會總體形態的人的價值,而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差之千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歧義,是因為研究者對“社會”的理解具有不同的側重點。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社會是以生產勞動為基礎的無數個人活動構成的系統,社會的本質也就是人的活動系統的本質,社會關系是個人的社會結合形式和社會的內在結構。”[9]也就是說,社會具有“人的活動”與“人的關系”兩個維度,“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社會有機體是囊括全部社會生活及其關系的總體性范疇,指人類社會是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各種社會關系同時存在而又相互依存所構成的整體。”[10]社會的實踐本質辯證地蘊含著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是“人的活動” 維度,列寧就強調要“把社會看做活動著和發展著的活的機體”。[11]社會的另一方面則是“人的關系”的維度。如果側重于從“人的活動”這個角度理解社會,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價值就可以被理解為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社會生產和發展方面的價值。而如果側重于從“人的關系”這個角度理解社會,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價值可以被理解為對作為人的主體形態之一的社會總體形態的人的價值。
綜上可見,思想政治教育的個人價值并沒有全面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對于人的價值的全面性,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價值這個概念也容易引起歧義,因而有必要對按照主體標準劃分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形態問題進行重新思考。
二、社會發展價值和人本價值:思想政治教育的兩種基本價值形態
人在社會生活的主體地位,決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生態活動等社會生活領域中促進社會發展的價值的實現,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之于人的價值的實現為前提的,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對人的價值在整個思想政治教育價值體系中具有基礎性、根本性和前提性,基于此,我們可以把把思想政治教育之于個人、群體、社會總體乃至人類的價值稱之為人本價值,把已有研究中提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價值”稱之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發展價值”。思想政治教育的這種社會發展價值實際上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活動領域創造的價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在社會發展中的間接體現。已有研究也指出,“個體價值是社會價值的基礎,社會價值是個體價值的延伸和驗證。”[12]這實際上應該是說,思想政治教育對于人的價值的實現是社會發展價值實現的基礎和前提。這就足以說明,已有研究成果也反映了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價值”這個概念的可行性。
論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價值”這個概念的科學性,還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現象本身。 從思想政治教育現象來看,人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效果就是個人的思想品德發展和由個人構成的共同體(群體、社會總體、人類社會)的精神力量的提升。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何以產生了這種結果,以及如何更好地達到這種結果,就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研究的一個總體性問題。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產生與價值實現問題。因而,就有必要從人的不同存在形態方面深入細致地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體價值形態。
這樣,在同樣按照主體標準劃分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基本類型的基礎上,思想政治教育價值便呈現為社會發展價值和人本價值兩種基本的形態。這樣規定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基本形態,一方面,能夠在認識上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價值的不同層次,有利于避免在實踐中一味地注重追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發展價值,從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價值置于更加基礎性、目的性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價值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也是為了防止和克服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出現某些偏差的考量。眾所周知,社會發展對人的發展的條件性意義往往容易導致在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出現片面追求其社會發展價值的傾向,即過分追求思想政治教育對于社會發展的效能與實際效果,相反卻往往忽視了這些效能與效果產生的人自身的思想與精神前提。提出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價值及其基礎性、根本性和前提性地位,就有可能使人們避免這些錯誤傾向。同時,也有利于我們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充分注意和理解人的本質、需要、能力等內在規定的多樣性、全面性和統一性,理解人的發展的無限豐富性和可能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價值形態的研究進路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的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價值研究著重突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具體研究進路。
第一,著眼于人們生活于其中的利益關系,把利益看做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價值產生的客觀基礎。自從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利益問題就一直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焦點問題。人類的全部生活活動,都與利益以及對利益的追求有關;人們之間的全部社會關系都是建立在利益關系之上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3]人作為主體的需要和利益是其價值活動的起點和歸宿,個人、群體、社會總體和人類社會的思想、動機和行為都可以從其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中找到合理的解釋,因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14]正如列寧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自然史理論觸犯了神學的陳腐偏見,引起了并且直到現在還在引起最激烈的斗爭。”[15]馬克思在談到社會歷史觀時指出,要“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16]從馬克思的這個理解社會歷史的方法論來看,自階級社會以來人類社會生活實質上就是人類以國家為主導的圍繞各種利益關系問題而進行的總體性活動。國家一般通過經濟途徑、制度途徑、觀念途徑來調節利益沖突。[17]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統治階級調節利益關系以鞏固政權的國家行為,是整個社會利益調節的觀念途徑。思想政治教育以價值引導的方式調節個人與群體、個人與社會共同體的利益關系,促進個人對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的自覺認同,使社會利益分配機制和制度安排得到普遍認同,以形成持久的利益認同精神支柱和社會心理基礎。因此,必須著眼于人們生活于其中的利益關系特別是物質利益關系,從利益根源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價值產生的客觀基礎。
第二,立足于人的社會總體形態,在社會總體框架下分別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個人價值、群體價值、社會總體價值以及類價值等不同形態。在人類社會中,現實的個人組成了形形色色的群體,這些群體構成了社會的總體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才出現的社會現象,在社會歷史進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表現為以一定社會的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圍繞建立或鞏固國家政權而進行的價值引導活動,目的在于調節各種利益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初提到的“宣傳”“宣傳工作”,以及列寧強調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從外面把社會主義思想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都是指無產階級在建立國家政權過程中進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為資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搖旗吶喊,則是資產階級在建立政權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但是,這些階級在取得革命勝利建立政權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之后,無不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以鞏固統治階級的政權。可見,歷史進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在人的社會總體形態的范圍下,統治階級整合社會中各利益群體的思想觀念從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來維護其政權統治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的具體實施是通過對群體中的個人進行價值引導來實現的。當然,我國社會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還具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目的,但是這與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社會整體利益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因此,我們要遵循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思維路徑,在社會總體框架下,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凝聚社會價值共識的重要方式來描述個人價值、群體價值以及社會總體價值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人本價值形態。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類價值,從人類的發展歷史看,迄今為止人的存在形態主要是個人、群體和社會總體這三種存在形態。雖然從理論上說也存在人的類形態,但是目前人類還沒有達到無階級的社會,人類之間的沖突仍大于和諧與共識。“時至今日,人類還很難形成整體的力量,因而還不能作為真正意義的主體來起作用。”[18]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類價值不在本研究的重點關注之列。
第三,從現實的個人出發,即把個人價值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價值研究的邏輯出發點,在思想政治教育個人價值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的群體價值與社會總體價值。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價值研究的邏輯出發點,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價值生成的起點。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強調了現實的個人在社會歷史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強調“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19]“現實的個人”本身就蘊涵著一定的社會關系與實踐活動,否則就不能稱之為“現實的個人”,而只能是抽象的個人。馬克思把現實的個人看作人類社會歷史的起點,從現實的個人出發,考察了人的現實生活過程,揭示了個人從現實的生存條件中解放出來的自然的歷史過程,也為歷史找到了真正的主體。由此,從現實的個人出發也成為唯物史觀觀察社會歷史現象的根本觀點和方法。個人、群體、社會總體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如果把社會總體看作一個系統,那么社會群體便是構成這個系統的一個個子系統,個人則是群體的基本構成要素或單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價值,也必須從現實的個人出發,首先探討現實的個人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關系,即思想政治教育個人價值形態的具體內涵,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的群體價值、社會總體價值等人本價值形態及其發展變化的過程與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