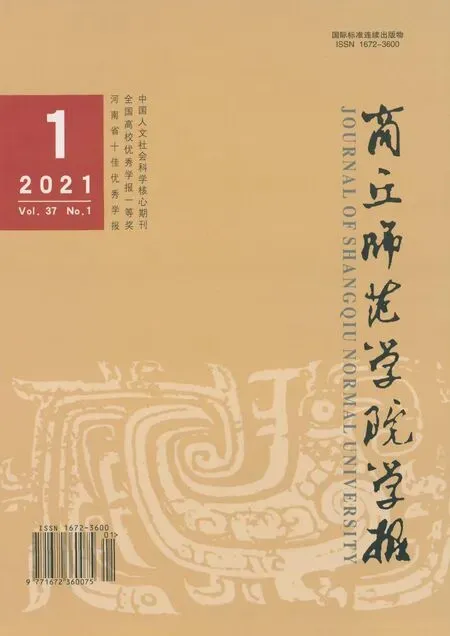道學之道
弗拉基米爾·馬良文
(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
道家創始人老子很早就得到了一個晦澀思想家的名聲。原因呢?他的學說被認為是深奧而神秘,有時使人感受到迷惑。實際上,這個定義來源于《道德經》作者的自我評價,我相信他就是老子本人 。《道德經》的作者從沒有用明顯的失望或諷刺的幽默提及同時代人對他的不予理解。為什么老子要抱怨溝通問題,而不是用“簡單明了的語言”來寫呢?答案是:他是一個思想家,其“心會”“神遇”,用的是古典道家的表達方式。這些都是道家先賢們所追求和重視的事情,其高于一切。
相遇是我們一生都在期待和回憶的事情。因此,相遇打斷了日常生活,它不能被身體感知,也不能被智力定義。它只能被直觀地理解為一條隱藏的經驗線索,將我們的生活變成命運。
道家所描述的東西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參照物的,不能按照任何“常識”或實證主義的知識加以理解。他們創造自己的語言,一種對信任他們的人的“方言”。他們不愿意創造一些可能會錯誤地指向某些東西的實質性的技術術語。因此,他們堅持使用自然語言,但在使用方式上,這些詞自發、甚至驚人地偏離其日常意義。否認自己,或者更確切地說,由于其含糊不清,體現了隱喻的轉變(使用J.Kristeva的令人難忘的表達),使每一個意義成為可能。老子的風格呈現出語言的犧牲,他的概念本身正在被清空,從構成這些觀念的內在矛盾中爆發(莊子對這一觀念作了精辟的闡述)。它們恰恰是在失去意義的時候獲得了意義,從而暗示了生活方式本身的終極現實,即連續的、無止境的、無處不在的而又不是局部性的變化。這些即興的語言轉換是相遇的標志。
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呢?這個問題在學術文獻中沒有得到認真的探討,在西方哲學的視野中也不容易解釋。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來確認這個本質上隱藏的轉變:使用那些已經在語義上否認或超越自己的術語。“忘”“虛”“隱”等是重要的道家觀念,“忘”要成為真正的“忘”,就必須忘卻自身 ;“虛”必須空化自身 ;“隱”必須隱藏其自身,且絕對如此,等等。
《道德經》第27章是道家“雙隱”策略的一個很好的例證。為了節省篇幅,我簡釋了最能代表老子難以捉摸的風格的著名悖論:善于旅行的人不留痕跡,善于封口的人不封口,善于制作繩子的人不用繩子,但繩結無法解開,等等。我以后再評論。這是近來安樂哲(R.Ames)與郝大維(D.Hall)翻譯的章節的后續部分。這一點在馬王堆漢墓中發現的老子《道德經》中有所展示: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第二十七章)
表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其格言是激進的甚至是不合邏輯的斷言。接下來幾行的信息是,智者保持內在的,本質上是贊美的,有助于與無知者建立聯系,也就是說,普通人的智慧和觀點并不真正相互矛盾。可以說這是老子的自然與精神在極限上的融合。沒有必要去操心靈性修養和洞察力:后者可以隨時隨地發生,因為生活本身就是潛在的靈性。難道我們不能在這里看到中國的道教老師的良性冷漠的根源嗎?這在外國人看來常常是一種不合理的傲慢?顯然,在“自然敏銳度”(1)“襲明”寓言的含義,當然更豐富,在馬王堆文本中有不同的文字,在西方文學中有不同的翻譯,例如:理雅各(J. Legge),陳榮捷(Wing Tsit Chan)等。中的交流具有本質上的道德性質,而且我們進一步看到了關于不拒絕無知者而后者充當了智者的“資源”(這里用“財富”一詞,似乎更合適)。為什么是資源,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財富?因為人們擁有共同的、一些絕對的,一種非知識的東西,在非存在中聯合在一起,而這些東西恰恰是他們所沒有的。“善”在這里既有“好”的意思,也有“能”的意思:智者知道如何養活老百姓,因此可以得到他們的支持;無知者之所以成為無知者,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開放到存在變化的深度。智慧是“贊美每一個存在”的能力,或者,我們可以說,為每個人提供享受生活的空間,并且,通過無為而在精神上成長。從整體的角度看待一切,即完整,提供了一個實踐“默示闡明”的機會,即一個真正的相遇,它包含或更確切地先于預測世界上的每一個角度(比較“最好的剪裁”不會在下一章產生分歧的說法;還可以參考《道德經》第36章中的“微妙”或“預測”闡明的概念)(2)吳澄把能者稱為“先知先覺者”,無知者為“后知后覺者”。。這也許是《道德經》最具體的主題:為了繼續活下去——“證實每個人的生活”——我們必須回到原始的存在基準、時間的起點。準確地說,這種在生命的流動中進行變化的能力,在《易經》的注釋中被定義為“善”或“能力”。
上述模棱兩可的推理在本章的最后幾行達到了新的深度。評論家們對“偉大知識”的含義看法分歧很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包括安樂哲與郝大維,在這里看到了對那些自以為知道的人的批評(《道德經》中的一個流行主題)。然而,一些道家或親道家的作家,如唐玄宗和宋代的道士詹白玉都認為,老子更進一步否認所有的傳統智慧,甚至是“有能力的人”,指出了一些超越任何道德判斷或理解的偉大智慧。這個真理無法定義,甚至無法想象。老子最終否定了智者與無知者的區別這一觀點,通過陳漢生(ChadHansen)的翻介,被西方翻譯界所接受。那么,我們就此認識“微妙的本質”: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第二十七章)
因此,人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真理之上,而這個真理卻沒有被人注意到,甚至是無法想象的。我們回到最初的格言:做的本質是不做,但正是這使任何行動有可能。一切事物都有其對立面的支持和證明,而非存在(無)則是每個存在的條件。我們所有的想法和觀點都得到了未知的善良和秩序,是我們頭腦中無法企及的。人們的相互關系通過“暗合”(玄通):他們越是不同,就越是相似。老子的智慧是自我消蝕的,因此本質上是反說的。然而超越是絕對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修煉時間越長,修煉越透徹。這是一種圓形或螺旋狀(因為它包括內部精神的破裂與升華)的思辨運動。順便來說,相當典型的《道德經》,說明了一個零碎的和邏輯的(表達),正因如此的風格惹惱了許多西方學者。不用說,它再現了蘊含沖突的“暗喻”本性。
老子的基本概念很好地說明了這種思維方式的“本真”(Thusness),“它本身就是這樣的”(自然)。這個概念超越了形而上學超越與內在、普遍與特殊的對立,自古以來就是歐洲思想的基礎。道家的自然意味著大多數情況下的一般原理和每一時刻的特殊性同時存在。毫無疑問,這是《道德經》中的“超然”和“獨立”的表達。然而,它也與“微妙的多樣性”的概念密切相關(“眾妙”),“無限的多樣”(“眾甫”)表達了多與奇的本體論。因此,自然的概念完美地證明了存在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此點,沒有通過建立任何特權的方式來代表現實,因此并不意味著任何對事物的暴力,不存在任何糾正世界的企圖。
宋代學者范應元對《道德經》第27章中對“精微”的表述進行了評論,指出它與老子教導中的另一個關鍵術語“中”有關。“中”的概念完美地詮釋了本質與媒介、焦點與斷裂的統一。這就是老子的精明:它自身永存,永存于事物的兩者之間,實際上是世界變化的一個取之不盡的備有者。“中”總是包含它的對立面:它既與自身相同,又與自身不同;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因此,這顯然是老子格言“中”所發現的“本真”概念和思想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結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它與“和”的思想相匹配,是一種平衡的、有節制的內在穩定的表達,它只能被理解為對不確定焦點的內在驅動力。
這就是老子的相遇方式的含義 :“最小的碎片”,一種寬度的斷裂這使得通過存在的“成功”的連續性和無休止的革新,或者更確切地說,永恒的重現使得創造世界成為可能。“中”總是指虛擬力量之間的差異關系:它是一個不起眼的事件,一個“即將到來”的真理,一個可靠的承諾。在西方思想中,這種創造性內含的非創造性因素,在歷史上已經成為事實,可是往往被傳統的形而上學所否認。道家思想對此有著深刻的理解經驗的基本層,主要是因為其修身自由,不受各種思想要求的遮蔽或限制 。《道德經》以“小”“微”“妙”“一”“信”等術語命名。“信”的概念的最高地位表明,道家的“原初”既不是某一種物質或本質,也不是某一種物質或本質的實現,是事物之間的聯系或者關聯。這也解釋了道家最重視傳統作為一種傳播行為,超越了傳統的暗喻,其存在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種“在我們出生前”的存在,體驗著“寂然誠誠”和“中中密印”。這種道只能傳播,而不能被占有,它是人際關系和交流的本質。
為什么這種道是“小”“妙”和“微”?由于意識對作為平淡事件的開放性所賦予的超敏感,屬于原始知覺的微觀世界,所以使用萊布尼茨的表達,小知覺構成經驗的原始矩陣。這不是虛無,而是過多地存在生命的豐富性、可變性的有限性,一種“虛空中的運動”,其最直接的表現是物質存在的內在性及其自發的動覺統一性。太極拳傳統的基本文本之一——《授密歌》中有這樣的描述 :“無形無象,全身透空。”[1]236
“潛移默化”的本質就是這樣:它由自身的自我消解、自我清空所證實。形與象的缺失,蘊含著事物無形的精華。它是經驗的條件,生命的源泉,能預見一切事物。它不是實在的,嚴格地說,是一個虛擬現實,根據經典表述為“存在和不存在之間”。在這個道的漩渦中,無數象征性的、潛在的世界在它們獲得可見的形式之前就產生并消失了。這種“道軸心”體現了純粹的情感,是一切生命轉變的動力,是構成“意”的非對象化存在的情感。“意”是一種自我決定的現實,是一種極端的有限性,它構成了一切事物的“微妙原則”(妙理),是每一種存在的內在限度和轉化的力量。
讓我提醒一下,最深層次的道學經驗,尤其是道家學徒的第一步,是對道和代表道的師傅的無條件的“信心”。這些工作需要信心或信任,因為它們與意識的預反射深度有關,只能象征性地表達。
在主體和客體分裂之前存在的“精神轉變”的連續統一體,必須被視為一種純粹的相互作用,沒有單獨的代理人的共同反應,一種無處不在的媒介和一切的限制。這個現實需要一種極其高度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與世界上自我解放的物質存在的充分性密不可分,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人積極地參與到梅洛—龐蒂所說的“世界之軀”中。我們的身體對外部影響的反應能力,甚至在它們成為意識的事實之前,就已經偶爾被西方哲學家所注意到,其中包括斯賓諾莎談到了“身體的理性”,尼采對“身體的偉大理性”作出了更加有利的評論。但也許這種生命的“內在啟示”的最激進的理論,是法國現象學家M.亨利提出的完全摒棄現象學距離的概念,并說到知識“不僅與我的第一個被動理解共存,而且與這種理解共存”。對亨利來說,生命是由原始的自愛滋養的感性,這種自愛包含著絕對的自我認識的原則。這一定義與老子基于自我認識的啟發概念有許多共同之處。此外,道學為我們提供了原始和無可挑剔的完整存在于世界系統之中的探索的經驗。
道家修行的目的,不管在膚淺的觀者看來有多奇妙,都是回歸到原始的、完全自然的存在狀態,這也相當于純粹的靈性。這是一種毫不費力的努力,是一種將自己釋放到原始存在的無縫網絡中,從“純粹自我”到大千世界前的“原始狀態”的方式。這種完美的自然性,是“本性”與“神明”的不謀而合。忘我將我們帶到一個非同尋常的覺知水平。為什么?原因在于正是這種充實的存在才是原則上自我區分的、無限分散的,其揭示了非創造的混沌和停頓,打斷了每一個節奏的構成。
因此,它指向了生命整體中的所有相互聯系,即“一體”全世界。誰會注意到這里?一個未知但絕對真實的“最高祖先”是所有人共有的“主體=x”,正如J·德勒茲(J.Deleuze)所說,它包羅萬象,但一旦反映的距離呈現,就消失了。“一”這個連續體,恒久不變、無所不在,異化是自身影響的復歸,是存在的虛實和相互滲透的實際方面。參與道的這種方式漩渦實際上是在恢復,或者說是“繼承”,是一切存在的源泉。因此,它認同預見未來事件的能力可以喚起未來。這也意味著道的行為與可見的傾向相反,它處于事物的邊緣,并且正在被世界永遠地遺忘。它根據道家格言走向一個“倒轉的小徑” :“逆來順受者為仙,效仿者將是凡人。”
本質上的中心是什么和諧的效果?正如我已經提到的,它是虛擬的持續時間,我們在這里處理的不是對象(和主題),而是預測,運動的航向。此外,“中心性”的前提是完美的、力量相互作用調整的,雖然也建立了它們的等級。最敏感的人是“先覺”(讓我們回憶一下吳澄的見解),正如老子自己所說,“先于人”,因此圣人自然是標尺,沒有提出超越的理想或存在的模式。精神敏感性使人意識到生命活力的內在來源,在道家文獻中被稱為“靜動之母”“玄機”“天機”,或叫萬物的變化等。這種“天機”正是因為“無形無象”,才無所不包,創造一切。太極拳大師李亞軒(LiYaxuan)把這種理念下的武術技能定義為“自發地跟隨天機并對變化作出反應”的一種能力。
“隨機應變”。我在吉列斯·德勒茲(JillesDeleuze)的思想中,發現了一個與這種思維方式相關的所見略同的西方看法,被描述為精神和身體之間的關系,一個實現不能完全實現與實現不能完全成為現實之間的關系。這個“天機”正是真實的虛無力量,它提供了具有深度虛無的現實。“存在的碎片”,在這種互動中是被遺漏的、可怕的儲存。正如德勒茲所指出的,對應于中國代表終極實在的道的循環思想[2]125。
我們現在可以補充說,生活在不斷流逝的瞬間虛擬模式中真正的時間,意味著動態中不斷下沉的存在,是由虛無與現實兩大方面所構成的。這種生活方式賦予了一個人“本真”的體驗,為什么?因為它是發自內心的喜愛,不需要公眾的認可——是對西方古典傳統的又一個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突破。
在從表面上真實的自我(個體)到真正的非自我(覺醒的自我)的實現過程中,一個人要經歷兩個主要的階段:首先要“忘記自己”,然后也要“忘記自我”,要消失務必被消失,意念本身必須是不經意的。這種道家無為的真理,超越了所有的意象和概念,甚至超越了純粹的、空洞的互動的概念。它是一種回歸“原本”的心靈或精神的運動,盡管它絲毫不否認“知”或“思”的心靈。一些現代道家大師把修行分為三個進程:第一個是使思想不存在(無),第二個是專注于所有形象的虛假(假),第三個是最后必須達到心靈的中心,即把握一切事物的無存在和不存在。它本質上是確定一個不固定的路徑。通過無保留的“天機”向覺悟的最高境界過渡,在我所知的太極拳大師的一句話中被描述為 :“有意則靈,無意則妙。”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這句名言與《道德經》第27章的結論驚人地接近。事實上,最高的成就意味著放棄自己的專注。正是絕對的空無,先于并使純粹相關的操作性、定性和差異性,虛無成為可能。反之亦然。恢復自然的感性揭示了生命的奇跡。太極的生活,就是生活在形與無形的交匯處,在“物之精華”的層次上,按照老子的說法,我們可以同時思考萬物的出現和歸宿。
最重要的是,我們預料到即將發生的事情。它是一種“可能”的存在方式,在這種模式中,事物“從虛無中產生”,在得到固定的形式之前經過轉換;它是存在于“存在和不存在之間”的東西。如果道家的洞察力超越了反思,那么它在人類實踐和意識中的軌跡是什么?它是一種甚至在物質實體之前的純粹的或絕對的知覺。正如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斯塔姆(O.Mandelstam)所觀察到的,有一種耳語存在于唇邊,有一種感觸既不知道客體也不知道主體,這才是卓越的觸感。事實上,在信息文明的條件下,感知能力已經變得非常重要,以至于它很可能被掩蓋為現代世界的身份認同,并提供基礎的智力反思。數字技術是否向我們揭示了我們在原始感知水平上遇到的那些極其靈活、短暫、充滿活力的微觀圖像元素?它難道不要求我們發展能力,直接處理圖像的流動,以生存的方式參與媒體世界,即永久的調解和聯系?
以前的時代,這些圖像構成了預言夢和精神的內容,成為被認同的一些人的幻象。現在公眾可以通過提供優先于物質存在的形象,刺激我們感知能力的發展,更廣泛地說是精神上的敏感。正是這些品質,我們才欽佩英雄。今天的數字資本主義:商人、經理人、經紀人、演藝人員等基于知覺的認同工程,為主體性開辟了一個新的避風港:先于反思的感知領域。這使得信息時代的社會價值觀,更接近于道家的理想,即一個指導世界而不被世界所注意的圣人。
如果被普遍評價為有害于人類精神的技術創新最終沿著新的路線迫切需要恢復精神的手段,我們難道不能稱之為歷史的天意扭曲嗎?我們還沒有準備好,依靠純粹的情感從而“遺忘”,不作自我反思,可以培養出什么樣的身份。情感是模棱兩可的,因為它揭示了世界對于批判性思維的不可用性。我們只能說,這將是一個偉大的自我的身份,其本質是一個承諾。一個新的人是匿名的,也是真實的,值得信賴的不可能。在實踐中,我們將觀察到反思與知覺的融合,反思同一性的動態平衡,以及最終達到知覺一個人對世界“軀體”開放的意識。這正是道家座右銘所說的 :“隨遇而安,我行我素。”這是人類最高的真理:和他人一起就是成為自己。
我還要指出,認同和感知的共同點是各自形而上學基礎的喪失。它需要主客體的超越二分法,正如瓦提莫(G.Vattimo)所說的“存在的弱化”。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對知覺的依賴意味著“虛無中的加速”,超越了鮑德里亞(J.Baudrillard)和其他許多同時代人所預言的歷史客觀性。毫無疑問,這個結論與道家關于現實是“懸于虛空”的純粹互動觀念,有很多共同性。
當下的僵局,對自我認同的總體驅動力,不可避免地背叛并最終取消了傳統思維,克服了傳統的、超自然的思考,并且最敏感地感知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現象背后的權力的作用。這個時代的當務之急,是需要在存在的內心真理(和證據)的基礎上創造“覺醒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