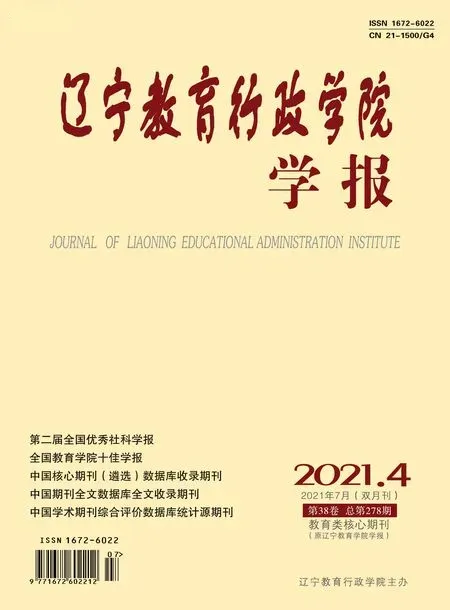試析新舊體碰撞下的東北第二代新邊塞詩
——以王子江作品為視角
郎曉梅
(遼東學院 師范學院,遼寧 丹東 118000)
一、關于幾個概念及研究背景
(一)關于“邊塞”“東北”“新邊塞詩”
《說文》釋曰:“邊,行垂崖也。”[1]“塞,隔也。”[1]1408《漢語大詞典》釋“邊塞”為“邊疆地區的要塞。泛指邊疆”[2]。“邊塞詩”概念中“邊塞”意謂邊疆。有人認為“邊塞詩”因題材內容歸類,取材“只要與邊塞生活相關的,統統都可以歸入邊塞詩之列。”[3]據此,關于“東北”,我們限定為今天遼吉黑三省行政區劃范疇內的地域,此域邊塞詩創作1949 年以前主要經歷過兩次興盛,第一次發生在東征高句麗的隋唐時期,第二次發生在清朝,因為清初文人、流人進入,以及清中后期至民國前的不斷開發和文官遣派。
1982 年新疆大學中文系發起的“新邊塞詩問題討論會”上正式使用“新邊塞詩”概念,其時間限定為1949 年至1966 年,空間限定為西北西南邊疆。學界后來的“新邊塞詩”研究空間幾乎一致指向“西部”。如周政保所說:“新邊塞詩是什么?那是中國西部豪放派的歌唱。”[4]浩明也說:“什么叫新邊塞詩?新邊塞詩是中國西部豪放派、婉約派……多民族、多聲部的大合唱。”[5]以至于80 年代中期“詩人和評論家們將‘新邊塞詩’的概念擴大為‘西部詩歌’”[6]。可見,其時邊塞詩研究不僅僅是忽視,甚至已經從邊塞詩“邊塞”的內涵上完全刪除了東北邊疆,略掉了東北邊塞詩。
(二)王子江“東北第二代新邊塞詩”研究背景
王子江1967 年生于遼寧阜新,1984 年入伍,于黑龍江省牡丹江工作2 年余,于吉林省通化工作9 年,在綏芬河及長白山邊境地區工作過,后任職沈陽軍區裝備部,經常隨軍區工作組奔赴邊防一線部隊。他說:“創作出版三歌集(舊詩集《牧邊歌》《即心歌》新詩集《雪塞歌》),是我一個很長時間的創作計劃。”[7]他的詩歌試驗是自覺的。
我們現在回顧“新邊塞詩”概念中的“新”的時間點。如前所述,1982 年新疆大學“新邊塞詩問題討論會”將其限定在1949—1966 年。后來的研究者們則將其后80、90 年代以來的邊塞詩統統冠以“新邊塞詩”。如楊金亭序《牧邊歌》標題“新邊塞詩創作的可喜收獲”[8],直接將《牧邊歌》歸為“新邊塞詩”。然而《牧邊歌》作者及其作品風格、創作傾向及藝術水準等已截然不同于學界已有“新邊塞詩”研究視域中的作家作品,為方便研究,我們將王子江作品歸為第二代新邊塞詩。
“三歌集”以闊大的東北邊關為背景,書寫其軍旅生活及情懷。“三歌集”形制幾番更替的寫作流程昭示著作者于新舊詩碰撞過程中詩歌創作的試驗性特征。可以說,王子江作品因為共時可觀的典型軍旅邊關題材和歷時所見的新舊碰撞中的突出試驗性,不僅使他在東北詩人群體中表現出獨特性,甚至在全國范圍的邊塞詩創作隊伍中都是卓爾不群的,在當代詩歌史上具有獨特的標志性意義。
二、《雪塞歌》《牧邊歌》:由新而舊的第一次碰撞試驗
(一)“三歌集”的創作時間節點
2011 年《雪塞歌》出版。王子江在后記中說:“這本詩稿應該是我最早的一本詩稿。”[9]王子江1985 年開始發表新詩,雖然新詩集出版時間靠后,但是毫無疑問,他是從新詩開啟詩歌寫作的。《雪塞歌》出版之前,王子江以新詩創作為主,兼寫舊詩。這些舊詩的創作起始時間為1990 年,雖然晚于新詩創作,但先于新詩結成《牧邊歌》,于2006 年出版。《牧邊歌》出版后,他繼續新詩寫作,并兼寫舊詩,并于2011 年出版新詩集《雪塞歌》。《雪塞歌》之后繼續舊詩寫作,2013 年出版舊詩集《即心歌》,其中“一小部分詩詞是未被選入《牧邊歌》的作品”[7]。《雪塞歌》的創作時間為1985 年至2011 年,《牧邊歌》的創作時間為1990年至2006 年,《即心歌》的創作時間為1990 年至2013 年,我們可以從這些創作時間點上發現“三歌集”創作時間的交叉性特點,并可以沿著主體創作的時間脈絡找到“三歌集”的試驗軌跡,以及因為時間的交叉性而必然產生的新舊詩體碰撞性特征。
(二)從《牧邊歌》看王子江新舊互參的舊體嘗試
《雪塞歌》《牧邊歌》的交叉寫作期間,發生了第一次新舊碰撞。這是一次由新體轉向舊體,而后新舊互參的過程。時任《中華詩詞》主編的楊金亭在為《牧邊歌》所寫的序言中說,盡管同期也出現了一批擅以軍旅、軍墾類邊塞生活為題材進行創作的詩人曾引起詩詞界關注,但是以其詩詞編輯的業務所及看,王子江才“應當是當代詩詞界尚在形成這個‘新邊塞詩’部落中的第一位名副其實的詩人”[8]2。毫無疑問,這次嘗試是有成績的。《牧邊歌》代表了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批舊體詩作者對傳統文化的深情回眸,是第一批新舊體碰撞試驗產物的代表。我們可以從其確為獨有亦非獨有的個體個性中感受時代整體的共性的創作情態。下面,我們從五個方面分析其碰撞性試驗特征。
第一,來看《牧邊歌》的詩歌體式試驗。“五四”新文化運動新詩打破舊體格律得以解放,改革開放后更多的新詩人開始回望舊體格律的古典美學。王子江在其后記中曾引用公木的話表達對舊體格律的敬意并指出,舊體格律形式“更適合于快速定格在快節奏的軍人生活中所能捕捉到的詩意”[8]210。但作品后記又提到詩集部分音韻曾受到過張正典校正,此事于張正典評論《一枝紅杏出兵營——讀王子江<牧邊歌>》中有所印證,他說:“今年春節過后,子江同志寄來《牧邊歌》再選稿三百首左右,欲改用平水韻結集成書,賜余先讀為快。”[10]最終出版的《牧邊歌》目錄非常清楚地分為兩輯:“第一輯平水韻(187 首)”和“第二輯 新聲韻(163 首)”[8]1-6,這種目錄方式說明了作者在用韻方面的著力和用心。
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批舊體詩人,尤其是北方詩人創作大多是運用普通話聲韻系統。關于平水韻和新聲韻的區別是在進行了一定數量的創作,有了自我反省之后,有的人放棄新聲韻轉用平水韻。這一方面,是基于對傳統音韻的進一步認識和接納;另一方面,是基于當時舊體文學界用韻的厚古薄今的風氣。《牧邊歌》的聲韻分類目錄體現了作者從新聲韻轉向平水韻的舊體創作初期的聲韻認知和試驗過程。
第二,《牧邊歌》表現了“我獨”之新的創作理念遷移試驗。新文學突出的“現代性”,決定了同期正在進行新詩寫作的作者必須在舊體形制寫作中,承載其新時期軍人所獨有的“我”的新生活、新情懷、新思想。關于“新”的追求,是他作為新舊兩棲詩人的必然選擇,是他的新詩創作理念向舊詩創作理念的正遷移。這種“我獨”之新表現在諸多方面,我們可以借其唯我獨用的意象試驗來看。譬如家鄉物類意象群:“明月三溝酒,春風半樹槐。相言皆俚語,都自故鄉來。”[8]130此詩用遼寧阜新所產國家名酒“三溝酒”作為阜新軍旅詩人的專屬鄉情意象,又引入同鄉從老家帶來栽在哨所旁的“槐”,兩相疊加以書寫軍中鄉情鄉誼,升華戍邊情懷。再如邊疆物類意象群,《詠界花》:“寂寂春關上,幽香暗自來。花知睦鄰好,一朵兩家開。”[8]25“界花”完全對立于岑參“故園菊”類的軍事地域邊塞意象,源于作者當今時代和平歲月戍邊軍人的身份。“漁火寒江盡,孤燈哨所明。峰頭聞鳴雁,一二三四聲。”[8]138邊地“鳴雁”渾比軍歌《一二三四歌》,聯想嫁接不可不謂新且奇。這種新奇是詩人的有意識追求,他曾在《緊貼時代要求創新軍旅詩詞》中說:“文學作品,其中也包括詩詞,其生命力,就在于其鮮明的時代性。”[11]
第三,《牧邊歌》也呈現了因新詩擅用而被認為是新詩創作手法的,其實在傳統舊詩中也廣被運用的詩法的泛化或白話式運用。如“春風今放貸,借我一船詩”[8]15之比擬類;“碧柳著裝春在手,紅旗一桿是中華”[8]51之象征類;“撈起童年事,追瓜野渡頭”[8]43之拈連類等,如是將“春風”擬為人,可以“放貸”可以“借”,將“紅旗”象征為“中華”,用“撈”拈出“童年事”,其共同特點是詩歌所呈現的皆是將具象轉化為抽象后的結果。舊詩講究借具象之“象”,以求抽象之“象外之象”,而非湮滅具象之“象”,但以抽象之象呈現。這種湮滅具象之“象”的抽象化舊詩寫作是作者新詩寫作手法的慣性使然,是由新體到舊體的遷移作用使然,這令其部分作品不像舊詩,而更像格律新詩。
第四,《牧邊歌》也表現了執著于傳統詩法的借鑒試驗。詩人積極仿用傳統舊詩所用辭格或踐行其他傳統詩法理論。譬如,“荒嶺明秋月,征衣寒野風。江中鳴過雁,夢里紡車聲。”[8]137此詩有李商隱《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形影,李詩云:“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12]兩詩都從邊關寫到夢中家里的舊物“紡車”“鴛機”,以寄托思家之情。但李詩從從軍遠寄征衣之難,進而寫邊塞天寒,因缺衣之患,故而夢到家中的老織布機,銜聯有致,水到渠成。而王詩雖言至“征衣寒野風”卻并無缺衣之實,且伊時早已不用自家紡車紡布做衣,“紡車”意象拿來突兀且生硬。可見詩人此期努力取法唐詩,嘗試用示現手法以記憶中所思對面的情境再現,來書寫當下境況中人的懷思之情的痕跡。此外如“界碑猶我我猶碑”[8]55“我不釣魚魚釣我”[8]73的ABBA 句式,也是對元稹《和樂天示楊瓊》“汝雖笑我我笑汝”[13],以及諸多唐人喜用的句內回環之法的不斷體悟與嘗試。
第五,《牧邊歌》中作品表現了對傳統詩法的試驗,不惟對具體辭格的體悟,更有因其入門的高取法唐宋頗受濡染而對傳統詩歌理念未必自覺地反復踐行,譬如形象思維。比如,“浮云林上過,返照鹿鳴泉。最是幽深處,營中一縷煙。”[8]7這是蘇軾所謂的“詩中有畫”[14],它描繪了一幅直逼人眼的邊地哨所風光圖。“雞鳴聞澗戶,返照云深處。木碗飲春芽,風吹杏花入。”[8]131詩中全為實像,無一字虛,構畫美景,木碗春茶杏花吹入,又得妙哉奇趣,足令人不舍把玩。顧況有《石竇泉》詩云:“吹沙復噴石,曲折仍圓旋。野客漱流時,杯粘落花片。”[12]100亦具形象有奇趣。然而兩詩并看,雖各有其美,顧詩在小泉之趣,意在其幽;王詩在農家之趣,更富煙火氣息,也更符合軍人的東北新邊塞詩創作基點,其意蘊更深厚有余想。從審美感覺上看,王詩也不遜于顧詩,相反其前兩句不似顧詩拘泥的散點輻輳式取象,或更勝于顧詩。如是通過具象可感的畫圖描繪,寫抽象的思想情感的作品,于《牧邊歌》中并不鮮見,且個別作品幾乎已經達到媲美唐詩的藝術水準。
三、《雪塞歌》《即心歌》:從舊而新而舊的第二次碰撞試驗
(一)《雪塞歌》的舊體思維
《雪塞歌》是詩人近乎天性的吟唱。一方面,詩人以“我”為軸心,用現代新詩形式,借助隱喻象征,與“雪”等客觀外物溝通交融,甚至時常進行主客體互轉,構架起了一個充滿性靈的邊塞詩國,詮釋著新時期戍邊唯一“我”之思想的革命性及情懷的現代性;另一方面,因為間雜于舊詩集《牧邊歌》和《即心歌》的創作過程,《雪塞歌》不可避免地表達著詩人不斷深化著的舊詩創作思維。
第一,《雪塞歌》部分作品不同程度借用了舊詩勻整的韻律形式,在對偶句的使用及句腳字的平仄調諧上,顯示了作者作為舊體詩人不同于一般新詩人的創作特點。例如,“連綿的山,因缺氧而匍匐/凄冷的風,因疲憊而斷續”[9]20,上下句字數相等,除“氧”與“憊”外,對應詞語結構基本相同,且能將連綿詞“匍匐”與聯合型復合詞“斷續”相對,從新聲韻看又平仄相對。再如,“只有靜靜的界碑/挺拔/孤傲”[9]93,后四字是詩句所強調重音,朗誦應有較長停頓以彰顯其意,因此尾詞形容詞詞性相同,聯合型結構相同,尾字一平一仄,工整對仗。此外諸如“或昂首嘶鳴/或低頭咆哮”[9]72上下句完全對仗,“關山是一本線裝的書/一頁雨/一頁風/一頁暴雪/ 一頁山洪/ 一頁鐵骨和英雄”[9]116,段內多處對偶或句內對偶的整句集中時可逢遇。1926 年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提出了新詩“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15]的“三美”主張,探索新詩格律化。《雪塞歌》體現了這種雖然是個人化的且可能只是潛意識的又一次的新詩格律探索,其實質是20 世紀末傳統文化回歸期,詩人向20 世紀初傳統文化沒落期的那些孤勇唯美的新詩格律化捍衛者們的不自覺的,但卻合乎文學發展規律的一次深情回望與呼應。
第二,《雪塞歌》部分作品表現出對古典詩歌典雅古氣的境味的追求。如《虎頭長城讀月》,“獨在深秋/踩著歷史砌成的高度/念春水伊人/讀曉月如鉤//多愁善感的江南/正飄著淅淅瀝瀝的小雨/穿透竹林的琵琶聲/把憂傷輕輕地灑濕了一地/欲遷往關東的燕子/正準備著各種問候語//潮起潮落的海邊/一節節長城吊起/思鄉的笛聲/瑟瑟/悠悠/幽幽/瑟瑟/往返于萬里長城的兩頭/讀曉月如鉤”[9]159,其間運用中國古典詩歌尤其是古典邊塞詩常用意象“月”“琵琶”“笛”“長城”,且首段、末段皆以古人詩語“月如鉤”結,令行文古風氤氳,讀之則思與千年以前的邊塞詩人聯通。唐代李益有《從軍北征》:“天山雪后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里征人三十萬,一時回向月明看。”[12]113對比之下,兩者雖形制不同,站位不同,情味有別,但有著一樣不絕的蒼涼邊塞征人相思的意味。此外,“于是/黃昏的郊野上/便多了個采摘紅豆的人”[9]144,“一盤粽子/兩碗硫磺酒/正在清唱屈原的《離騷》”[9]83,諸如此類容納古典詩歌因子的詩句也無不表達著作者新詩的古典主義試驗精神。
(二)《即心歌》的試驗實績
《雪塞歌》是兩次新舊體碰撞試驗的樞紐。其后的《即心歌》是詩人從新詩走出重歸舊詩的產物,它對照《牧邊歌》體證著王子江詩歌試驗的進程和實績。
第一,從形制體式上看,《即心歌》表現了作者關于舊詩體式認知的基本成熟。詩集中偶爾出現關于某些入聲字、平水韻的注釋或入聲字誤用的情況,說明了作者關于音韻的由新向古轉化的持續努力,而我們從其目錄“五絕”“七絕”“五律”“七律”“詞曲”幾部分的安排又可見這一時期作者舊體創作不再過度拘泥于音韻。另外,《牧邊歌》中存有5 首左右仄韻古絕,至《即心歌》仄韻古絕則有至少15 首之多,表明作者對舊詩平仄格律認知的進境,創作處于不斷趨于自由的行進狀態中。
第二,從創作風格上看,《即心歌》更加成熟穩定,整體表現出自在安詳的氛圍,堪稱“田園牧歌”式的邊塞詩集。例如,“隱隱云深處,陽光爬老樹。春眠哨所中,山鳥敲窗戶。”[7]3極富野趣,倘若詩中沒有“哨所”二字,所寫就是一個普通的山里人睡足醒來怡然自得的樣子。再如,“濺濺懸崖水,森森了望臺。夜深人不靜,雨過雁聲來。”[7]4雖有軍事意象“了望臺”,但不礙其對哨所環境的生動率真脫俗空靈的描寫。兩首詩間詩人的自在安適頗可比與王維《輞川集》中山林隱居的心境。作為邊塞詩集,《即心歌》以安寧平和的浪漫調子為主,呈現出恬然自在的風格特征,與蒼涼悲愴的中國西部邊塞詩及苦寒怨懣的中國古代邊塞詩徹底區分開來,有其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時代特色,以及強烈的辨識度,是此期國泰民安的客觀映像。
第三,較之《牧邊歌》,《即心歌》在藝術表現上新舊糅合度更高。一方面,《即心歌》繼續植新詩慣用之修辭入舊詩。例如,“熒屏監控界江橋,鎖定邊情動鼠標。拉近春風笑中看,兩只黃雀筑新巢。”[7]35嵌入“熒屏監控”“鼠標”等新語詞,“拉近”也是現代科技功能,其新不必說,“兩只黃雀筑新巢”則有其新詩象征意味,它們象征著邊地蓬勃的自由發生著的生命力,他們的活動象征著邊地安寧有愛的生活,而整首詩看來似乎也隱喻著正在監控著這一切的軍人的有愛情懷。再如,“戰士拽朝陽,踏歌荒徑雪”[7]6,“拽”意為“拉”,及物動詞,其賓語語義條件要求為“+ 具體+可觸”,“朝陽”雖具體,卻不可觸碰,自然與“拽”不能搭配,詩中的反常規搭配可視為“錯搭”修辭,是當代新詩人必欲破壞漢語語法語用習慣的語言陌生化追求的直觀表現和具體方法之一。《雪塞歌》中即用“我的影子急促地拉著我”[9]5,動詞“拉”在“用力使朝自己所在的方向或跟著自己移動”義項上的主語語義條件要求應為“+ 動物+ 有自主行為能力”,而“影子”全不具備,因此詩句新奇。另一方面,《即心歌》新事化古之功漸趨通透練達,有更多渾然天成頗具唐風的作品。如“野徑T 臺路,山巖老板床”[7]86,“上下蒼茫里,K 歌煙火中”[7]25,其中的“T”“K”英文字母移用其意雖新,而不隔于舊體形式暫且不談,更有諸如新事入古勝古者,“幽谷藏營院,雞鳴泄密聲。如繩縛云路,時隱綠衣行。”[7]3四句中三處涉新,但皆能與語境融合一體,并不突兀跳脫。“營院”和“綠衣”兩處即明確指事又不似用“軍”類字令刺目不諧不安,此外“藏”更顯谷幽,“繩”“縛”妥帖佩用,表現林中山路的屈曲狀貌,都表現出作者煉字的非常手段。詩風清幽閑逸,古意蔥蘢,不輸王維《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危徑幾萬轉,數里將三休。回環見徒侶,隱映隔林丘”[16]之味,而其從戍邊意義上出,韻味上或比王維詩更醇厚綿遠。
四、結語
王子江曾撰文批評現代詩詞創作“重內容輕形式、重思想輕藝術”[10]209的現象,強調學習中國傳統詩詞技法的重要性。但是他同時指出,學不能全盤照抄,而應該“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特別要借鑒當今世界上諸如攝像‘搖、拉、推、移、跟’等新的有益于詩歌發展的藝術表現技巧”,“古為今用,洋為我用,用新理念、新方法、新手段,來反映新時代的新內容、新思想、新境界”[10]209。“三歌集”清楚地表達并實現著他的創作理念。因此《牧邊歌》出手即有不亞于唐代詩人的作品,而《即心歌》于古形制之間寫新事、用新法、出新趣,而猶能古意盎然,新舊中和以標新之功力愈發爐火純青。
以“此時代”“東北”為兩個基本點,王子江的邊塞詩主體以平和安定的“田園牧歌”式風貌區別于中國西部邊塞詩,以唐風駘蕩新意盎然的更高層次的藝術水準區別于藝術相對粗糲的第一代“新邊塞詩”。同時,以《雪塞歌》為樞紐,從《牧邊歌》舊體寫作期的第一次新舊碰撞試驗到《即心歌》舊體創作期的第二次新舊碰撞試驗,1985年至2013 年間,王子江經歷了大概28 年的新舊體交互摻雜的詩歌創作區間。這個區間正值改革開放以后文藝思想解放新時期文學復蘇春潮拍岸的黃金時期。此期關于文本形式、寫法及相關方面不斷變革反復試驗的文學創作思想氛圍極為熱烈濃厚。
當此潮流,王子江以“三歌集”為文本依托,經歷了將投射西方文化的目光轉移到中國傳統文化、最終帶著觀照過西方文化的目光回歸傳統的過程,并終究以豐饒的實績宣告他的民族性書寫的試驗代表的詩界地位。“詩人,任何藝術的藝術家,誰也不能單獨地具有他完全的意義。他的重要性及我們對他的鑒賞就是鑒賞他和以往詩人以及藝術家的關系。你不能把他單獨地評價;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間來對照,來比較。”[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