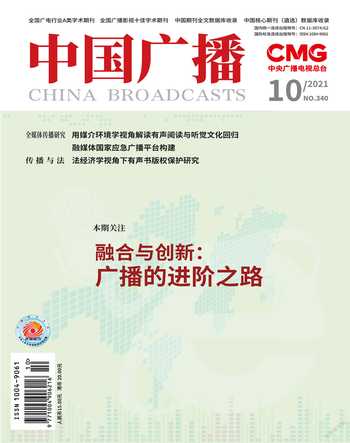互動儀式鏈視域下移動音頻平臺的互動分析
趙平喜 胡瀅
【摘要】移動音頻平臺的用戶角色是產消合一者,互動是用戶與用戶、用戶與平臺之間最顯著、最多內容的形式。用戶個體互動趨向私密化,平臺群體間的互動趨向社區化,平臺互動逐漸兼顧線上與線下,但存在著部分用戶互動內容低俗化、用戶平臺互動參與度不足、新媒體平臺媒介素養缺失等問題。本文以喜馬拉雅客戶端為例,提出移動音頻平臺要強化把關機制,提升內容質量,創新互動方式,增強用戶黏性,加強政策引導,提高媒介素養。
【關鍵詞】互動儀式鏈? 移動音頻平臺? 喜馬拉雅
【中圖分類號】G222? ?【文獻標識碼】A
移動音頻平臺利用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作為媒介載體,通過網絡下載或者上傳等方式提供音頻收聽服務。這是一種新環境下的聽覺業務,服務于人們的聽覺系統,展現音頻的價值。對比傳統廣播,移動音頻在5G支持下將以更加定制化、場景化的服務贏得用戶認可。①
本文認為,移動音頻指在互聯網環境下以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個人便攜智能終端為載體,以訴諸聽覺應用軟件的語音互動為主要表現形式,提供收聽、分享、交流、互動的沉浸式服務,內容涉及生活各個領域。移動音頻平臺指承載移動音頻服務業務的載體。
一、移動音頻平臺的傳播特征
(一)用戶角色:產消合一者
在web3.0時代,移動音頻平臺的受眾扮演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雙重角色,是美國學者阿爾文·托夫勒所強調的主動“產消合一者”,“只要既生產又消費自己的產品,我們就是在進行產消合一”②。移動音頻平臺用戶在消費喜聞樂見的他人作品時,閑暇之余也會生產自己的作品。
(二)內容類型:長尾化、個性化
移動音頻平臺滿足了不同圈層群體的個性化需求,還有效地創造出長尾市場。與其他平臺在內容取舍上的“二八定律”不同,移動音頻平臺關注“頭部”,更專注“尾部”,注重個性化需求,著力細分市場,挖掘讓不同受眾得到滿足的內容。
(三)生產模式:專業生產內容(PGC)+用戶生產內容(UGC)
移動音頻平臺的用戶主體意識強,越來越多的聽眾將自己的作品進行展示或提供給他人鑒賞,在這類UGC模式下,網民不再是只會窺屏的觀眾,而成為內容的生產者與提供者。而移動音頻平臺的另一種內容生產模式PGC,則以內容的個性化、專業化創造價值,實現價值變現。移動音頻平臺憑借UGC+PGC的內容生產模式,實現內容—用戶—價值變現的商業閉環。
二、移動音頻平臺互動的路徑
(一)內容生產過程中的互動
移動音頻平臺作為內容型的媒介,從用戶使用該平臺時便開始了互動。一方面,用戶在平臺內容生產過程中參與互動,具體表現為上傳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用戶使用該平臺娛樂、消遣時,也創造了內容,實現了用戶與平臺互動,沉浸在移動音頻平臺的用戶看似在打發時間,實則成了“免費內容”生產供應商。
(二)面對面人際傳播過程中的互動
移動音頻平臺作為線上虛擬平臺,時常舉辦主播與粉絲之間的線下交流會,通過面對面的人際傳播,將在虛擬世界建構起來的互動延伸到現實社會,并強化群體間的紐帶關系,使其變得更加牢固和穩定。
(三)強社交網絡傳播過程中的互動
移動音頻平臺在微博、微信及抖音等多個社交媒體平臺都擁有賬號,微博的弱連接和微信的強連接使用戶和平臺的互動關系更加緊密、即時。這種強社交網絡傳播過程中的互動也正是移動音頻平臺迅猛發展的原因。
三、移動音頻平臺互動的趨勢
(一)用戶個體互動趨向私密化
在移動音頻平臺上,主播與受眾間的互動可以實現兩者之間的“點對點”傳播。一對一的往來對話不像平臺中明顯可見的點贊、評論式的互動溝通,這種“點對點”形式的互動只有使用者自己知曉,屬于移動音頻平臺用戶個體間的一種私密性互動。
(二)群體間的互動趨向社區化
任何一種媒介受眾或用戶都會按照一定的群體規則產生屬于自己較為親近的社群,同時與其他社群之間保持著圈層壁壘。目前的移動音頻平臺也存在著類似的特征,平臺內各用戶群體用心經營著虛擬的網絡互動關系,不與其他群體溝通交流,平臺群體間的互動在這種趨勢下逐漸走向社區化。
(三)平臺互動逐漸兼顧線上線下
移動音頻平臺本身有著良好的互動傳播,也扎根于現實世界的人際互動傳播,主播與粉絲之間構建更牢固的互動傳播關系。這種線上虛擬世界的互動傳播與線下現實世界的社會交往傳播完美結合,使得移動音頻平臺的互動傳播特征更加立體,具有傳統廣播無可比擬的優勢。
四、喜馬拉雅移動音頻平臺的互動分析
喜馬拉雅平臺的用戶呈現“高學歷、年輕化”特征。作為新興的移動音頻平臺,喜馬拉雅豐富的錄音、直播等功能和優質的互動體驗吸引了“數字原住民”。50.85%的被調查者表示通過媒體廣告知曉喜馬拉雅,38.14%的被調查者表示通過朋友推薦使用該平臺。喜馬拉雅用戶的活躍時間大多是在每天的18:00~23:00,使用時長約為1~30分鐘。對大學生來說該時間段休閑時間相對比較充足,喜馬拉雅能夠滿足其精神需求及與他人互動的需求。
(一)互動形式
喜馬拉雅平臺用戶互動形式最直觀呈現的是點贊、評論及邀請好友一起聽。當用戶發現自己與某一主播發表的作品契合時,就會不由自主地評論、點贊,甚至通過點擊“星星”表達對主播及其內容的喜愛。相較于傳統廣播,喜馬拉雅平臺用戶互動形式還增加了一項直播的環節,可以增強聽眾與主播之間的情感聯系。
(二)互動動機
喜馬拉雅平臺用戶互動動機可以劃分為以下兩種:一是個體情感的釋放與表達,他們可以留言、與他人交談,宣泄自己的情感,當得到他人回應時,用戶自身使用該平臺的意愿也會進一步得到加強;二是個體存在感的需要,特別是獲得觀看者“打賞”的時候,猶如自我價值得以實現。
(三)互動儀式的形成條件
互動儀式包含身體共在的群體聚集、局內局外的劃分界定、相互的關注焦點、共享的情感狀態四個要素。③喜馬拉雅平臺互動儀式的形成條件主要基于以下兩點:
其一,虛擬的在場感。不管在場的人是不是有意識地關注對方,都能通過其身體在場而相互影響。④喜馬拉雅使用者創造“我要錄音、我要直播”的虛擬情境空間,并提供諸如寫評論、邀請好友一起聽、多人錄音、粉絲互動等線上互動形式。用戶可以通過登錄賬號實現不需要身體在場的遠程虛擬共在。通過虛擬在線,平臺用戶還可以與喜歡的社會名人、演藝明星等展開互動,建立在現實生活中難以達到的互動關系。
其二,共享的情感糾葛。喜馬拉雅平臺用戶可以通過錄音或者配音的形式表達或抒發情感,其他用戶收聽該類作品后受到觸動,會主動上傳作品表達自己的情感或在評論區做出回應,形成共同的群體情感。喜馬拉雅平臺為用戶的信息交流和情感聯系創造了多元的頻道式互動際遇,滿足了用戶多樣化的情感需要。
(四)互動儀式的結果產出
互動儀式的組成要素有效綜合,積累到高程度的相互關注和情感共享時,參與者便會產生群體團結、個體的情感能量、代表群體的符號、道德感等四種體驗。⑤喜馬拉雅互動儀式的結果產出主要有:一是群體圈層的凝聚。例如:喜馬拉雅參與陜西少年兒童文化傳承行動“少年三秦說”,少兒主播們通過訴說家鄉的歷史文化、美食美景、發展變化等逐漸形成一個圈層,強調“我的家鄉”集體符號存在的意義和重要性,陜西人群體成員的身份感和歸屬感得到強化,凝結成了更高層次的群體團結精神。二是個體情感的滿足。自豪感是自我受到群體激勵而生成的情感,是一種自我自然地融入互動流中的感覺。在“少年三秦說”活動中,少兒主播們通過共訴家鄉情、講家鄉故事,增強了自己對故土的感情,并且在互動儀式中強化了身為陜西人的自豪之感。
(五)互動儀式的市場資源
在不同際遇條件下,參與者能否以及怎樣吸引對方加入互動儀式,體現了互動儀式的市場特征。喜馬拉雅互動儀式的市場特征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符號資本。喜馬拉雅平臺用戶之間符號資本的匹配程度是劃分互動儀式中圈內人和圈外人的準則⑥。用戶發現對方愛好與自己相同,并毫無隔閡地進行互動,這個用戶就歸類于該頻道的圈內人,反之則為圈外人。在喜馬拉雅頻道的分類中,用戶A是相聲小品類聽眾,用戶B是評書類聽眾,二人則沒有共同的關注點,因為該類符號不同,兩人所進行的互動儀式也不盡相同。
第二,情感能量。喜馬拉雅平臺為用戶提供情感連接與互動交流的情景空間。通過錄音上傳作品、評論、分享等表達方式,用戶從其中獲得充分的情感能量,為下一次互動儀式的參與增添動力。喜馬拉雅平臺用戶的情感展示滿足了用戶的個體情感需求,“在互動中,人們對時間、能力、符號資本和其他能應用的資源進行估計,然后選擇那些能夠最大程度地增進他們感情利益的方式”⑦。
五、移動音頻平臺互動發展的困境
(一)部分用戶互動內容低俗化
移動音頻平臺內容生產模式為用戶生產內容+專業生產內容模式,這一方面增加了內容的生產數量,但“人人都是主播”的最大弊病是造成內容質量的參差不齊。無論是用戶上傳內容還是直播內容,都存在著把關缺位情況。
(二)用戶平臺互動參與度不足
盡管平臺存在評論和邀請好友一起聽、打賞、直播等互動模式,但互動氛圍仍較為冷清,互動模式較為單一,平臺互動的參與度嚴重不足。主播和平臺用戶完全可以繞過平臺,直接在社交媒體上實現一對一的溝通交流。而且,用戶對喜馬拉雅、荔枝等移動音頻平臺黏性和依賴性都不高,長此以往,移動音頻平臺的互動機制勢必難以有效維持。
(三)新媒體媒介素養缺失
移動音頻平臺作為一個新媒體平臺,吸引了大量聽眾和數以萬計的主播,但也極易因龐大的流量和利潤而走向歧途,喪失自身的媒介素養。如2018年喜馬拉雅為了留住更多的用戶、主播,追逐平臺互動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出現了侵犯某些作家版權的問題,導致企業產生損失。
六、進一步優化移動音頻平臺互動發展的對策
(一)強化把關機制,提升內容質量
不同于傳統廣播擁有一套非常嚴格的內容生產流程,目前移動音頻平臺用戶互動中的內容低俗化問題亟待整頓,必須強化把關機制,嚴格審查各項內容,對低俗化、媚俗化等內容堅決做到零容忍。
(二)創新互動方式,增強用戶黏性
移動音頻平臺必須采取相應措施,確保用戶和平臺間的黏性,拓展用戶評論渠道,創新互動方式,可以設計研發圖文、表情包甚至語音等評論方式,激發聽眾與主播間的互動。
(三)加強政策引導,提高媒介素養
當地管理部門應出臺相關法律法規或監管規定,加強對移動音頻平臺的互聯網屬地化管理,促使平臺自省并加以更正。移動音頻平臺的使用主體歸根到底是人,管理部門應該加強對移動音頻平臺用戶的政策引導、宣傳和教育,督促其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與他人、平臺進行可持續發展的互動傳播,共建共享良性、和諧的移動音頻平臺媒介生態環境。
注釋
①申啟武:《移動音頻的崛起與傳統廣播的選擇》,《中國廣播》,2019年第9期。
②《托夫勒的“產消合一經濟” 》,《管理與財富》,2007年第2期。
③④⑤⑦〔美〕蘭德爾·柯林斯:《互動儀式鏈》,林聚任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⑥鄧昕:《被遮蔽的情感之維:蘭德爾·柯林斯互動儀式鏈理論詮釋》,《新聞界》,2020年第8期。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規劃一般項目“加強我省互聯網屬地管理的法治體系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5ZT31)前期成果】
【作者趙平喜系三明學院文化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胡瀅系猿起(武漢)科技有限公司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