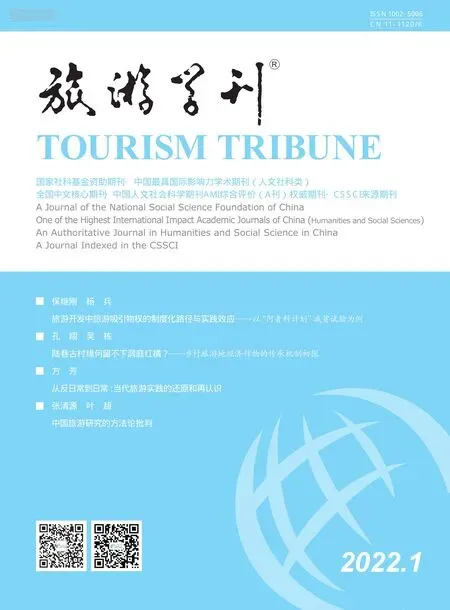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強化循環內生動力
張樹民
隨著“國際國內雙循環”“推動高質量發展”“加速文旅融合”等時代任務的提出,站在“十四五”新時期的時代節點上,旅游業如何反觀“雙循環”作用,搶抓“內循環”機遇,破解自身發展難題,并更大力度發揮其綜合作用,的確需要仔細辨析、深入探討、精心謀劃和認真實踐。
一、旅游業在此前的“國際循環”中,總體處于被動地位
從改革開放之初,旅游業就作為“窗口行業”被高度重視。因此,在國內“黃金周”制度出臺之前,旅游業的主要發展基調就是“大力發展入境,實現創匯目標”。在這個階段,中國總體參與國際循環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資和國際技術,國內加工,對外出口”,旅游業由于“通過窗口讓外方更了解中國,通過創匯為引入積累更大能力”的作用而參與循環并發揮作用,這種“國家政策驅動”,迅速擴大了供給能力。“黃金周”制度使國民旅游意識得以激發,加入WTO使出境旅游目的地國家和地區迅速增多,越來越富裕的中國游客在“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時間、旅游動機”三個方面,都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尤其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讓周邊亞洲國家加強了對中國的旅游宣傳,歐美國家也發現和重視中國游客規模和消費潛力,加上國內當時甚囂塵上的“奢侈品”消費風氣,導致了通過旅游渠道“出國購物”成為一種風氣,并一直延續到2020年疫情暴發才終止。其后果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讓中國旅游業界與國際接軌速度加快,迪士尼、環球影城這類項目得以引進,國際上文化IP應用模式對中國旅游業界也進行了啟蒙;另一方面,“消費外流”迅速提高中國游客滿意度門檻,使國內旅游投資的方向感、節奏感、積淀感、成就感都變差,催生出不少好高騖遠、虎頭蛇尾的旅游項目。這個階段,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和“消費市場”。旅游業因“境外購物”的市場驅動而參與循環,“出境便利條件、目的地宣傳、國民富裕度”等綜合因素為參與能力提供了可能。
基于這樣的發展背景,第一,無論是最初的“入境”循環,還是后來“出境”循環,旅游業都是“被裹挾”——入境時代是“引資創匯”的政策工具,出境時代是“消費外溢”的市場渠道。第二,“入境”循環與“出境”循環,此消彼長,先后出現,并未互為補充,互相均衡。第三,旅游業自身循環驅動力,并沒有形成和凸顯,盡管兩個“循環”階段旅游業都得以迅速發展,但長期從屬地位導致總體上地位邊緣和能力孱弱,這在疫情初期已經明顯暴露。
二、旅游業“內循環”較早出現,但面臨困境
1999年國慶開始的“黃金周”制度,既帶來出境旅游增長,也帶來了國內旅游需求暴發。2009年,國務院把旅游業定位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各省也紛紛把旅游業作為支柱產業發展,政策利好與流動性充足的同時作用,使旅游投資逐漸趨熱,以“招商引資、資源開發、投資建設”為主要驅動的國內旅游循環開始出現。這個循環,與前面談到的兩種國際循環不同:一是主動,旅游投資成為主動性內生驅動力;二是閉環,基于需求增長、供給擴大、資本逐利、開發能力提升等邏輯,都指向內部閉環;三是正向,更多開發建設對總體經濟發展有利,國家“幸福產業”的定位對促進質量有利,市場對文化IP的重視對提升能力有利,項目增加對就業拉動、扶貧脫貧有利。但是,這個循環邏輯在實踐中遭遇了困境,主要體現在旅游盈利水平的低迷,使市場主體投資意愿下滑。這必然使循環驅動力受損,并影響速度、質量和持續性。導致這種困境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第一,除了“旅游+地產”的模式外,還基本沒出現能夠支撐項目投入規模和盈利周期的市場反哺模式;第二,看似龐大而日益增長的國內市場需求規模,因為出境旅游消費分化、國際質量與價格對比等原因,讓國內旅游投資回收期和回報率都很難達到預期;第三,關于自然、人文景區在用水、用地、利用鄉村房屋等多個方面的政策限制、分割、變化,導致隱形投資巨大,旅游項目投資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第四,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資階段的過度承諾和項目建設運營期的服務缺位(甚或過度管理),使一些旅游項目得不到應有的扶持;第五,現行假日制度的彈性不足,使不同時間節點經營收益極不均衡,增加了運營難度。
三、疫情及中國應對措施,給旅游業“內循環”帶來寶貴契機
新冠疫情暴發后中央的果斷決策和強有力領導,為我們帶來了寶貴的發展契機。(1)在國際疫情仍然快速蔓延之時,中國已經能夠有效控制疫情,使國內旅游得以迅速恢復;(2)原來每年超出1000億美元且不斷增長的出境旅游消費規模,因為疫情隔斷而不再“外溢”,將為國內旅游提供新的消費拉動力;(3)國家不斷出臺的促進扶持政策,仍在為旅游業發展提供更優環境。這種新契機,可以說就是給原來“投資驅動”的獨輪,增加了“需求拉動”的另一輪,既讓“雙輪驅動”成為可能,又讓供給動力和需求動力能夠在空間上一致,時間上吻合。同時,“十四五”期間文化發展政策、供給鼓勵政策、消費刺激政策,又會讓“雙輪驅動”的速度得以加快。長遠看,這種旅游內循環的逐漸鞏固與不斷演進,也增加了旅游業主動為中國外循環“賦能”的可能性。可以預見,旅游業在內生“雙輪驅動”、外部政策加持的作用下,將逐步補足國內旅游項目建設中的投資回報不理想、投入能力不持續、文旅融合不充分、產品質量不進步、創新動力不強勁、時間安排不科學、空間結構不合理等短板,使旅游業成為“內循環”的主力軍和示范者。這既能讓旅游業為進一步提升國家經濟實力作貢獻,又能使中國國內旅游業成為世界旅游業的示范,進而對提升文化話語權也起到重要作用。
四、更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為加快實現旅游業內循環助力
長期以來,旅游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在中國旅游業發展中起到巨大作用:一是直接實現政策意圖,近40年來的各項旅游發展政策最終通過企業作用于市場而實現;二是帶動市場創新,旅游業的諸多創新業態、模式、商品、服務,大都由基層實踐中肇始,實驗室研發轉化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三是擴大就業規模與人才隊伍,企業吸納從業者、持續擴大從業規模、積蓄發展潛力,對高端人才進行實戰培養和鍛煉;四是帶來旅游經濟滾動發展,多年來,旅游企業的利潤也為旅游業發展、國民經濟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五是成為旅游市場的穩定器,中國旅游業即便遭遇新冠疫情這種重大災難,也具備迅速恢復的市場基礎。
但總體來說,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旅游企業普遍規模偏小、質量不優、實力不強、影響力弱。這和社會發展階段有關,也受旅游業文化含量與創新研發能力影響,還和全社會對企業的關注度息息相關。尤其是后者,很少被重視、被反思。長期以來,政府主導是旅游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學界也大多在宏觀導向、政策體系籌劃、解讀、執行等方面花費了較多精力,導致全行業都對大概念、大趨勢、大市場等十分關注,而對市場主體的生存環境評價、發展困難跟蹤、運行規律總結、實踐案例解析等更處前沿、更在一線、更與市場短兵相接的重要領域熟視無睹。這一點已經成為中國旅游業發展的一大缺陷。
進一步重視市場主體,優化其發展力,強化其持續力,提升其應對力,發揮其影響力,是加快實現旅游業內循環的重要課題。這需要多方面努力。一是在政策出發點和著力點上,要更多考慮企業能否受益、能否承受、能否借力、能否實踐,而不是把重點放在直接刺激社會消費、規劃業態布局、展望產品數量、提出數字目標等領域;二是要有更多針對旅游企業的研究成果,除在環境、效益、市場、生態等外部領域外,還要在商業模式討論、企業文化解讀、內部構架分析、管理方式總結等方面著力,給予企業更多的市場性參考資料和未來發展指導;三是構建更好的人才培養體系,針對投資、運營、營銷等市場短缺人才,在全社會層面提升培訓能力、增強培訓力度;四是認可、激發、保護、傳承企業家精神,根本性承認企業家的重要性,樹立鼓勵企業家發揮作用的輿論導向,精準提煉優秀企業家的各種群體稟賦要素與各自不同表現力,持續培養代際企業家群體等,都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
發揮市場主體作用,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快構建旅游企業的市場化分工體系。現在基本上企業無論資本屬性、規模大小、基因特征、模式優劣,都大多在同一市場上進行同質化競爭,這就帶來一種“內卷”——市場看似繁榮,實則混亂,不利于提升效率,不利于加快創新。改變這一點,需要國家進行進一步引導。首先,要摒棄旅游業發展“充分市場化是唯一靈丹妙藥”的觀點,認清旅游業市場主體的結構與分工需要更科學的頂層設計與路徑規劃;其次,要出臺精準政策,引導市場形成不同能力層次、不同供給角度、不同流域位置的企業群系;再次,要發揮大企業集團作用,讓其在旅游業的國家戰略推進、基礎平臺建設、產品創新研發、人才集聚輸出等方面發揮率先引領的作用;最后,直接培育,對一些基礎好、潛力大、模式新、人才強的中小企業,可以提供更多的扶持和傾斜,促使一些在構建市場分工體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企業能夠盡快發育。
(作者系該院常務副院長,華僑城旅游投資管理集團總裁;收稿日期:20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