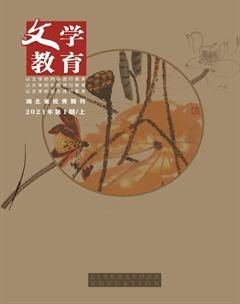鄧一光“深圳系列”小說的景觀書寫與城市想象
鐘瓊
內容摘要:城市景觀是經過作家創造的“第二自然”,融合了作者的審美、想象和價值判斷。鄧一光在他的“深圳系列”小說中呈現了許多富有深圳地域特色的都市景觀。作者進一步思考都市與都市人的生活,通過對都市的空間想象、都市場景的描摹和真實再現等方式與景觀對話,表達出都市人身份認同的困惑、都市歷史記憶的斷裂、都市人的焦慮和生存困境等主題,完成了他對深圳這座城市的想象和敘述。
關鍵詞:鄧一光 小說 景觀 城市想象
“景觀”一詞最早作為生態學和地理學概念出現,泛指風景或景色。從人文地理學的視角來看,“風景是一種意象、一種心靈和情感的建構”。[1]文學中的城市景觀既不是單純的花草樹木,也不是生活實際景觀,而是經過作家創造的“第二自然”。對居住之地的個體經驗和體認成為作者審視城市的一個視角。作家筆下的地域景觀承載著記憶,想象和生命感受。這些地域景觀融合了作者的審美,投射了作者隱蔽的內在精神世界。作家對城市的再創造過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和價值判斷,為作品中人物的行為發生創造了一個想象的空間。鄧一光在他的“深圳系列”小說中呈現了許多富有深圳地域特色的都市景觀,并通過小說主人公表達了他對深圳都市景觀的感知和認識,完成了他對深圳這座城市的想象和敘述。
一.身份認同的幻象與困境
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無數漂泊在這個城市的打工者渴望真正擁有“深圳人”的身份。可是,又怎樣才算是真正的“深圳人”呢?擁有戶口?亦或房產?
在《離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安潔帶著成為“深圳人”的渴望搬到離市民中心最近的高級公寓。她甚至幻想著在市民中心舉辦自己的婚禮。她覺得住在深圳最中心、最高貴的地方便實現了成為“深圳人”夢想,而當她得知廣場清潔工在三年零七個月的工作中一次也沒有進入過市民中心時,清潔工的一句“我不是深圳人,從來不是,一直不是”[2]68將她居住在城市中心的榮耀和成為“深圳人”的幻夢瞬間擊碎。如果說清潔工代表著對自己的身份有著清醒認知的底層民眾,那么,受過良好教育、擁有較好經濟條件的“安潔”們,他們將身份的確認依附于對城市空間的占有。這無疑也是一種巨大的景觀幻象。
鄧一光將城市看作是一座森林,在這座城市森林,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自然景觀也是鄧一光感知城市的最直接的方式。“我對深圳的整體認知可能跟別人不一樣,對這座城市的發展史無法形成個人經驗構成寫作行為。我最早認識的是氣候、植被、動物,然后是人。”[3]
在《簕杜鵑氣味的貓》一文中,蓮花山公園中的植物們被賦予了生命的氣息,會疼痛,會散發氣味,它們“和人一樣,有的聰明,有的笨,有的內斂,有的張揚,它們性格不同,但氣味同樣活躍。”[4]51這些植物和這座城市的人的命運一樣,“公園剛建時沒有經驗,植物選種不對,比如桂花樹耐熱性差,大面積種植很難養護,這些品種要不斷置換,就像很多早年來這座城市闖蕩的人,他們也是選種不好的植物,他們在這里生長過一段時間,要么死掉,要么遷移走。”[4]47小說主人公羅限量便是其中一員。他在深圳生活了18年,他熱愛自己的工作,把那些大王椰、金山葵、大葉榕、散尾葵當成自己的兄弟姐妹、街坊鄰居,甚至是兒女。他對自己生活的城市有習慣和依戀,可是,他還是要離開,他已經33歲了,“他得結婚生子,把日子過起來,這個,在深圳辦不到”。[4]48他就像是遷移到這座城市的一株植物,最終不得不面對需要移栽到其他地方去的命運。小說充滿了隱喻意味,樹木移植成功的艱難隱喻了諸如羅限量這類人融入城市的艱難和困境,成為了“有意味的風景”。[5]
二.歷史記憶的打撈與“尋根”的困境
深圳是一座新興的現代化都市,不具備北京、上海那樣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短短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使它似乎少了歷史的厚重感。但是,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歷史和記憶。鄧一光從武漢移居深圳,移居地激發了他強烈的好奇心。“我想看看深圳人埋在什么地方,看看那些逝者,他們來自哪兒,怎么安葬。墓地是血緣、信仰和歷史的集中地,是一個地方的歷史,有墓地的地方才有前世來生。”[3]79帶著對這樣的困惑,鄧一光從梧桐山開始,沿著地理學上的深圳河走了一趟,并把他對深圳的現在與過去的思考和感知寫進了《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開的》和《深圳河里有沒有魚》兩個短篇。
《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開的》以梧桐山作為故事地點背景,小說開篇就談到“我”到梧桐山的緣由——為“深圳的原地屬花木是不是都是源于梧桐山?”這個問題來尋求答案,通過主人公歐陽先生的講述帶出了一段“逃港客”的慘痛記憶。這一段個人角度的瑣碎敘述,拼貼出當年大逃港歷史的真實細節和面貌。“花木有自己的家。它們有自己出生的地方。它們不會告訴別人。”[2]72當年不顧生命危險逃離家鄉的逃港客,現在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而失去女兒的創傷和那段歷史一起永遠的沉淀在了個人的記憶里。從“現在——過去——現在”,小說在承載著歷史記憶的梧桐山這一景觀空間,表現了時間的縱深感,呈現出滄海桑田的歷史感,也表達出對個體命運的感嘆。
小說《深圳河里有沒有魚》充滿隱喻,富有先鋒色彩。“我”一直在尋找林若說的有著渾圓腦袋、像孩子一樣笑的魚,可是“我”最終并沒有在這條城市的河流里找到魚,連林若也是“我”想象出來的而已。最后“我”縱身躍入河中,成為了那條魚。
這是一部可以從多個角度解讀的作品,是一個城市的寓言。無處尋覓的魚表達了對當下城市環境生態惡化的憂慮,客家女孩林若已逐步消失的客家特征是對傳統消逝的感傷,養蜂老人的講述是對“逃港”歷史的記憶打撈,母親的溺亡,亦或可理解為尋根的困境和文化的斷裂。
在對城市歷史的回望中,作者表達出對已經消逝或正在消逝之物的思索與無奈,“很多東西不在了,消失了,比如鴿哨、鐵環、胡琴和竹笛聲、齊額的劉海、明亮的眸子和干凈的微笑,它們過去存在過,如今消失了,有關它們存在時的內容已經變成了傳說,……”。[4]66這些逐步消逝的歷史和傳統,使城市失去了縱深感,變成了沒有歷史感的個人化生存,從而也引發了作者進一步對城市的集體認同的思考。“逐水而居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原則,一個聚集地沒有自生水源,母親河被肢解成這樣,如何超越現實?飲水者思源,深圳人無源可思,這座城市本身就不認同自己,在集體認同上都是可疑的。”[3]
三.現代都市的生存焦慮和困境
在鄧一光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耳熟能詳的深圳地名就直接鑲嵌在小說標題當中,世界之窗、市民中心、萬象城、龍華廣場等等,這些地名某種意義上構建了鄧一光筆下的深圳文學地圖。毫無疑問,這些都市景觀都是作者精心選擇的結果,它們進入作者的視野,并被賦予了某種象征意義。
萬象城是“深圳最值得炫耀的地方”[2]127,它有琳瑯滿目的商品和燈火輝煌的耀目,也有德林的容身之處——一間小小的雜物間,甚至一段相互安慰的感情。但這一切并不能阻止德林想要回家過年的愿望。德林想念他的母親、妻子和女兒,甚至牽掛那個不懂事的哥哥。在一次又一次被客觀現實打敗,一次次地糾結徘徊之后,德林在大年三十獨自走在了行人寥寥無幾的街上。小說通過過年回不回家這個問題,映照出一個底層群體的辛酸和卑微。萬象城是輝煌和耀目的,德林熟知它的細節,但是萬象城從來不會關心德林的命運。就像深圳這座城市,無數個“德林”們像螺絲釘一樣,帶動著深圳這座城市的發展,卻無法融入這座城。“城市從來沒有成為人們生活的侵犯者,它是人們共同的想象體和誘惑源,人們沖著它的光芒來,在這里實現自我,但它沒有成為人們愜意的生活地。”[3]
在《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同樣讓我們看到了底層工作者的焦慮、迷茫和辛酸。小說中多次提到“天橋”,下班時,在龍華的打工者們像潮水一般地涌出廠門,“他根本看不見她。數萬名紅色POLO,加上數萬名藍色POLO,再加上萬名白色POLO”,[2]129個體的人被消解于群體之中,人成為了不同顏色的符碼,散失了人的本質屬性。這也深刻地反映了流水性工人在刻板的生活環境下被現代工業異化的可悲。“廣場”是小說中另一個有意味的景觀。無數男女青工們聚集在廣場跳舞。廣場是一個城市的公共空間,在這個人人可享受的開放空間里,人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自由和平等。在廣場跳舞是底層務工者為爭取幸福生活和融入這座城市的努力。“什么時候不跳樓了,就讓你們跳舞”[2]135也讓我們看到這種努力背后的辛酸嘆息。
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和記憶都是由多樣化的個體感受積淀而形成。每一位作家對于一座城市的想象和敘述參與了這座城市的文化記憶構建。鄧一光“深圳系列”小說通過呈現和塑造各種景觀,使深圳這座城市不是單純作為物質客體或背景存在。它們或訴說中人心中的隱秘話語,或承載著這座城市的人的集體記憶,或解讀出城中人的焦慮。作者進一步思考都市與都市人的生活,通過對都市的空間想象、都市場景的描摹和真實再現等方式與景觀對話,表達出都市人身份認同的困惑、都市歷史記憶的斷裂、都市人的焦慮和生存困境等主題。作者通過人物與景觀的對話,挖掘出城市與人物命運的聯系,構建了屬于作者想象中的深圳城市形象,也豐富了中國城市的書寫。
參考文獻
[1]段義孚.風景斷想[J].長江學術,2012(3):78.
[2]鄧一光.深圳在北緯22°27'—22° 52'[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
[3]張克.鄧一光的城市書寫[J].名作欣賞.2017(31):79
[4]鄧一光.深圳藍[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6
[5]施暢.真實的風景和風景的政治 [J].文藝研究2013(4):37
基金:廣東科技學院2019校級科研一般項目“廣東作家的城市想象與敘述”(GKY-2019KYYB-91).
(作者單位:廣東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