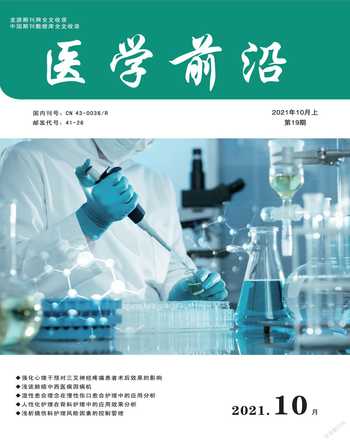通腑法在內科病之臨證一得
陳凱 徐月利 白振南 陳振廣
關鍵詞:內科病,通腑法,中醫藥療法
通腑法亦即“下法”,是中醫祛邪治則之一。早在《內經·素問》一書中已有記載,如“中滿者,瀉之于內”“盛者瀉之”“留者攻之”。醫圣張仲景就是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創制了寒下的“大承氣湯”、溫下的“大黃附子湯”、峻瀉的“白散”“十棗湯”和潤下的“密煎導”以及下法與清熱法并用的“大黃黃連瀉心湯”和下法與活血化瘀法并用的“抵當湯”等經方凡36首之多,至今無論中西醫均廣泛用之于外感時病與各科雜病之治療,有無可替代之卓效,其作用以單味藥大黃及承氣湯類方尤為突出,在臨床上發揮著重大作用[1]。在內科病癥搶救過程中,由于其病因病機各異,搶救期間極易發生胃腸功能紊亂,可出現大便干結或便溏粘滯不爽、上腹脹痛、惡心、嘔吐、厭食、舌苔厚膩等癥。據筆者之臨證經驗,可在治療原發病之基礎上,應用通腑法以蕩滌“中滿里實”之邪熱,常收“釜底抽薪,治病求本”之捷效,可使病情迅即緩解,從而提高了搶救成功率。有感于此,誠與同仁分享,以冀造福眾患。現將筆者以通腑法在內科病之臨床應用體會略述如下,以正同仁,不吝指教。
1.病例
1.1 急性肺炎
肺炎多屬風溫范疇。肺與大腸相表里,痰熱壅肺,既可灼傷肺絡,又可移熱于大腸,致使腸熱津傷,燥屎內結,腑實氣壅,濁氣上逆而增喘滿。采用通腑法以“釜底抽薪”使肺氣得以肅降,則喘息自止。如王某,女,36歲。寒戰發熱,右胸痛,咳吐鐵銹色黃稠痰4天,口渴喜飲,溲黃赤,便結3日未行。查體溫39.5℃,呼吸喘促,鼻煽,舌紅苔黃燥,脈滑數。白細胞計數20.0*109/L,嗜中性粒細胞比率90%,胸片示右下肺片狀密度增高陰影。診為大葉性肺炎。證屬痰熱阻肺,腑有熱結。治宜通腑瀉熱,肅肺平喘。擬麻杏石甘湯合宣白承氣湯加減:麻黃 杏仁 桔梗各10克 瓜蔞25克 石膏 60克 金銀花 連翹各30克 元參25克 甘草10克 大黃(后下)15克 水煎服。藥后日解褐色稀水便3次,2劑后即熱退脈靜,呼吸平穩,咳減痰少,胸痛消失。腑氣雖通,但痰熱未盡,前方減大黃量為6克,加黃芩10克,繼服5劑后胸肺透視正常。
1.2 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變化主要是肝細胞充血、腫脹、壞死、匯管區間隙細胞浸潤、水腫及不同程度的膽汁淤積,甚至形成膽栓,導致膽紅質的潴留。瀉下通腑乃中醫歷來公認治療陽黃、急黃行之有效之大法,而以大黃為首選,以其苦寒之性,沉降下行,能清熱瀉火、通下退黃、涼血解毒、化瘀止血,可作用于重癥肝炎之多個病理環節,故其應用指征不僅在于有無腑實便秘,舉凡濕、熱、火、瘀諸類邪毒壅盛者皆可用之。由于大黃有抗病毒、利膽、消炎之功而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都有一定的療效。一般常用方為茵陳蒿湯、大黃硝石湯及柴胡茵陳蒿湯等,取方中大黃之通腑作用。在一些重癥肝炎,特別是在病情進展期,病人全身急驟發黃,發熱,腹脹,嘔惡不食,二便不利,肝功能顯著損害,藥后即可獲二便通利量多,病情好轉。如陳某,男,56歲。全身重度黃染,發熱,肝區不適,腹脹,惡心,納呆,乏力,溲紅赤而少,便秘4日未解,脈弦數,舌絳苔黃厚而膩。治以通腑瀉熱,涼血解毒,逐瘀退黃。予茵陳蒿湯加減:茵陳30克 萹蓄30克 生梔子10克 郁金12克 虎杖30克 赤芍15克 白茅根30克 大黃(后下)25克 水煎服。并用肝太樂及維生素等保肝藥物治療3天,大便黃褐而稀日4次,尿量增多,隨之熱退,腹脹減,食知味,精神好轉。原方進退繼續服用月余,隨訪前癥未見發作,體質亦見恢復,無其他不適。說明通腑瀉毒能迅即控制病情之發展。
1.3 急性細菌性痢疾
大黃能抑制痢疾桿菌而常用于治療痢疾。本病證屬大腸濕熱者居多,據“通因通用”“痢無補法”之論點,宜通腑為治。一般常用大黃黃連瀉心湯加味以蕩滌積滯,使細菌及其毒素迅即排出體外。如劉某,男,26歲。晝夜大便一、二十次,兼夾膿血,小腹急痛,里急后重,痛苦異常。擬大黃黃連瀉心湯加味:黃連6克 黃芩12克 木香10克 生白芍30克 甘草10克 大黃(后下)15克 服1劑,即排便爽快,便數大減。守前方連服3劑而愈。
1.4 乙型病毒性腦膜炎
乙腦一病屬暑溫范疇,三焦熱熾、陽明腑實、邪陷心包,常需通腑泄濁。此病屬熱極生風,熱為本,風為標,宜瀉熱息風,陽明為十二經脈之海,“六經實熱,總清陽明”,往往用下法后腑通熱退神清痙止,病情趨于好轉,從而降低死亡率,減少后遺癥。如安某,女,8歲。以高熱頭痛、抽風、昏迷而住院,體溫40℃,便秘。查頸項強直,布氏征、克氏征、巴氏征均陽性,脈滑數,舌絳苔黃厚起刺。診為乙型腦炎。經吸氧、輸液并用安宮牛黃丸鼻飼2天未效。后加枳實18克 大黃(后下)15克 芒硝(沖服)6克 ?煎湯送服安宮牛黃丸1丸,排褐色稀便甚多,熱臭熏人,日解3次,次日體溫降至38.5℃,諸癥好轉。減芒硝繼服4天,大便暢行,舌脈證日趨正常而痊愈出院,無明顯后遺癥。
1.5 心系疾病
心系疾病包括冠心病、肺心病、高心病、高血壓病、動脈粥樣硬化等常見之老年病。通腑法適宜于長期過量進食膏粱肥膩,熱結于內,除具有原發病的臨床表現外,均兼有不同程度的頭眩目赤,煩躁不安,腹脹不適,大便干結難解或黏滯不爽等腑實證。用下法能通腑泄濁,推陳致新,調理氣血,暢達氣機,增進食欲。尤其對病情較重或多臟器功能衰竭,通腑護臟以阻斷其病理環節,提高搶救成功率,降低死亡率。如梅某,男,42歲。因急性心肌梗死收入院,經吸氧、輸液等搶救措施,3日后脫險。但“心衰”經西醫常規處理數日效不著。仍表現氣喘,心悸,端坐呼吸,咳痰量多色黃,動則汗出喘甚,頭暈,心胸煩悶,徹夜不眠,腹脹、納呆、口干、溲黃少,便結7日未解。查其唇甲紫紺,頸靜脈充盈,肝大,腹滿拒按,兩下肢腫甚,按之如泥,舌紅紫而胖大有齒印,舌中苔黃厚而干裂,脈數按之無力。證屬臟病(心氣陰兩虛)及腑(陽明腑實),血瘀痰阻。治宜通腑護臟,散瘀化痰。予承氣生脈湯加減:黃芪30克 玉竹20克 黨參15克 麥冬15克 五味子10克 枳實15克 葶藶子30克 白茅根 30克 丹參15克 赤芍15克 地黃30克 元參25克 厚樸15克 大黃(后下)15克 芒硝6克(沖服)水煎服。藥后6h許下燥屎夾褐色稀便1便盆,熱臭灼肛,大便下后而小便漸利,尿量增多,當日量約600ml,氣通壅除,腹脹頓減,面目水腫漸消,咳喘隨之而緩,即能間斷高枕臥位入睡,諸癥隨即大為減輕,上方去芒硝繼服。后以原方隨證加減,服用1月余,諸恙悉退,病情逐日好轉直至出院。此“難治性”心衰之“病”而有腑實之“證”,以“通腑護臟”為法而提高了療效,縮短了病程。
1.6 腦溢血
腦溢血后,除心血管、神經系統、呼吸系統等出現障礙,消化系統同樣會紊亂。張潔古“三化湯”首次在“中風”應用該法,“中風外有六經至形證,先以加減續命湯,隨癥汗之;內便溺之阻格,予以三化湯下之。”后各家論述強調了平肝潛陽、滋陰息風、滌痰開竅,對下法重視度不足。近年來,臨床實踐證明,通腑法可減輕顱內壓,改善腦水腫,對于中風者具有重要作用。例如王某,女,76歲,由于過度勞累突感頭部劇痛,伴嘔吐、惡心,送院急診治療。神經科會診后確診為腦溢血,入院一周持續高熱,T為38-39℃,神志昏迷,痰液壅阻氣道后行氣管切開,邀中醫會診,患者昏迷且痰液間聲漉,面紅耳赤,腑氣不通,舌質紅,舌苔黃膩而厚,脈弦有力。中醫指出“內風之氣,多從熱化”,即風從火出,病邪鴟張,正氣尚未衰退,予以滌痰通腑之法。但治其熱,風即自消,遂取三化合三甲復脈施治:牡蠣30克 炙鱉甲30克 丹參30克 石菖蒲15克 茯苓15克 炙龜板15克 天竺黃12克 制南星12克 ?枳殼10克 ?遠志6克 甘草6克 大黃15克(后下) 芒硝10克(分沖) 2劑。云南白藥2克,分四次鼻飼。上方服用1劑后,患者解醬色熱臭稀便一盆之多,次日體溫隨降,神志漸清。二診時呼吸節律均勻,舌苔厚膩漸化,脈象緩和。上方去大黃、芒硝,加瓜蔞30克、玄參15克,服用2劑后,諸癥悉減,繼用原方進退調治1周后,日漸好轉。可見通腑法用治中風一病,最宜于閉證與熱證,同時配合滌痰開竅、祛瘀止血、滋陰息風之法,方可獲取滿意之療效。
2.體會
《內經·五臟別論》言:“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六腑“以通為用”“以降為順”,保持六腑之暢通狀態符合其生理特點,也是機體健康之基礎。《內經》認為“下法”之適應范圍是“中滿里實”、熱病“其滿三日”入里、血瘀等證。下法是通過蕩滌腸胃內之實質病邪,使滯留在腸胃內之燥屎、實熱、宿食、冷積、瘀血、痰結、水飲等病理產物排出體外,從而使病證得以消除或緩解。其瀉熱通下、解毒通下、逐水通下、祛濕通下、消積通下、活血通下等功效之方劑可為代表。清代溫病大師葉天士、吳鞠通等醫家善用“下法”[2]。二者在吳又可“溫病下不厭早”之基礎上,創立了“急下存陰”“增水行舟”等治療溫病之大法,進一步擴大了“下法”之臨床應用范圍。但凡燥屎內結,腑氣不通之各科急慢性病證,皆可通腑泄濁為法,亦即“釜底抽薪”之義,用之得當,常達“邪去正安”“柳暗花明”之效[3]。其作用以單味藥大黃及承氣湯類方表現尤突出。
大黃,其味苦性寒,入脾、胃、大腸、心包、肝經,具悍利之性,擁“將軍”之美稱,既走氣分,又入血分,沉降下行,通利二便,攻逐力強,瀉熱蕩實,涼血解毒,化瘀止血,利膽退黃,推陳致新,安和五臟,有“將軍除暴安良”之功。其成分主要含蒽醌衍生物。藥理學研究示:大黃產生瀉下作用之有效成分乃蒽醌甙,其瀉下作用有二:一是通過抑制鈉鉀離子從腸腔轉運至細胞,使水分滯留在腸腔而促進排便;一是通過刺激大腸,增加其推進性蠕動而促進排便,作用較緩和,藥后6小時左右排出軟泥狀糞便或粥狀稀便,一般緩下一次后即止。其瀉下之特點是不妨礙小腸對營養物質之吸收,能排出、防止吸收細菌及腸道毒素,有減輕內毒素血癥之作用,從而減輕心腦肝腎等重要器官組織之損害,并可減輕消化道和中樞神經系統之癥狀,對遏止病變進展,促進病變之恢復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可達到“惡穢一去,邪毒從此而清,證脈從此而退”之目的[4]。大黃清熱解毒之功居群藥之首,亦與其抗菌抗病毒作用有關。實驗證明,大黃對葡萄球菌、溶血性鏈球菌、白喉桿菌、肺炎雙球菌、傷寒、副傷寒桿菌、痢疾桿菌、淋病雙球菌、真菌及流感病毒等均具有不同程度之抑制作用,并有抗病原、消除炎癥反應、降低高氮質血癥及增強細胞免疫作用,體現出大黃之清熱涼血解毒功效;大黃具有保肝利膽、利尿和調節植物神經系統等作用,增強胃腸道運動功能,增加腸血流量,改善腸道血液循環,降低毛細血管通透性,促進腹膜吸收,加強血液凝固,對消化道出血有止血作用,能升高血小板,改善微循環,緩解殘余腎高凝狀態,糾正貧血,延緩慢性腎衰竭之進展以及抗腫瘤等作用,體現出大黃之逐瘀生新功效[5]。這是“六腑以通為用,腑病以通為補”之實驗依據,也是通腑法治療多種疾病屢獲良效之道理所在。
筆者臨證擅用大黃攻邪扶正,積驗有年,體悟頗深,淺見有三。
(1)重用大黃,蕩邪安正,力挽危局
大黃,乃中醫“下法”中之主將,攻下劑之主藥。考《神農本草經》言其性味及功用為:“味苦寒,主下瘀血,血閉寒熱,破癥瘕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谷,調中化食,安和五臟。”此說明在漢代已對大黃有充分之認識,故《湯液本草》亦載:“大黃,陰中之陰藥,泄滿,推陳致新,去陳垢而安五臟,謂如戡定禍亂以致太平無異,所以有將軍之名。”可謂大黃之知音。大黃乃一霸藥,蕩實滌熱,急下存正,用之得當,有“推陳致新”“安和五臟”之功。真懂大黃,斷不會以其為峻瀉而畏之,能神用之者,方為真中醫。大黃實乃蕩滌之“將軍”,具悍利之性,可單刀直入,無堅不摧,斬關奪隘,將腑內污垢邪毒,一蕩而盡。無論“邪實”與“正虛”之孰輕孰重,“有是證則用是方”“急則治其標”,不必為“正虛”所囿,應放膽投之。危急關頭,生死一線,若能重用大黃,方顯急下存正之關鍵。臨床常以大黃開路,配合枳實、厚樸等行氣之品,藥后矢氣一轉,大便通解,腹脹旋消,諸癥隨減[6]。前人雖有“千寒易解,一熱難除”之喻,但遇各種急慢性發熱病證,久羈不退,當謹守“熱”“瘀”“濁”“閉”之病機,無論有無大便不通,均可在相應之方劑中配用大黃,以清熱解毒,通腑瀉熱,使熱毒從下而解,可獲事半功倍之效。但“亦要驗之于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且無論苔之厚薄,只要舌中苔黃而干為有熱象,或下后邪熱宿垢未盡,即可放膽用之,“可謂萬無一失”,惟酌情增損大黃之量而已。但凡辨病、辨位、辨證明確,用之果斷,穩、準、狠、快,可收“釜底抽薪,治病求本”之捷效,往往可使急危重癥患者頓起沉疴,轉危為安,化險為夷。
(2)以通為補,推陳致新,卻病延年
著名金元四大家之一張從正,自成攻邪一派,是“攻邪派”與“攻邪”理論之鼻祖,擅長攻下,主張“以祛邪為主,邪去正自安”,清代名醫翟玉華認為,下法是“去其所害,而氣血自生,借攻為補”,說明大黃之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有通之一面,又有補之一面,可奏“有故無殞”之效。大黃為推陳出新、間接扶正之有效藥物,是攻堅祛邪之上品,寓補于攻之良藥,既走氣分又入血分,一藥多用,適用廣泛,切勿局限于承氣湯系列治療陽明腑實證范圍,否則會重蹈“大黃救命無功”之憾。可以說掌握和用好大黃乃中醫之基本功。在當今營養過剩之年代,大黃是一把利器,既通便又泄濁,為祛邪扶正之不二選擇。在氣、血、陰、陽、臟腑各類虛證中,只要具備腹脹、便秘、腸中有宿便者,均可配用或單用大黃,而年老體虛者常服大黃,可卻病延年。如便秘一病,雖不危及生命,但可引起或加重某些病證,加速肌體衰老,因人之大腸中寄居大量細菌,其所產生之大量毒素,經腸壁細胞吸收,可導致慢性中毒,從而引起一些重要器官如心、腦、肝、血管等病變,直至肌體衰老和死亡。故大便之暢通無疑可減少大腸中有毒產物之蓄積與吸收,減緩肌體衰老[7]。臨床和實驗研究表明,大黃之藥理作用已超越了傳統之功用,其應用范圍正日益擴大,不僅在急危重癥之診療中起著重要作用,且在治療虛證方面正顯示著威力,是一味具有廣闊前景之重要藥物。雖有“久病多虛”之論,但宜首重辨證論治,切莫亂投補益之劑,否則補其有余,實其所實,往往犯“虛虛實實”之戒。醫圣張仲景善用大黃?蟲丸治血痹虛勞,《醫方考》用百勞丸(主藥大黃)治療勞瘵積滯,均為大黃治療虛證之先例[8]。蓋大黃有蕩滌瘀濁、暢達氣機、推陳致新、安和五臟、以通為補之功,老年人可堅持經常服用大黃,令大便通調,痰脂減少,穢濁下泄,氣血流通,藥后自感肚腹輕松,納谷覺馨,精神振奮,從而增強體質,降脂減肥,延緩衰老。特別對老年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腦血管病、高脂血癥、動脈硬化、心衰、腎衰及肥胖癥患者,大便不暢,更為適用,既可通腑泄濁,活血化瘀,又有降壓、降糖、降脂等作用[9]。大黃目前為治急、慢性腎衰竭之圣藥,針對“本虛標實、虛實夾雜”之病機特點,以大黃逐瘀生新、泄濁排毒,既可“內服”通利腎絡以泄其內蘊之“溺毒”,使邪有出路,又可“灌腸”通腑瀉濁以促進毒素從腸道排泄,可將瘀濁溺毒及時由二便排出,從而減輕健存腎單位之負荷,改善腎功能。但在臨床中,常見以體弱氣虛為由,對老年人及諸多慢性病證忌用大黃之類苦寒瀉下藥物,卻忽略了“六腑以通為補”之原則,正如前人所謂“寓通于補,方為圣補”,誠乃經驗之談[10]。
(3)妙用大黃,寓通于補,進退有度
臨證活用大黃,不囿于常,善用之機巧在于把握方法。大黃之用,巧在用量,妙在炮制,貴在配伍[11]。若悟透大黃用藥之理,用之得法,可謂善將取才,勝人一籌。大黃可分生、制、酒洗、炭藥四種:生藥味苦性寒,以攻積導滯,瀉火解毒力專,多用于熱積便秘和熱毒壅盛之證;制藥味苦,性寒偏平和,瀉下力遜,清熱化濕力勝,多用于濕熱內阻之候;酒洗藥味苦微辛,性寒稍平和,以活血行瘀力強,多用于瘀血證;炭藥味苦微澀,性寒偏平,以和血止血力強,多用于出血證。雖大黃之加工不同,量效有異,但貴在靈活掌握。通常在相應處方內加大黃1~3克,起疏通經絡、活血利滯、健胃助消化、排除瘀積、催化藥物等多種作用,目的為推陳致新,并非專為滌腸、掃蕩宿積糞便[12]。論投與標準,當隨其年齡、體重、強弱而變,不分男女(孕婦忌用),可任攻下者,以藥后排便“快利”為度,但腑實熱結者例外。古有“要想長生,腸中長清”之說。取一味大黃研粉泛丸,名獨圣丸,每次3克,日2服,可作保健藥,有降脂、減肥之效。大黃酒制,九蒸九陰干,研細末,水泛小丸,名清寧丸,每服3~6克,每日1~2次,治肝胃火盛之習慣性便秘。也可每次3克,早晚分服,以減肥養生保健,歷經實踐驗證,十足珍貴。大黃重用輕用則效用不同,如0.5~1克引經,2~3克化食,3~6克輕瀉,10~15克瀉下。小劑量引藥入腎,中劑量逐瘀泄濁,大劑量急下通腑,其最高量在30克左右,以腑通為度。首服應從小劑量2~3克開始,再按耐受情況逐漸調整劑量,若致瀉不明顯可與消導、理氣之屬配合應用。大黃能攻善守,具有雙向調節作用,量大則瀉,量小則斂,生大黃瀉峻,熟大黃次之,酒大黃又次之。大約生大黃通便之作用產生在4~6小時,熟大黃在6~8小時,酒大黃在8小時以上。便前部分病人出現腹痛,便后則自行緩解,不必作特殊處理,腹痛較甚者,可配合白芍30克、甘草10克同煎以解之。脾胃弱者,宜飯后服,伍以山藥可緩大黃礙胃之弊。服后其汗液和尿液均可發黃,屬正常現象。大黃可與諸藥同煎30~35分鐘,不必“后下”,后下不但通便力量較弱,且清熱解毒之力亦差。腎功能不全,用生大黃降濁時,應保持大便日2~3次為宜。另外,使用大黃亦應注意其禁忌癥,如表證未罷,血虛氣弱,脾胃虛寒,無實熱、積滯、瘀結,以及胎前產后,均應不用或慎用,如大黃之瀉下成分尚能進入乳汁之中,引起嬰兒腹瀉,故對大黃亦“不可忽而輕用。”
參考文獻:
[1]徐晴, 王宇凰, 鄭蓉,等. 益腎泄濁通腑法治療慢性腎功能衰竭的經驗總結[J]. 醫藥界, 2020,18(5):22-23.
[2]劉鋒. 盧云教授運用通腑瀉熱法治療急性胰腺炎驗案舉隅[J]. 全科口腔醫學電子雜志, 2019, 6(3):1.
[3]修春英, 林貽照, 曾屹生,等. 行滯通腑法治療肝胃郁熱型胃食管反流病30例[J]. 江西中醫學院學報, 2019, 31(06):30-32.
[4]李澤虹,趙建更.通腑法在外科急腹癥中的應用[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2019,19(71):275+278.
[5]楊潔,韋緒性,李冀南.通腑法在重癥醫學科中的應用[J].中國民間療法,2019,27(07):40-43.
[6]韓文倩,臧運華.通腑法治療神經科疾病現狀[J].現代養生,2019(02):37-38.
[7]姜小剛,任鳳梧,曹蕊,蔣曉野.通腑降氣法治療心系疾病驗案4則[J].江蘇中醫藥,2020,52(09):56-57.
[8]劉超, 王銀平, 朱小亮,等. 益氣化瘀通腑法治療早中期慢性腎臟病的臨床研究[J]. 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 2021, 30(20):5.
[9]李昊天,謝晶日,孫志文.謝晶日以開郁通腑法治療胃食管反流病經驗[J].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20,44(08):719-722.
[10]劉鋒.盧云教授運用通腑瀉熱法治療急性胰腺炎驗案舉隅[J].全科口腔醫學電子雜志,2019,6(03):18.
[11]楊恩權, 李瑞. 李瑞教授運用通腑法針刺治療面部疾病舉隅[J]. 中醫臨床研究, 2019, 11(25):3.
[12]張溪,張偉,孫燕等.嶺南甄氏益氣清熱通腑法聯合針刺治療卒中相關性肺炎的臨床療效[J].實用醫學雜志,2019,35(05):818-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