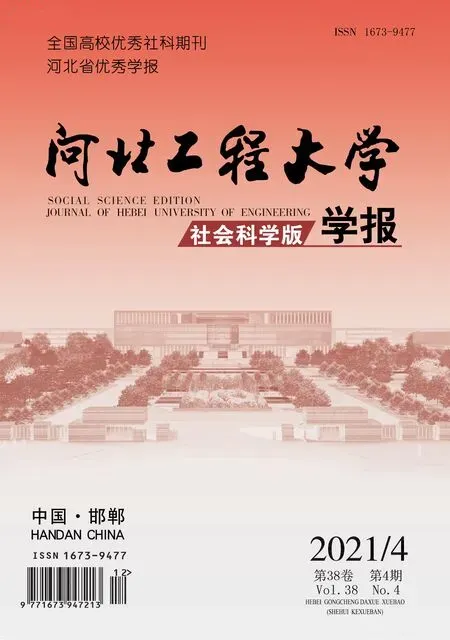高校英語線上課堂答題參與及其影響因素調查研究
王秀麗
(安徽建筑大學 外語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互聯網+”時代,在線教育對高校教學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各高校均開展了各種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實踐。在進行在線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教師們體會到學生課堂參與的積極性有明顯變化。具體表現在與線下課相比,學生線上課參與問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有明顯提高;愿意主動答題學生人數有所增加,且同學間答題互動也更頻繁。那么,究竟是線上、線下課堂哪些差異,影響學生課堂參與行為的變化,本文將進行相關探索性研究。明晰線上課堂的哪些因素能夠有效促進學生課堂參與,將有助于教師合理利用其中的積極因素,優化教學行為,助推課堂教學效率的提升。
一、文獻回顧
課堂參與包括行為參與、認知參與及情感參與。針對課堂參與影響因素,國內外學者進行了諸多探討。早期,研究者們對影響課堂參與的具體因素進行探討,這些具體的影響因素可歸為三方面:課堂環境因素如班級規模、座位安排、上課時間、課堂氛圍等;教師因素如教師行為、態度、性格、能力等;學生自身因素如性別、年齡、自信、焦慮、性格、態度與動機、準備等[1-5]。近年,學者們將社會心理學計劃行為理論用于預測和解釋學生課堂參與行為。研究者們認為主觀規范、感知行為控制及行為態度能夠顯著正向影響學生課堂參與行為[6-8]。事實上,主觀規范等同于外部因素包括環境和重要他人對學生參與行為的影響。感知行為控制及行為態度等同于學生自身因素對參與行為的影響。以上研究主要針對傳統線下課堂。針對線上課堂參與影響因素的研究方面,楊九民認為網絡課堂參與是學生基于網絡,在相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基于教師語音講解或視頻講授、通過意義討論與協商,完成基于任務或問題的認知、行為和情感轉變的學習過程。他同時提出,課堂環境因素如民主的課堂氛圍、合適的平臺工具,以及教師因素如組織多類型討論活動,明確的評價體系等教學行為可提升網絡課堂參與度[9]。冉新義結合社會性參與理論對遠程課堂的學生參與進行了研究,也提出網絡課堂參與涉及學生個體因素、教師因素和學習環境因素之間的互動[10]。鑒于目前針對線上課堂影響學生課堂參與的研究較為匱乏,本文將對此進行相關研究。
線上課的學習場景與線下課截然不同。依據媒介情景論,媒介、場景變化會導致行為變化[11]。結合課堂參與影響因素研究,線上、線下課堂差異研究以及媒介情景論可以得出:關于學習環境方面,線下課堂,學生在真實、嚴肅的教室環境中參與課堂學習互動;而線上課堂中,學生在相對輕松的非教室環境中參與學習互動。最為重要的是,由于互動媒介變化,線上課堂互動參與形式,從線下一對一交流模式轉變為一對多,甚至是多對多的多重互動模式。其次,教師因素中,教師性格、專業水平、教學能力等方面通常不會因為授課媒介變化而突變,但教師授課行為會因授課媒介變化而發生較大改變[12]。再次,學生因素中,學生性格、學業水平等不會因為學習媒介不同而明顯變化,但線上課堂學生的課堂參與焦慮感(即答題壓力感)[13-14]可能有明顯變化。同時,學生答題準備行為可能因學習媒介變化而產生較大變化。具體而言,本研究中的“答題方式”主要指從線下以學生舉手答題或集體答題為主的較為單一答題方式轉變為線上師生生生多元、多渠道的互動答題方式[15]。教師授課行為主要指教師的課中教學環節中的主要教學行為,包括教學組織、課堂提問、提問反饋等方面的行為變化[16]。學生答題壓力主要指學生在線上不同學習狀態下緊張不安等情緒感受方面的變化。答題準備行為主要指線上、線下不同學習環境中學生預習行為、搜集答案渠道和時間方面的變化[18]。
二、研究設計
(一)調查問題
1.學生線上課堂答題參與,與同類課程線下課相比,存在哪些差異?2.什么因素影響學生線上答題參與度?如果確有不同,哪些變化導致這種差異?
(二)調查對象
來自安徽建筑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及合肥師范學院非英語專業的365名有線下、線上英語課體驗的學生參與本次調查研究,其中男生211人,女生154人;2019級學生280人,2018級學生85人。為了確保學生對線上、線下課堂變化有更準確的判斷,本研究選取的調查對象滿足以下條件:1、線上課、線下課為同一系列課程,如大學英語1,大學英語2;2、該課程線上課、線下課的講授教師為同一人。
(三)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行設計“線上課答題參與及影響因素問卷”進行調查。問卷的具體設計過程如下:首先,挑選6位同學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發現學生認為的英語線上課變化最突出的方面。訪談的題目包括:1、你覺得,線上和線下英語課相比,自己及同學的答題參與,是否有所不同?2、如果有所不同,你認為可能是什么原因?3、線上與線下英語課,你感受到哪些比較明顯的變化,可以從老師、同學和上課環境等方面談一談嗎?根據學生回答提取高頻關鍵詞,如“提問次數多”“壓力小”“不尷尬”“同學互動”“學習通”等。其次,結合訪談與文獻研究結果,形成本次調查的具體維度。即從線上課堂教師授課行為變化、答題方式變化、學生答題壓力變化、學生答題準備變化等方面入手,設計了24個相關問題。再次,進行小規模預調查。根據學生反饋,剔除表達重復或表述不清的問題4個,保留20題。
正式問卷包含三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調查被試基本信息,包括年級、性別,教師線上授課方式等。第二部分是對學生線上答題情況的調查。第三部分是對線上課堂變化因素的調查。問卷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要求學生對符合自身情況的線上課答題感受描述進行選擇。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太同意,3代表不清楚,4代表基本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四)調查過程
問卷由各校外語學院的數位任課教師,通過班級QQ群發送班級學生。學生遵循自愿參與的原則,參與此次問卷調查。問卷在英語課程結束前的一至兩周發放(2020年6月中旬),問卷完成后,由任課教師收集并轉發。共收回問卷365份,其中有效問卷344份,有效回收率為94.2%。
三、數據分析
(一)問卷的信度和效度
首先,利用SPSS17.0對問卷的整體信效度進行檢測,結果顯示Cronbach α系數為0.877,說明問卷具有較高內部一致性,可信度高。其次,問卷效度主要考慮聚合效度與區分效度。利用SPSS 中的KMO 與 Bartlett 的球形度檢驗對問卷的整體效果進行檢測。KMO值為0.853,p值為0.000<0.05(見表1),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顯示各測量指標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說明問卷具有較好聚合效度。同時,利用各因子中具體測量指標的因子載荷計算AVE值,發現各因子AVE平方根值均大于該因子與其它因子間的相關系數(見表2),說明問卷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1 KMO 和 Bartlett 的檢驗

表2 區分效度(Pearson相關與AVE根值)
(二)學生線上課堂答題參與狀況及各影響因素描述性統計
1.學生線上課堂答題參與狀況
問卷第1、2題是對學生線上課堂參與答題的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如表3所示),兩題的均值皆高于3.5。通常情況下,五級量表等級評分的均值在3.5~5之間表示贊同[15]。3.8-3.9的均值說明絕大多數同學贊同,無論從個體角度而言,還是班級整體的角度而言,學生線上課堂答題主動性更強。

表3 學生線上課答題參與
2.各影響因素描述性統計
(1)教師線上授課行為
問卷3-8題是針對教師授課及提問行為變化的調查。調查顯示(見表4):各題均值在3.98-4.36之間,均高于3.5,說明絕大多數(約70%-86%)同學感受到并認同教師在線上課堂教學中的授課及提問行為有明顯變化。其中,同學們感受最明顯的變化依次是,“教師給予充分的預習材料”;“教師提問次數明顯增加”以及”教師不斷鼓勵答題”。

表4 教師授課行為變化
(2)線上答題方式
問卷9-13題是針對答題方式變化的調查。調查顯示(見表5):各題均值在3.95-4.46之間,均高于3.5,說明絕大多數同學認同,線上課堂的答題互動方式與線下課堂存在巨大差異。其中,學生感受到最明顯的變化依次是:”線上課堂答題渠道更豐富”;“評論區同學之間互動頻繁”以及“線上課堂評論區答題的便捷性”。

表5 答題方式變化
(3)線上答題壓力
問卷14-17題是針對答題壓力變化的調查。調查顯示(見表6):各題均值在3.70-4.17之間,均高于3.5,說明絕大多數同學認同,線上課堂的答題壓力小于傳統線下課堂。其中,同學們感受最深的是“線上課氛圍輕松”和網絡視覺匿名性帶來的“發言壓力小”。

表6 答題壓力變化
(4)學生線上答題準備行為
問卷18-20是針對學生線上答題準備行為的調查。調查顯示(見表7),各題均值在3.69-3.81之間,均高于3.5,說明絕大多數同學認同,線上答題準備更便捷、更充分。其中,同學感受最深的是“線上課堂答題,準備時間更充分。”

表7 答題準備變化
(三)答題參與與各影響因子之間的相關分析
為了明確四個因素與答題參與的相關程度,采用SPSS相關分析,探討四個因素與學生答題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如下,見表8。

表8 答題參與與影響因素相關分析
從表8中可以看出,學生“答題參與”與“線上教師行為”存在最為最顯著的關聯(相關系數為0.501**),與“答題壓力”和“答題方式”也存在中度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422**和0.355**),與學生的 “答題準備”存在弱相關(相關系數為0.235**)。
由于各因素之間也存在顯著相關,例如“答題壓力變化”和“答題方式變化”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476,“答題壓力變化”與“教師行為變化”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438,需要通過進一步分析來厘清各影響因素之間以及各因素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因此,采用SPSS偏相關分析進行進一步分析。
(四)偏相關分析
由于教師行為和答題方式屬于影響學生答題行為的外因,而答題壓力和答題準備變化屬于影響學生答題行為的內因。外因往往需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內因如”答題壓力““答題準備”很可能作為中介因素存在,影響”教師行為變化“和”答題方式變化“對”答題參與“的作用。鑒于以上考慮,需要通過偏相關分析來進一步確認各變量之間的關系。
偏相關分析(見表9)顯示,在 “答題壓力變化”作為控制變量時,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明顯變弱,說明“答題壓力變化”有可能在“教師行為變化”、“答題方式變化”與“答題參與”之間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將“答題準備變化”作為控制變量時,相關關系變化不明顯,僅稍微減弱,說明“答題準備變化”的中介作用不明顯。

表9 “答題壓力”“答題準備”為控制變量,自變量和因變量相關性變化
(五)回歸分析
為明確各因素對答題參與的影響程度,用SPSS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回歸方程(表10)顯示,這些因素可以解釋學生答題行為中31.6%的變化,p值為0.000,說明這些因素是學生線上課堂主動答題的有效預測變量。

表10 回歸方程模型及方差
回歸系數(見表11)顯示:“教師行為變化”和“答題壓力變化”“答題準備變化”是“答題參與”的有效預測變量,標準化回歸系數分別為0.356、0.203和0.097,p值均小于0.05,但“答題方式變化”并不能有效預測學生的答題行為。這印證了偏相關分析中“答題壓力變化“作為中介變量存在的結論。”答題方式變化“更直接影響學生線上答題時的壓力感,間接影響主動答題行為。

表11 回歸系數
四、討論
(一)調查結果表明,線上課堂,同學們答題參與更積極、更主動。這印證了媒介情景論關于媒介變化導致行為變化的預測。無論是連麥答題,還是評論區回復,同學們參與問答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正如訪談中的一位同學所說“同學們可能希望通過文字或聲音來體現自己的存在感吧”。
(二)調查顯示學生普遍感受到教師授課行為變化明顯,且回歸分析顯示“教師行為變化”是學生答題行為變化最為有效的預測變量。教師以“問題為導向”、“強調課堂答題重要性”、”鼓勵答題“等正向引導行為直接引發學生積極的課堂問答參與。由于授課媒介變化,線上授課時,因無法有效感知和監控學生學習行為,教師最關注的是“學生們有沒有坐在電腦桌前認真聽課”。為確保學習行為最大限度發生,教師大多放棄以往講授式教學,轉而“以問題為導向”進行授課。這一變化既可以更明確教學目的,也可以增加與學生互動機會,使教師能夠更好地監控和實實在在地感知學生學習行為。同時,目前外語教學中,教師依舊是教學活動“組織者”,學科知識“權威”,學科成績“評定者”。按照計劃行為理論的解釋,學生行為必然會受到特定社會規范和環境中重要他人的影響[16]。教師強調答題重要性的話語,以及鼓勵、引導學生答題的具體行為,必然會引起學生的重視,對其行為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引發更多主動答題行為產生。
(三)調查顯示,學生普遍認同線上課堂答題壓力較小,而答題壓力感降低是另一個顯著影響學生答題參與的因素。線上課程的答題壓力小于線下課程,有多方面原因。第一,學生在非教室環境中學習,這樣非正式的學習環境能帶給學生較為放松的心情。第二,本次調查中,幾乎所有老師線上授課均采用音頻會議或錄播+QQ或微信群討論的方式。由于互不可見,社會臨場感弱,答題學生不太容易受到同伴負面的非言語評價的影響[17]。同時,參與課堂問答的渠道,不限于連麥發言,更多同學通過評論區評論方式參與。評論區多人同時參與的方式弱化了個體發言的壓力。更為重要的是,評論區發言多是同學們之間的互動。大家水平相當,不用擔心來自老師的評價,參與答題討論的壓力小。此外,由于線上課堂往往依托某一學習平臺開展,往往有硬性的預習要求,學生通過預習也為答題積累了知識儲備;加之,在老師看不見的情況下,學生在屏幕后,可以自由地通過網絡檢索、查閱預習資料等渠道搜索、整理答案,也使得答題風險減小。總體而言,本研究發現與Blau的發現一致。Blau研究發現,雖然學生在面對面學習環境中,情感體驗更佳;但通過音頻會議學習,學習者會更加主動地參與討論,更愿意承擔出錯風險[18]。這一行為變化可用Suler提出的“網絡去抑制效應”解釋[19]。在Suler所提及的6個網絡去抑制因素中,互不可見(invisibility)和權威弱化(minimization of authority)是推動學生線上課程參與積極性的最重要的兩個因素。線上教學過程中,由于大部分教師采用音頻直播或錄播方式授課,彼此不可見,所以學生在參與課堂討論時,表達的意愿不會受到他人(包括教師和同伴)負面的非言語性反饋的抑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學生主動表達的意愿。其次,網絡交流所具有的多重交互性特點使相對平等的交流成為可能。本學期線上教學中,教師提出問題后,多個學生可以多種形式同時回答,并且學生之間也會產生多重互動,問答過程和結果不再完全由教師控制和主宰,這種相對平等的交流環境也提升學生的表達愿望。
此外,調查結果雖然顯示學生認同線上課堂答題方式有明顯變化,但答題方式變化因素卻不是學生答題行為的直接影響因素,答題方式變化通過影響學生的答題壓力感和答題準備行為間接影響學生答題行為。
五、應用與啟示
通過對學生線上課堂答題參與影響因素的調查研究,我們發現:由于授課媒介變化,線上課堂教師授課行為發生變化、學生答題壓力感變化以及答題準備行為同樣有所變化。這些變化能直接地、有效地引發學生的主動答題行為,而答題方式變化則主要通過影響學生答題壓力感而間接影響學生答題行為。具體而言,首先,在“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環境中,教師行為對學生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教師關注的焦點如是否主動參與會成為學生行為的風向標,加之,教師一系列鼓勵答題的行為,都會引發學生主動參與課堂問答的行為。其次,線上課答題環境變化明顯,尤其是網絡媒介特有的視覺匿名性和多重交互性大大削弱了學生答題時的壓力感,提高了學生表達與交流的愿望,使更多學生愿意主動參與到課堂問答互動中來。此外,教學平臺硬性的預習要求也促使一部分學生進行課前預習,較為充分的課前準備也使得同學們更有信心,更愿意主動答題。
本研究為提高學生線上課堂參與帶來了以下啟示。首先,鑒于教師行為對學生課堂參與的重要影響,教師應強化課堂參與要求,明確參與的評價標準,提供充分的學習材料支持,多提可參與性強的問題,并給與積極有效的評價以推動學生課堂參與。其次,充分利用網絡媒介視覺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的特點,組織形式多樣線上教學和討論活動,鼓勵學生在網絡學習平臺上更加平等、充分地參與討論。再次,學校和教師應當權衡各學習交流平臺利弊,選擇最為適合本校學生學習和交流的平臺,使學生能夠便利地參與課堂;同時也能更準確追蹤、記錄和分析參與情況。
本次研究主要針對安徽合肥部分高校一、二年級的線上教學實踐中極為有限的對象展開調查,調查對象的局限性使文章結論難免有些偏頗,在今后的研究中應擴大研究對象范圍,使研究結論能更好地服務于教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