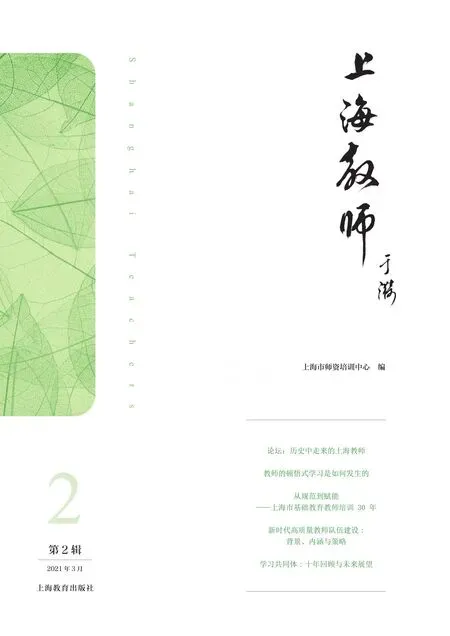從歷史中走來的上海教師
吳國平
上海師范大學副教授
“歷史中走來的上海教師”這個主題,乍一看是當前四史教育的拓展,也能夠很快明白它是圍繞我們集刊的名稱和定位的研討。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上海教師的故事,這確實是我們今天應該承擔的工作。從這樣的意義出發,《上海教師》未來少不得要說好一個又一個上海教師的故事,但是更重要的是說好故事的資本——上海教師究竟有怎樣的品質,這些品質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它又將如何在新時代書寫上海教育的輝煌。
從歷史中走來的上海教師,它有兩條線索,一個歸宿。一條線索是歷史的。地理意義上的上海源遠流長,但是教師身份的出現卻是晚到1840年以后才出現的事情。沒有鴉片戰爭的挨打,恐怕也不會很快出現這個“教師”。那么,被人家打進來的這個教師是個什么“東西”呢?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另一條線索是稱謂的。民國初,它叫先生;民國后期,它叫教員;1949年以后,它叫教師,進而又叫人民教師。而它的歸宿只有一個,就是反映上海教師的品質。那么,上海教師具有怎樣的品質呢?我想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命題的價值所在。
一、 師之由來與演變
從歷史中走來的上海教師,是怎樣的呢?歷史中不光上海沒有“教師”,中國也沒有“教師”,古語里邊不僅沒有“教師”一詞,也沒有專門從事“教”的“師”。古時只有師,沒有教師。師,更確切地說是政治家。韓愈的“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與其說是對授業者的要求,不如說是對政治家的要求。當然這里的政治家不是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也不是現代文明意義上的,而是維系宗法社會倫理的各級君卿士儒,所以古時候有道統、有政統、有學統,但就是沒有教統。“教”,在中國古代沒有獨立的地位。古人常言“半部《論語》治天下”,但在《論語》中幾乎沒有論及“教”,而是反復不斷地提及“學”,所以后人討論“教”多從荀子說起。說歷史上我們沒有教師,但是能不能說這個地方就沒有教育呢——恐怕不行。那么我們是怎么體現“教”的呢?古人的“教”隱在政治中,常常以教化的形式出現。道統代表家國天下的儒法理想;政統接近于制度安排;學統反映著對儒法社會及其制度安排的體認。“三統”合起來處理宗法社會的家國事務,處理好了,天下一統,國泰民安,就是好的政治,也是對理想的家國天下思想的示范;反之,處理得不成功,則天下大亂,內憂外患,政治失敗,理想的家國天下價值示范宣告失敗,改朝換代總是以“替天行道”為借口就是這個原因。所以在中國古代表現出來的是“政教合一”,“教”,在政治中——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中,所慮的興亡不在于一家一族的利益,而是理想社會的價值;所擔之責也不是個體的犧牲,而是匹夫身上所內化的天下道義。就此,政教合一把社會的價值和個人的行為糅合在政治——教化之中,將對理想社會思想價值的弘揚同個體的修為與責任建立起了聯系。所以荀子提出“以善先人者謂之教”(《荀子·修身》),“教”就意味著個人的社會表現比別人更優秀、更值得示范。《中庸》說“修道之謂教”,認為“教”就是修道,強調的同樣是“教”的社會表現。可見,中國古代不僅沒有今天專門從事“授業”活動的“教師”,連教育活動也多是通過政治性的社會活動得以體現。
二、 師名稱謂的流變
從師名稱謂的演變來看,近代意義上教師的出現是西學東漸以后的事情。民國初期,最早的稱謂是“先生”。為什么叫先生,先生覺后生,先學覺后學,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教育的真諦在于躬行和覺悟。先生后生之別只在于時間的前后和程度的差異,都在行與悟的進行過程中。所以古人一度嘲諷那些自詡為師的人,以好為人師為負面警策。可見,“先生”通過示范“善”彰顯“師”的本義,至今都是人們對德高博學者的敬稱。沿襲在民間還有“教書先生”一稱。“書”在歷史中有狹義、廣義之分,最早專指《尚書》;此后也指稱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那時的書多是刻制在竹簡上的;再到后來隨著印刷技術的出現,把經過裝訂印制在紙帛上的文字稱作書,及至今日各類形式的書已是目難盡收。試想,狹義、廣義之書所承載的知識和學問之深之多何人能傳?只能靠個人治學,靠個人修行,“教書”表明謀生形式,“先生”揭示治學修行的進階——以“善業”“善德”“善覺”啟“后生”的“先人”而已,這就是荀子“以善先人者謂之教”的道理。由此,也就容易理解世人所謂“后生可畏”是對“先生先覺”的必要補充。
及至民國中后期,人們對授業人員稱“教員”,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出現了專門開展教學活動的新式學校,有了專門從事授業的人員。教員的任務就是講得清楚,教得明白,講解是教員的外在能力,知識修養是教員的內在品質,講授清晰就是教員的本事和能耐。“先生”和“教員”這兩種稱謂在我國臺灣和同為東亞文化圈的日本沿用至今,且經常交叉使用。
從教的人可以稱師,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事。它體現了人民政權對教育工作意義的高度認識,把從教人員的身份提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從事教職可以為“師”——傳統社會身份地位最高的群體。這樣的師,自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它理所應當就是人民教師。繼之,又有人民教育家的稱謂,用以激勵從教者不斷進取。冷靜地看,師也好,人民教師也好,這些都是對從教者的應然稱謂,卻未必是普遍的實然狀態。
可見,從歷史中走來的教師,就是從帝王之師,再到先生覺后生的“先生”,從只重知識傳遞的教員而到引導民眾的人民教師,至今又誕生了人民教育家,它為上海教師的發展書寫了一條清晰的歷史畫卷。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沒有“師”這個概念,只有政治家、藝術家之流,卻不見“授業家”之說;相應地,“教師”也不是對“teacher”的翻譯。西方教育學里邊也沒有傳道、授業、解惑的從教要求,好的從教者是激勵學生自己學習。社會學家沃德就將教師分為四類:平庸的老師傳授知識;水平一般的老師解釋知識;好的老師演示知識;偉大的老師激勵學生去學習知識。無獨有偶,在近代中國私塾里的先生,也很少“開講”,“讀書”多是“生徒”自己的事。就此來說,實際上教員用傳道、授業、解惑的政治家標準來要求自己,那確實不是別人的高尚,而是我們自己的熱情。
三、 可以觸摸的上海教師
近年來“海派教師”常常成為業界議論的話題,那么上海教師究竟有怎樣的品質呢?自開埠出現新式學堂以來,上海教師就以自己的眼界寬闊、勇于引領時尚和潮流、追求一流等品質受到世人矚目。早年,格物致知的新知識多是由上海教師率先引入課堂。有人統計1949年以來的兩院院士,多出于江南,其中上海又獨占鰲頭,原因有許多,而滬上名師薈萃是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兩院院士王選早年就讀于南洋模范中學,后來回母校憶及當年求學歲月,名師薈萃,歷歷在目,其中雖有用滬語授課的教師,卻素養高超,精彩紛呈。他形象地以“大餛飩”來贊譽那些學養厚重、眼界開闊、一流上品的優秀教師,并以復雜的情感贊嘆趙憲初為“南模最后的大餛飩”。有些年歲的老師應該記得,后來成為南模校長、滬上著名教育家的趙憲初是南模數學教師,他教代數是出了名的。除南模以外,上海還有澄衷中學、格致中學、大同中學、市三女中、延安中學、育才中學、向明中學、浦東中學、上海中學、徐匯中學、萬竹小學,等等,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有一批大學附中崛起。伴隨這些學校的有馬相伯、黃炎培、豐子愷、陶行知、陳鶴琴、段力佩、葉克平、薛正、袁瑢等一大批聲名顯赫的教師,他們都當得上王選口中的“大餛飩”。
顯然,關注上海教師不是為了講好故事,而是為了讓上海教師出現更多的“大餛飩”。當年王選說趙憲初是“南模最后的大餛飩”,言語之外雖透著些許無奈,好在這之后上海又出了于漪,似乎表明上海教師隊伍中還有“大餛飩”。近年來,隨著各式“故事體”敘述興盛,上海教師日益名揚四海,在自豪和贊嘆之余也難免生出庸人自擾的疑問:于漪會是上海教師最后的“大餛飩”嗎?且不說今天還有沒有與上述一大批人物等量齊觀的上海教師,就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活躍在滬上杏壇的那些教師:教數學的曾容、教物理的袁哲誠、教英語的何亞男、寫《知困錄》的沈蘅仲、勝似雜家的商友敬、對教學法毫不含糊的張平南、強調導讀的錢夢龍、教小學數學的封禮珍……他們基本上沒有受到后來熱鬧非凡的課程改革、評價改革的熏陶,也幾乎沒有從各地“覓”來的出身,還沒有習得說故事的本領,純屬地地道道的上海教師品質。顧眼四望,今朝這樣的教師似乎蹤影難覓。誠愿上述有關“大餛飩”的一堆議論只是作為庸人的余慮,而不是滬上一眾名師之尷尬。“人民滿意的教育”不是寫在文件上、掛在嘴巴上的金句銀語,而是課堂里演繹著的一幕幕生命的精彩,上海教育需要更多“大餛飩”式的教師。
由此可見,上海教師不是一個符號,而是一種存在狀態,是特定的品質。
四、 上海教師的品質
上海教師的品質是歷史地形成的,也應該做出歷史性的回答。其概括起來有四個特征:
第一是情,即家國情懷。上海教師的形成就是積貧積弱的民族危機的直接結果,無此,上海的開埠還無從談起,沿襲近1300年的科舉也不會瞬間被廢,構成上海教師所必需的地域空間和身份角色便是空中樓閣。可以說上海教師與生俱備的是從苦難中被拷打出來的品質,這些品質集中到一點就是家國情懷,那是中國知識分子從歷史和時代身上汲取的優秀品質:抵御外敵,不畏強暴,師夷制夷,匹夫有責。
第二是新,即與時俱進。正因為近代上海的崛起是古老文明因應外部沖擊的結果,上海教師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求新應變、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特征。無論是早期開設的新學、引入的新知,還是仿學日本學制,繼而引入美國學制,再到以俄為師學習蘇聯的近代學制改革,是如此;考察歷史可以清晰地發現,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行于歐美的各式教育思潮都在上海教師這里留下過探索的痕跡,也是如此;恢復高考之后,上海又是主動求變,率先引入第二課堂,繼而進行高考自主命題改革,再到一期課改、二期課改、綠色指標評價改革等,都是主動求新求變,以回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同樣是如此。可以說,與時俱進已經成為上海教師的特有基因。
第三是寬,即視野開闊。和與時俱進結伴的品質是,上海教師的視野開闊,從不拘泥于一時一地的局部經驗和成果,從全球視野和社會經濟、科學技術最新發展成果里邊學習、借鑒,汲取不斷前行、不斷發展的動力。從綜合實踐活動到芬蘭經驗,從PISA測試到中英教師交流,從教育信息技術的運用到深度學習理論的探索,等等,莫不是如此。
第四是優,即追求卓越。上海教師從不停步于既有經驗,從不躺在既有成果的功勞簿上。在上海教師身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他們始終在追求更優秀的道路上。在這里,不僅有中國本土最優秀的教育經驗,也有國際化、世界級的辦學成果,這些經驗和成果無不來源于上海教師追求卓越的品質。無論是上海本地學校的辦學聲譽,還是國際學校的教育質量,背后都有上海教師追求卓越的因素。
上述四大特征,歷史地反映了上海教師的特有品質。今天,我們需要更全面地展現這些特征新時代的意義。這不僅是因為上海教育自身面臨著新的發展局面,從關注課程到回歸教師是教育發展的內在要求,唯有內在于教師的課程才是從應然到實然的正道;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站到了民族發展新的歷史時期,復興是偉大的夢想,展現在于人的教養水平。體現國家強盛的教養是什么呢?這是每一位上海教師都應該認真思考并做出確鑿答案的命題。
五、 對《上海教師》的期待
作為教育的從業人員,今天為上海增加了一份以教師為主題的讀物高興,為上海教育領導的遠見卓識所欽佩,為在座和不在座的各位行家對讀物的支持贊嘆。
新生的刊物猶如新生的孩子,總會寄托人們的無限希望。《上海教師》同樣如此,它不只擁有了自己的稱謂,更有了成就自己、成就上海教師的無限可能。
作為一個符號,上海教師日益受到關注。面對上海二十萬教師的真實生存,我們希望,刊物不必學術,但求畫像,一展師者風貌;不必贊美,但求訴說,一敘講臺甘苦;不必謳歌,但求療慰,一撫身心疲乏。
教育所內含的價值,無法自己表現,總要通過教師的言傳身教來傳遞。就此而論,課程、評價都無法替代教師的創造。藝術史家貢布里希曾經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借用到教育可以說:沒有教育,只有教師。在動輒課程、動輒評價之后,今天,我們需要迎接一個教師的年代。沒有教師理解的課程是理想,沒有教師展現的評價是說教,我們期待《上海教師》能夠引導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
由此需要研究和關注上海教師的品質。上海教師是歷史地形成的,它具有開拓創新、視野開闊、銳意進取、追求卓越等品質,面對轉瞬即逝的時代變遷,它需要不斷與時俱進,開創未來。
在常人看來,刊物依賴的是名人名家名篇;其實,一份刊物的價值和資源是讓作者找到讀者,讓讀者認識作者,讓作者與讀者不斷產生共鳴,確認進步的價值,進而不斷壯大共同的力量。我們期待,在《上海教師》的號召下,能夠集聚上海更多的教師,成就一個時代大寫的上海教師。很高興在《上海教師》結識各位賢達,讓我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