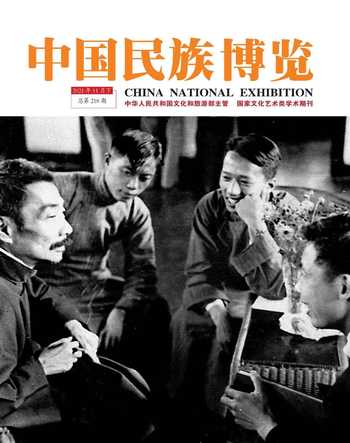別樣的孔子——淺談話劇《孔子》的人物創(chuàng)作
【摘要】在戲劇表演創(chuàng)作中,塑造人物形象是演員的使命,因此,在排演的過程中,演員如何接近角色,創(chuàng)造出有價值的人物形象,永遠是演員所追求的目標。本文旨在通過《孔子》的排演實踐,將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孔子這一主要角色的塑造與探索進行總結,著重分析這個歷史人物的舞臺形象創(chuàng)造,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積累的創(chuàng)作體驗,以期給予同行們一些表演創(chuàng)作、人物形象創(chuàng)造方面的有益啟示。
【關鍵詞】話劇;舞臺劇;戲劇表演;角色塑造;孔子
【中圖分類號】J8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22-190-03
【本文著錄格式】 別樣的孔子——淺談話劇《孔子》的人物創(chuàng)作[J].中國民族博覽,2021,11(22):190-192.
山東省話劇院話劇《孔子》的創(chuàng)作和演出已經(jīng)告一段落。筆者作為孔子的扮演者,在排演的過程中受益良多。因為這是一次艱辛而有意義的實踐,在創(chuàng)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從人物分析到舞臺呈現(xiàn)的整個過程,包括經(jīng)驗上與技術上的專業(yè)問題都將成為一個從普通演員過渡到成熟演員所要邁過的方方面面的“檻”。
在表演行業(yè)中,人們常言“不瘋魔不成活”,演出雖已結束,但筆者卻難逃出這個早已刻于內(nèi)心的角色。因為在乎,所以心甘情愿的為之付出,筆者留戀著那個和自己朝夕相處,甚至與自己融為一體的孔圣人。如何塑造春秋戰(zhàn)國時代那個“亂世中的木鐸”是筆者在此次創(chuàng)作中需要思考的核心,因此,本文旨在通過《孔子》的排演實踐,將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孔子這一主要角色的塑造與探索進行總結,著重分析這個歷史人物的舞臺形象創(chuàng)造,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積累的創(chuàng)作體驗,分享真實的創(chuàng)作體會,以期給予同行們一些表演創(chuàng)作、人物形象創(chuàng)造方面的有益啟示。
一、如何進行人物分析
如何接近角色是每個演員最初拿到劇本時的困惑,尤其是一個與自己相隔著遙遠時代的歷史人物,一個與自己生活經(jīng)歷完全不一樣的角色。關于孔子的資料如此浩瀚無邊,到底哪些是此次創(chuàng)作所需要的重點,哪些是呈現(xiàn)在舞臺上,表現(xiàn)所不可忽略的。因而,筆者創(chuàng)作初期開始了初讀劇本,從初讀后的印象中一點點找尋人物形象的輪廓,這是演員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也是將來塑造人物形象的起點與契機。而后,演員需要再讀,在再讀的過程中,筆者著重分析劇中的主要事件、人物的性格、人物關系、人物命運等關于人物形象系統(tǒng)的分析。在這一階段,演員的任務是繁重的,由于要扮演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是一個大眾所熟知的圣人,于是筆者采用最踏實的方式,閱讀有關孔子的典籍,從字里行間研究他的個性、為人處事和孔子那些曲折無常的人生經(jīng)歷,以及那些遭遇所帶來的時而波瀾壯闊時而細致入微的內(nèi)心、情感變化。
得益于本人參加過上海戲劇學院2017年舉辦的國際導演大師班,學習了一些戲劇創(chuàng)作方法,在對《孔子》進行細致的劇本分析后,筆者開始尋找創(chuàng)造人物“抓手”。人物形象創(chuàng)造的過程就是要一遍遍熟讀劇本,再從相關的資料里尋找與舞臺人物形象相關的重要部分,找到引發(fā)事件的緣由,是性格亦或是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在這些事件發(fā)生的過程中,去梳理由事件所引發(fā)的人物的內(nèi)心波瀾。初讀與熟讀劇本是創(chuàng)造人物形象的必經(jīng)之路,是一步步走向人物,保證其思想邏輯連貫性的抓手,也是在將來體現(xiàn)角色時明確其上場任務,以及通過行動去完成人物在整部作品中的最高任務的創(chuàng)作基石。
然而,這只是一個創(chuàng)作的步驟,還需在此基礎上進行角色的體現(xiàn)和打磨。孔子一直是筆者夢寐以求想要塑造的角色,其排演過程壓力和喜悅共存。“誰排孔子,誰就是孔子;誰演孔子,誰就是孔子!”就是這樣一句簡簡單單、沒有修飾過的、樸實無華卻宅心仁厚到極致的話,成為筆者在創(chuàng)作中期遇到瓶頸,從精神到肉體都很疲勞,甚至開始無緣無故胡思亂想,缺乏創(chuàng)作靈感的時候,鼓勵著自己走下來的動力。
二、對孔子出身的誤讀
《史記》記載:紇(he)與顏氏女禱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很多人包括學者都誤將這句話解讀為孔子是個私生子,而實際上魯國的首都在今天山東曲阜附近,其周邊有一座名為尼丘的山,據(jù)說孔子父母是于這座山里野合生了孔子,因而,孔子的名字叫丘,字仲尼,仲即老二的意思。名字里含尼丘二字,是為了紀念這座山。而對孔子出身的描述與現(xiàn)代人的理解常常很難劃等號,用現(xiàn)代人的片面理解,“野合”是一種低于正當禮儀的婚配,而大多數(shù)現(xiàn)代人也傾向于理解為未婚男女之間,或不合法的一種茍合。而“野合”之于古代是合法性行為,而非現(xiàn)代人所理解的婚外非法性行為。從這個角度來說,它對此次排演塑造人物形象有著一定影響,因為它涉及到理解這個人物的完整性,也是接近這個角色時,首先要矯正的有失偏頗且固有的思維定式。
三、“帥”是他的靈魂閃光點
千秋文圣萬世師表,孔子不是杜撰設計出來的人物,歷史上對孔圣人有承、解、著、傳的賢人雅士多如牛毛,其言說之精湛飽滿,如昆侖之美玉,木中之奇楠。當代,打開電腦輕撩度娘,鼠標且點,你會發(fā)現(xiàn)電腦里面的孔夫子,豐富到可以隨時復活。但是從古至今又有幾人能把孔夫子的內(nèi)心讀懂呢。他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但他也終歸曾是活生生的凡人。是凡人就會有喜怒哀樂,就會有悲歡離合。在排練中,筆者沒有什么耍機巧的方法,只是選擇最原始的辦法,讓夫子活在自己身上,筆者把自己的名字給他,給夫子一個“帥”字作為他的靈魂閃光點。一位卓越非凡的思想家,一個溫文爾雅的智者,這是他作為文學形象在筆者心里的印象。作為舞臺形象,筆者想要詮釋一個有血有肉、全新的孔圣人,而非離我們千萬里之遙相框中的遠古圣人。這個有血有肉首先在于他也是一個凡人,他的思想光輝讓人忽略了他還是一位兼具才情的孔圣人。被稱為“周禮樂之圣地”的魯國,有這種別于其他時代的特點,琴和劍是周禮之外,智者們信手拈來的智慧體現(xiàn),同樣也是孔子這一舞臺形象很多面光彩中的一方面。因此,為了飾演好孔子這個角色,將琴和劍視為塑造這一角色最基本的任務并加以磨練,來增添孔子這個人物人格魅力的一抹底色。他的“帥”體現(xiàn)在:孔子是以一種大謀大勇的毅然前行,折射出他堅定的大同和禮治信念,和他“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的真正志向。從這方面說,這個“帥”包含了孔子的智和勇。勇,是沖破難關無畏的果敢;智,則是發(fā)現(xiàn)心中的理念在當下不可為的時候,做出的讓步和轉變的大智慧。
筆者所扮演的孔子,“帥”既是他的魂也是他的外在。然而遺憾的是,今天的人們看到的大多是孔子晚年的畫像,人們幾乎忘了孔子也有年輕的時候。此次創(chuàng)作正好彌補了觀眾對孔子年輕時代的空白,這讓筆者可以有無限發(fā)揮的可能。都知道孔子的思想,可年輕的氣宇不凡對這個人物的完整性來說,同等重要。
有別于以往的幾版孔子,《孔子》第一場就奠定了這個全新的人物形象,過往人們所熟悉的擺幾個造型、貫用的腔調、流于表面情緒化的蒼白表演是滿足不了這個更為多面和立體的舞臺形象。正如劇中第一場夫子與子路論劍比射那樣,他生于凡人而又過于常人的“帥”,這種“帥”不是耍酷,它的張力將恰到好處地襯托他年老時,虛負凌云萬丈才,一身襟袍未曾開的人生境遇。用現(xiàn)代人的話來說,即誰會想透過你邋遢的外表去了解你的內(nèi)心。外在的帥與內(nèi)在的惆悵對比,才會使多義的形象更加豐滿而具有人格魅力。誠然,相較于一個站著思考,不會動的劇本朗頌者來說,唯有將智和謀統(tǒng)統(tǒng)讓位于舞臺上可視的“帥”,才有可能是今天的觀眾所期待的。這就如同我們見過了一個非凡的芭蕾舞演員,因地震失去雙腿從此一輩子與舞臺無緣一樣,只有強烈的對照才更能激起觀眾的由衷地感嘆。這種鮮活是筆者塑造這個舞臺形象所始終追求的,也只有當他的“帥”內(nèi)外一致時,舞臺上呈現(xiàn)的孔子才最符合觀眾心目中那個天人合一的孔圣人。
四、如何理解孔圣人的“情”
人物的情感是筆者接近這個角色的切入點,孔子的情分兩種,一是情操,一是情感。情操表現(xiàn)在他對君子的執(zhí)著。在《論語》中,處處都可以看到他對君子這一概念的定義。另一方面是他對魯國的執(zhí)著,這種情感可以看作是鄉(xiāng)土情結,即是他對故土的一種特殊情感。情感方面,首先,他對其弟子。孔子一生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對待自己的弟子,可以用一個誠字來表達,弟子們面前的他沒有掩飾,就算是缺點和瑕疵也都一樣沒有遮遮掩掩。夫子最得意的門生應算是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回不改其樂,在夫子眼中,顏回是一個能傳承他的思想和主張的人。他對顏回是認可的。甚至,對顏回這個弟子,夫子自己對他都會有欣賞之心。對其他的弟子,夫子也都把他們當作是另一種意義的家人,比如子路、子貢等。
五、孔子的舞臺形象設想
同為圣人,在筆者主演的《兵道》中孫武是兵圣,相較于《兵道》里千軍萬馬鏖戰(zhàn)的激昂,《孔子》更需要沉穩(wěn),從一個凡人的角度去詮釋孔圣人的“神”,才可能拉近與當代觀眾的距離。由此,如何從一個文文弱弱的讀書人形象里,體現(xiàn)如海濤般洶涌澎湃的千軍萬馬,統(tǒng)領著一個時代的人物,也是筆者貫穿此次排練創(chuàng)作中的重點。
劇中大自然的變化亦是孔子內(nèi)心的幻化,從第一場《君子》到《為政》殺少正卯,再到《去國》的“細雨蒙蒙”,以至《困境》一場的“大雪茫茫”,無不揭示著孔子內(nèi)心的雨雪風暴。在為政殺少正卯一場戲中,筆者借助戲曲中表現(xiàn)人物在情緒激蕩時所用的圓場、投袖、拖腔、撩袍等技巧,化用在此時釋放夫子內(nèi)心壓抑、積郁已久的表現(xiàn)上。臺詞也由慢至快,再由快到慢,以盡可能最為生動的手段,將人物最隱蔽的內(nèi)心世界和最復雜的心理變化視覺形象化,將人物的內(nèi)心風暴推向頂點,展現(xiàn)一位有血有肉,更重要的是有溫度的孔子。
六、創(chuàng)造人物獨有的詩意
人物的魅力有時候來自于他的人格魅力,有時候在于他的一個小動作、一個小表情,甚至是一句有韻味的臺詞表達。有觀眾反饋說臺上的演員都在喊,這無疑是片面的。從整體呈現(xiàn)而言,這部戲需要安排200人的交響樂團現(xiàn)場演奏,以凸顯整部作品的宏大敘述,因而演員勢必需要更強烈的激情、更高分貝的音量去支撐人物的慷慨激昂、抒發(fā)復雜的內(nèi)心情感,甚至,有時候演員要用自己的半寸聲帶和臺詞專業(yè)技能,于任何輔助手段面前都要始終讓觀眾聽清角色的臺詞,保證臺詞的清晰表達而不被舞臺上的其他因素所干擾。此時的基本功尤為重要,喊是一種技術,也是塑造人物形象所需的基本功。但是毫無情感的喊,就會使表演變得空洞,破了人物獨有的詩意。孔子這個角色的戲核,恰恰就藏在“韻”中,藏在“味”中,張飛、李逵般的大嗓門只會毀了孔子人物形象獨有的特殊氣質,也完全背離了他郁郁不得志的憂愁;因為孔子的一生像一首詩,詩中有酒的濃烈也有水的甘甜,既有心懷天下的情操,也有悲天憫人的情懷。
正如宋國開國宰相趙普曾說過一句話:半部《論語》治天下,孔子的思想學說,是奠定中華文化的核心,是使后人受益匪淺精神之髓,故而,筆者將他于耄耋之年的那段獨白視為其受盡顛沛之苦后,一種既有不甘與無奈,也有順應自然知天命的泰然,來抒發(fā)孔子這個人物應有的情懷,凸顯其偉大的生命個體的不同反響之處。
七、將戲曲功底熔鑄于角色塑造中
筆者從小學習京劇,對話劇演員來說,戲曲基本功使筆者有別于其他同臺話劇演員,也是筆者優(yōu)于其他話劇演員的一項存在于自己身上的技能,更是本人塑造孔子這個角色形象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古代人的穿衣方式、生活方式和現(xiàn)代人完全不同,所以在舞臺上的寬袍大袖對別人來說可能是一種障礙,而對于、本人,一個習慣了身韻臺步,習慣了漢服長袍的演員來說,這恰恰成為表現(xiàn)這個人物內(nèi)心活動的一種手段。然而,許多演員甚至是專業(yè)話劇演員都不明白壓腿的意義,比如在排練進行中,本人下意識把腿放于高處壓腿的時候,就有一個比我年紀大一點的話劇演員忽然來問我,一個話劇演員你為什么要壓腿呢? 從他不屑的表情中可想而知,這并非只是一個個別現(xiàn)象,尤其是在當下,強調話劇向傳統(tǒng)戲曲學習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也是專業(yè)院校在探索戲劇教育以及創(chuàng)建“中國演劇學派”的前進方向。試想,一個扮演古圣先賢的演員,沒有行走坐臥的形體姿態(tài)意識,不從自身的肢體上去鍛煉出與人物相符的氣質,又如何能在厚重的古代服裝下,展現(xiàn)出人物的舉手投足、音容笑貌,如何在人物的神情意韻中體現(xiàn)它獨有的風范? 就如同劇中的孔夫子,需要坐在硬板輪車上。坐在硬板輪車上的那一刻,演員不僅要保持古人的氣質,同時還要有足夠的基本功在車上保持著完美的平衡,那種控制力甚至要達到在人物情緒狀態(tài)不變,并且保持人物造型平穩(wěn)的情況下隨著車輪駛向未知的地方。只有在熟練的身體技能和強大的基本功的加持下,用人物的語言、情感、肢體去詮釋:“看雪地里那條車轍,歪歪扭扭伸向何方,這人間正道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回家。”
于此期間,本人還學著去演奏孔夫子當年所演奏的古琴曲。在反復演奏的過程中,將自己置身于劇中的意境,去感受《文王操》里的莊嚴和肅穆,甚至在腦海中想象出周文王的人物形象,高高的個子,斯文而莊重。順著想象中的情景孕育出的意識,去體驗周文王,去體驗孔夫子所描繪的周文王,此時,筆者仿佛也感受到了孔夫子在演奏此曲時的內(nèi)心波瀾,筆者認為自己已經(jīng)進入這個角色了。
塑造人物是一個將自己身體與靈魂注入角色,使其活在舞臺上的過程。筆者為了讓自己更加像一個古代人,甚至開始學習導引術,開始學習中國的道家文化。開始站樁冥想,讓自己進入那種虛靜無為的狀態(tài),試著去理解道的含義,盡管短時間內(nèi)無法參悟通透,但是偶然自覺,當一個人真正讓自己放空的時候,他的身體是會有所改變,內(nèi)心的變化就會帶來外在的變化,只有當放空之后才能讓自己自然而然的與角色產(chǎn)生鏈接。
孔夫子是古人,筆者是現(xiàn)代人,但是從某種角度來講,無論生活在哪個時代,當心向往之的時候,是可以同頻共振的。雖然這樣說沒有任何的依據(jù),盡管筆者也不是搞什么量子力學的,角色的誕生誰說不是從分析和探索與人物的同頻共振而產(chǎn)生的呢。
八、結語
孔子是一只木鐸,是一只一直在警示人要良善的木鐸,筆者就是那只“木鐸”,在整個排演過程中,如何賦予其靈魂是筆者著重思考的,這一思考,貫穿著整個人物形象創(chuàng)造的實踐。同時,作為演員,也同樣注重如何將其豐富且復雜的內(nèi)心展現(xiàn)在舞臺上,使其成為一個鮮活的人物形象活在觀眾的心中。
這是一次美妙的創(chuàng)作之旅,只有在準備充分的情況下,才能在更高層次上去接近他,復活他。他高尚的品格和偉岸的人格力量此時已無需過多的表演技巧,應該說,在體驗他的過程中,他早已活在筆者身上,正如觀眾對筆者所扮演的孔子這個形象回饋的那樣,這個角色是如此不同,演員對情感的細膩把控和通過考究的肢體語匯,賦予其靈魂豐滿、充盈,已然使孔子這個人物形象從文字中躍于舞臺上,就像出場時,他緩緩轉身,然后開始娓娓道來……真切、自然、像一位令人敬仰的智者,又似鄰家和藹可親的常人。
簡言之,在塑造這個有血有肉的“木鐸”的過程中,筆者將自己最大的收獲是像孔圣人一樣的做人做事、像他一樣對生活充滿信心。正如戲劇導演雷國華所說:“戲劇之所以有力量成為世界永恒的舞臺藝術,正是因為劇作者們描述的社會及人生經(jīng)歷無論是殘酷還是美好都深藏著寫作者對人類社會所經(jīng)歷的種種災難和不幸遭遇中發(fā)現(xiàn)人性本善和那些不為人知的隱秘的悲喜交織的情感故事。”
注釋:
①《孔子》山東省話劇院排演,導演:張繼剛。
作者簡介:李帥(1975-),男,山東濟南,創(chuàng)作中心主任,話劇演員,研究方向為戲劇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