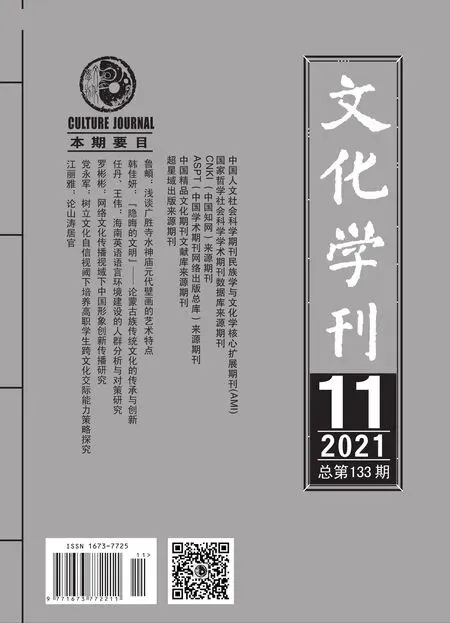《論語》中的民俗思想探析
王才俊
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社會變動加劇,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觀念都發(fā)生了很大改變。一部分服務(wù)于周王室的大夫、士紛紛流入民間,他們將包括周禮等上層文化也帶到了民間,進(jìn)而引來一場“禮俗互動”。周王室的衰微,諸侯僭禮而行,導(dǎo)致周禮分崩離析,社會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失范狀態(tài)。當(dāng)此之時(shí),孔子提出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復(fù)興周禮主張。這一主張并非一味復(fù)古,而是結(jié)合民間的“俗”,結(jié)合上層的詩、樂等意識形態(tài)來達(dá)到社會治理的目的。針對這一救世方案,孔子做了諸多努力。首先,他為政時(shí)實(shí)行仁政,使魯國大治。“導(dǎo)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政令、刑罰與道德、禮教之間,孔子更重視后者,這實(shí)際上是孔子重視民俗以俗化民的社會治理功能。其次,開辦私學(xué),一方面向?yàn)檎咝麄魅收⒅芏Y的思想并輸送“合格”人才,另一方面發(fā)揮文化以文化人的作用,這其中包含著移風(fēng)易俗的主張。第三,晚年編訂《詩》《書》《禮》《易》《樂》,為后人保存?zhèn)魇牢墨I(xiàn),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民俗資料。
一、人學(xué)化的文藝民俗觀
文化有雅俗之分,文學(xué)亦有雅俗之別,上層的士大夫文人之作謂之陽春白雪,是為千百年來文學(xué)的正統(tǒng)。與作家文學(xué)相比,民間文學(xué)則是下里巴人,登不上大雅之堂,一直以來為士大夫文人所鄙視,宋詞、元雜劇、通俗小說出現(xiàn)之初,無不如此。然而,幾千年的文學(xué)史,不能沒有神話、傳說、歌謠等民間文學(xué)。在遠(yuǎn)古時(shí)期,沒有文字的時(shí)代,人們靠什么來傳承歷史文化?只能靠口耳相傳,因此,神話就產(chǎn)生了。由于封建統(tǒng)治者的管控限制,歷史的書寫從來都是出自御用文人,而這些歷史也都只是英雄的歷史,沒有民眾的影子。所以,下層的民眾也建構(gòu)了自己的歷史,這便有了傳說、歌謠、民間故事。
孔子晚年編訂文獻(xiàn)資料,為我們保留了大量的民俗資料。尤其《詩》《易》中的歌謠,《書》中的傳說,這為我們探討孔子的文藝民俗觀提供了可能。結(jié)合《論語》文本,我們不難看出,孔子的文藝民俗觀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一)對歌謠的重視
《論語》中的歌謠往往是只言片語,雖然這些歌謠已經(jīng)很難還原本來的面貌,但從《論語》語錄體的特點(diǎn)可以管窺當(dāng)時(shí)社會中歌謠的流行,這些歌謠也顯示出孔子對歷史、社會、人生等問題的思索。如《論語·子路》中的“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yī)。”孔子這句耳熟能詳?shù)母柚{告誡弟子們要有恒心。又如《論語·八佾》引《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子夏從孔子所講的“繪事后素”中,領(lǐng)悟到仁先禮后的道理。
又如《論語·子罕》:
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
豈不爾思,
室是遠(yuǎn)而。
原是一首情歌,孔子加以發(fā)揮,用以表示求道的真心。又如《論語·微子》: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
楚國的一位隱士接輿見到孔子,唱了這首歌謠,歌中以鳳凰喻孔子,諷刺他在天下無道之時(shí)不能歸隱,是一種德行衰敗的體現(xiàn)。但從儒家的角度看,這正是“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除了日常言語引用歌謠外,孔子還重視歌謠的收集和整理,尤其《周易》和《詩經(jīng)》。在某種意義上講,《周易》就是遠(yuǎn)古時(shí)代中原地區(qū)的一部民間歌謠總集[1]。而《詩經(jīng)》則是公認(rèn)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其中的國風(fēng)部分則是采自民間的口頭歌謠。
(二)對神話傳說的態(tài)度
《論語》對孔子及弟子的生活記錄雖然重在說明思想,但許多地方已經(jīng)顯示出民間傳說的雛形,甚至某些就是傳說。譬如前面所說的“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子路遇荷蓧丈人”“長沮桀溺耦而耕”,雖然是片段,但可以看作傳說,何況《論語》本身就是經(jīng)過口頭傳播后形成的文字典籍。這里,我們不僅看到了民間傳說的嬗變形態(tài),而且也可以從中窺見孔子的民間文藝觀。
孔子對神話傳說的態(tài)度是二重的。一方面,生活在由上層文化下移、上下層文化交流的文化語境下,諸子們?yōu)榱诵麚P(yáng)其說,充分利用下層民眾的“嘉言善語”,廣采街談巷語、神話傳說、寓言故事,以求擴(kuò)大自身學(xué)說的影響力。在先秦的典籍中,諸子著作中保存的神話傳說往往是不自覺的,尤其在《論語》等“語”類文獻(xiàn)中,這種利用口傳話語資源進(jìn)行的思想建構(gòu),使其學(xué)說表達(dá)更加故事化、通俗化,甚至更加接地氣,利于民眾接受。(見表1)

表1 《論語》中關(guān)于歌謠、傳說、諺語、神話的記載
另一方面主張“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將歷史介入民俗,拋棄“怪力亂神”的思維,將神話傳說歷史化。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言:“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shí)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zé)o所光大,而又有散亡[2]。”比如堯舜的事跡,多為當(dāng)時(shí)的民間口傳,文獻(xiàn)資料實(shí)為不足以證明這些賢王的存在,但為了給世人樹立道德的楷模,孔子將他們的口傳資料整理下來,甚至日常生活中時(shí)有提及:

續(xù)表1 《論語》中關(guān)于歌謠、傳說、諺語、神話的記載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shí)而仕,趨視四時(shí),務(wù)先民始之……。”(《孔子家語·五帝德》)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wèi)靈公》)
孔子對神的態(tài)度決定了他對神話傳說的觀念,“敬鬼神而遠(yuǎn)之”,因此,他對神話的態(tài)度是否定的。但孔子對神話傳說中的圣王形象又加以推崇,使后人堅(jiān)信歷史確有其人。孔子用人文歷史的觀點(diǎn)透視神話,這就使神話這種精神民俗從上古社會已開始就具有價(jià)值,也在春秋社會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獲得了重要的意義和社會地位[3]。
二、“功能派”的禮俗觀
《論語》中充分反映了孔子的社會治理模式,即仁和禮,前者注重內(nèi)在的修養(yǎng),后者強(qiáng)調(diào)外在的規(guī)范。仁包括“孝、慧、信、智、勇、敏、恭、寬、忠、愛人、博學(xué)、好禮”等一切美好品格。禮是維護(hù)尊卑、長幼、貴賤、親疏等社會政治地位的行為規(guī)范。仁往往外化為禮,在知禮、尊禮中得到體現(xiàn)。孔子以知禮而聞名,“入太廟,美事問。”充分表現(xiàn)了他對禮的重視。其實(shí),這些禮很大程度上都夾雜著民俗的成分,比如婚、喪、嫁、娶、冠、祭、宴等都是具體的民俗事項(xiàng),儀式的程式、場景的布置,乃至所用的音樂都有一套規(guī)范。可以說,孔子的民俗觀是源于其禮樂思想的民俗觀,或者說是禮俗合一的民俗觀。
(一)禮俗合一的思想
民俗的根本屬性是模式化的慣習(xí),是一定范圍內(nèi)民眾群體共同創(chuàng)造并遵循的生活規(guī)范。上古之初,未有法律、哲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等學(xué)科,唯有約定俗成的風(fēng)俗,大家共同遵守,這也是最初的習(xí)慣法。所謂的周禮,實(shí)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將遠(yuǎn)古到殷商周的原始禮儀加以大規(guī)模地整合、改造和規(guī)范化,以適應(yīng)當(dāng)世的階級統(tǒng)治的一種禮儀規(guī)范[4]。也就是說,所謂的禮制,其本源來自于民眾中流行的風(fēng)俗。不過,當(dāng)統(tǒng)治者從民俗中提取某些營養(yǎng)加以升華,就成了早期法律的雛形。
在孔子的言論中,當(dāng)提到上層階級的風(fēng)俗時(shí)則多稱“禮”,這些概念并非孔子的獨(dú)創(chuàng),而是出自對前代禮俗的學(xué)習(xí)。“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xiàn)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孔子是殷商的后裔,近祖為宋國宗室,所以,他能言夏禮和殷禮,除了學(xué)習(xí)所得知識外,更多地是出于他們家族一代代傳承下來的舊俗遺留物。“先進(jìn)于禮樂,野人也;后進(jìn)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jìn)。”(《論語·先進(jìn)》)在孔子看來,這種“野人”風(fēng)行的禮樂是先進(jìn)的,可見他對殷商古俗的尊崇態(tài)度。很明顯,前一句提到的庶民(野人)所保持的“禮樂”就是民俗,在這里,禮俗是合一的。
同時(shí),孔子也注意到禮俗的流傳變異性。“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民眾中流傳的那些不合時(shí)宜的民俗必然會被淘汰,又會有符合新時(shí)代環(huán)境的新民俗應(yīng)運(yùn)而生,對此,孔子是肯定的。“樊遲問知。子曰:‘務(wù)民之義,敬鬼神而遠(yuǎn)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對于夏朝的“遵命文化”與殷商的“尊神文化”,孔子持批判的態(tài)度。孔子“不像各國君主那樣,每逢旦夕禍福,便繞著天地鬼神的形象兜圈子,而是宣傳從事祭祀活動的關(guān)鍵,在于對祭祀對象保持一種至高無上的虔敬態(tài)度[5]”。雖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他“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前后看似矛盾,實(shí)則表明了孔子不流于俗、隨俗入世的態(tài)度。
(二)孔子對禮俗社會治理功能的重視
民俗對社會具有教化、規(guī)范、維系、調(diào)節(jié)等多種功能,“禮之所興,眾之所洽也;禮之所亂,眾之所廢也。”(《禮記·仲尼燕居》)在孔子看來,婚嫁、服飾、宗廟、喪葬、飲食、器物、歲時(shí)、祭祀、宴饗等民俗事項(xiàng)無不對民眾起到浸潤和儒染的作用。人們就生活在這些民俗之中,時(shí)時(shí)刻刻都受到民俗的限制。“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論語》中多處提到孔子的這一思想,他將諸多民俗事項(xiàng)提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使民俗與禮制、政治結(jié)合起來,達(dá)到社會治理的效果。
1.喪葬習(xí)俗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孔子提倡這一喪葬習(xí)俗,旨在為社會樹立一種養(yǎng)老敬祖、奉上愛下的社會風(fēng)氣,以維護(hù)社會和諧。
2.服飾習(xí)俗
《論語·鄉(xiāng)黨》中孔子對著裝有大段的論述,服飾的顏色、款式、配飾,適合的階層、場合、季節(jié)都詳有說明,這種禮俗起著強(qiáng)化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社會維系功能。
3.飲食習(xí)俗
《論語·鄉(xiāng)黨》中除了對飲食的選擇、食材的加工等各個(gè)環(huán)節(jié)有論述之外,還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了飲食中的禮俗。“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飯。”“食不語”。對于既成的禮俗,孔子也認(rèn)為不能隨意更改,否則名實(shí)不副。“觚不觚,觚哉!觚哉!”
4.祭祀習(xí)俗
《論語》中記載有祭祖、祭神(奧、灶),甚至驅(qū)鬼的活動。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論語·八佾》的一章:“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每月初一都要?dú)⒁活^羊來告祭祖廟,子貢或許出于愛惜動物,主張那頭羊也應(yīng)該省去,而孔子卻認(rèn)為告朔必餼羊,無羊,就違背了祭禮制度。
三、結(jié)語
綜上所述,孔子的民俗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五個(gè)方面:一是發(fā)覺民俗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將禮制貫穿于民俗事項(xiàng)之中,民俗、禮節(jié)、政治相結(jié)合,禮俗合一的民俗觀。二是對傳說、歌謠、街談巷語等民間口傳資料的重視,將其納入思想說理之中,以民眾耳熟能詳?shù)拿耖g話語,提升了儒家學(xué)說的通俗性和影響力。三是將歷史介入民俗,拋棄“怪力亂神”的思維,將神話傳說歷史化。四是重視民俗的社會治理功能,通過提倡優(yōu)良習(xí)俗,遏止惡俗陋俗來移風(fēng)易俗。五是將民俗與詩、樂相結(jié)合,用詩樂推助民俗的教化,“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