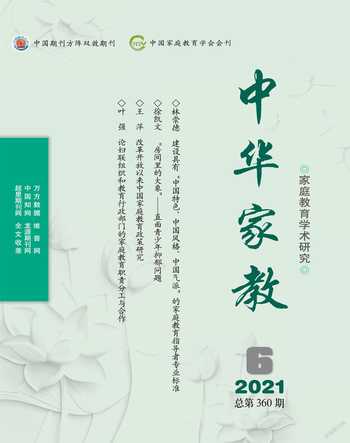大學生抑郁風險及其家庭療愈
海子奕
在世界范圍內,抑郁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病癥。對于處于高等院校的大學生而言,抑郁風險也早已潛入象牙塔的暗影之中。2020年9月,國家衛健委提出,“高等院校要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引發了普遍關注和討論。面對大學生日益顯著的抑郁風險,不禁讓人困惑:大學生抑郁是怎樣發生的?家庭可以如何預防和應對大學生所面對的抑郁風險?本文試圖梳理國內外相關研究,分析大學生抑郁的影響因素,探討基于家庭的療愈之道。
大學生正處于向成年過渡的人生階段,這是一段壓力疊加的時期。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癥狀在世界各地的大學生中都很常見,大學生患抑郁癥的風險遠遠高于普通人群。除了學習問題,一些大學生還要面對與家人分離帶來的壓力,甚至承擔家庭的責任。這一時期身心發展的不平衡會使他們很容易陷入焦慮和抑郁。
據《北京青年報》2016年的一篇文章報道,在一所在京著名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負責人表示:“據粗略統計,5年前,10個咨詢對象里平均一兩個有抑郁癥,而現在則上升到3—4個。”世界衛生組織2017年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四分之一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曾有過抑郁癥狀。國外多所知名大學的調查也顯示,大學生們的精神健康狀況堪憂,抑郁風險激增。密歇根大學的經濟學家Daniel Eisenberg研究發現,2015年有22%的大學生正在尋求心理健康服務(有些規模較大的大學低一些,只有10%,但私立和小型大學高達50%),并且這一比例近20年來都在上升。
對于初入大學之門的年輕人來說,大學生活是一個全新的生活情境。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認為“抑郁的根源就是社會世界中的涵義與關系”。了解大學生抑郁的影響因素,需要關注他們的日常生活。
(一)學業和就業壓力
盡管上了大學,應試的壓力有所減輕,但大學期間的成績還是會直接關聯獎學金、讀研的可能性以及畢業時的職業選擇。因此,學業仍然是主要的壓力來源。許多大學生掙扎于各種科目的考核標準和績點要求,不得不陷入高度競爭性的“內卷”之中。蘇珊娜·布瑞巴克(Susanne Bregnbaek)在近期出版的《脆弱的精英》中就描繪了中國頂尖大學的大學生與極大的期待伴隨的巨大壓力以及他們面臨的兩難困境——“不停歇的自我否定,考試和競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我滿足之間的矛盾”。
此外,就業壓力也是大學生抑郁的重要影響因素。曹文君等人在對不同年級的大學生進行研究后指出,大四學生的抑郁癥狀檢出率較高。這說明處在由學校向社會轉變關鍵時期的大學生可能面臨著多重壓力,既面臨就業、求學深造的選擇,也有來自畢業論文和畢業設計等方面的壓力,更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田圣會對湖南省的10所高校大學生進行了抽樣調查,也發現就業壓力是當前大學生心理壓力的最主要來源。對于更需要一份理想的就業機會來幫助個人和家庭的家境不好的大學生而言,他們面臨的就業壓力則會更大。
(二)家庭環境的影響
作為個體成長的“第一所學校”,家庭在各個方面都深刻影響和塑造著大學生的情緒體驗和心理健康。首先,家庭的經濟條件會直接影響大學生抑郁風險的發生比例。丹尼爾·艾森伯格(Daniel Eisenberg)等人在對美國大學生進行調查后發現,過去或現在有經濟壓力的學生患抑郁癥的可能性要高得多。王蜜源等人也通過研究發現家庭經濟水平困難的大學生抑郁癥檢出率較高。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這些大學生和條件較好的同學之間有較大的反差,這種比較會“加重自卑心”,讓他們和其他同學產生一種距離感,難以獲得人際支持。饒燕婷等基于江蘇省的19所高校的調查也指出,父母文化程度低或者職業是農民的大學生會有更明顯的抑郁傾向。
在經濟條件之外,父母或監護人的親職責任和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也有重要關聯。有學者研究了兒童期受虐和大學生的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認為兒童期受虐經歷會降低主觀幸福感,進一步導致大學生抑郁癥狀。因此,家長或監護人能否履行好親職責任,關系到兒童能否在一個平和、安全的環境下成長,也直接影響他們成年后的人際關系和心理狀態。
(三)互聯網時代的原子化困局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改變,線上交往取代了現實中的許多活動,降低了人和人之間面對面的社會參與度。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為了避免人員流動帶來的安全風險,能線上解決的問題經常依賴于網絡。學生的日常生活更是和互聯網形影不離,社交軟件、電商平臺、線上學習等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格雷格·盧金諾夫(Greg Lukianoff)和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嬌慣的心靈》一書中討論了互聯網時代(書里形容這一代是“Z世代”)大學生群體心理健康所面臨的普遍危機,多重因素共同造就了沒有被煉成的鋼鐵——嬌慣的心靈。羅伯特·克羅特(Robert Kraut)等人曾對73個家庭169個用戶的互聯網使用情況進行了連續兩年的追蹤研究,發現互聯網的使用者與家人以及身邊的交流會減少,社交圈也會縮小,互聯網上彼此的弱連接取代了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強連接,這不僅會降低使用者的心理幸福感,而且會增加使用者的孤獨感和抑郁感。
互聯網開闊了每個人的生活世界,也讓許多大學生沉醉其中。在網上,多元的生活方式既觸手可及又無法企及。互聯網到處展示的理想化身體、職業和娛樂方式,很容易讓人在對比之下產生焦慮和抑郁情緒。讓·特溫格(Jean Twenge)的研究認為,互聯網和新媒體的使用,特別是智能手機技術(smart phone technology)的快速進步可能是誘使大學生抑郁的重要原因,女性大學生尤其深受社交媒體伴隨的“展示版生活”帶來的傷害。上網時,她們無形之中就在與電子媒體的曝光中這些高度理想化的人物和情景進行一種“社會比較”,而這一過程被看作壓力應對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個體抑郁的重要因素。
大學生抑郁體驗反映了他們成長中的心理和情感危機,也反映了埃里克森(ErikHomburger Erikson)所說的“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危機”,有其制度性和社會性根源。大學生的抑郁風險反映了他們身處的高等院校和社會環境中存在問題。盡管造成抑郁的原因是復雜的,但家庭對于預防和干預大學生抑郁風險有著重要作用。勃朗芬勃倫納(Urie Bronfenbrenner)把小系統看成最直接、最重要的生態系統,對人的行為有更大影響,家庭即屬于其中。有研究證實,“熟悉的人的支持對于緩解環境中的壓力源有重要的影響”。
(一)讓孩子“可以傾訴”“有家可回”
很多大學生都是初次離開父母獨立生活,“高依賴性和缺乏社會經驗導致大學生群體在歸因方式和應對方式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除了需要面對學業壓力,他們還要在沒有獲得成年人的技能和認知水平的情況下,去承擔很多類似成人的責任和任務。在各種新的挑戰面前,沒有充分的社會支持讓他們很容易陷入一種無助的困境。這時,家庭能否給予適切的支持就顯得尤為關鍵。
幾乎每一個大學生都有自己的家,卻并非每個人都隨時有家可以回。家庭成員的支持對于消解患者的抑郁情緒尤為重要。但是,許多大學生在遭受學業、就業方面的壓力時,不僅難以得到家庭的支持,甚至很難向父母開口傾訴自己的困擾,由此不斷累積,帶來了嚴重的身心困擾。如果父母能和子女建立起友好、民主的關系,那么子女就更有可能在面對困境時有傾訴和獲得支持的可能。而總是貶低、打壓和指責孩子的父母,就在無形之中關閉了孩子的求助通道。父母需要和孩子共同營造出溫馨、平等、安全、信任的家庭氛圍,讓孩子可以放心傾訴,讓家成為“溫馨的港灣”。
(二)健康的陪伴和愛
每一個家庭都會形成獨特的親子關系和情感結構。在一些寒門家庭,子女經常承受著一種“有負擔的愛”。這里的家庭關系常常是報喜不報憂的,孩子和父母的交流是堵塞和不通暢的,心里很容易積壓情緒。而在一些經歷了從底層打拼歷程的知識分子家庭,則會在描述“優秀”時常常提到“我像他那么大的時候,我都能干……”,經常對子女做出“不爭氣”的評價。在這樣的家庭成長,容易造成內心壓抑、叛逆。健康的親子關系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輕松又不摻雜過多的附加條件的,父母和子女之間最合宜的關系也許就是像李辛在《精神健康講記》中所言,“是簡單的、平靜的,你看到她以后心生歡喜,互相吸引,但是沒那么多纏繞沖突的力量”。
此外,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父母要學會適當放手,避免過度干涉,把孩子的人生等同于自己的人生。在獨生子女政策下成年的大學生們,體驗的家庭生活常常是“錦衣玉食、壓力飽嘗”。對于這些大學生而言,他們甚至成了一個家庭,甚至家族里“唯一的希望”,父母希望自己的付出和犧牲能夠讓子女獲得“盼望的精英職業”。但是過度強烈的盼望和控制既束縛了孩子的成長,也束縛了自然而然的親子關系,給子女的成長扣上重重枷鎖。唯有給予孩子充分的自由,才能讓孩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得到充分的發揮,促使孩子不斷去拓展自我能力的邊界,賦予成長更多的可能性。
(三)“去污名化”
“抑郁”是一個讓人臉色頓時凝重的詞語,與它相伴的常常是人生苦難。正因為如此,許多家庭對抑郁是談之色變,是逃避和恐懼的。沃格爾(Vogel)就認為人們不愿意尋求心理幫助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污名。郝志紅也在以大學生為樣本進行研究后發現,他們自身的污名越多,就對心理咨詢的態度越消極,尋求心理幫助的意愿就越低。
直面大學生抑郁風險需要父母與孩子一起積極建構健康的家庭文化。同時父母需要敢于自省,承認自己可能給孩子帶來了不好的影響,接納他們的不完美。如果一個家庭的父母是難以接受子女抑郁的,那么子女就更有可能將自己封閉起來,把偽裝出的“好”的那一面展現給父母,這將給被抑郁困擾的大學生帶來更大的壓力。因此.父母對心理困擾的開放態度將很大程度上拓展子女尋求心理幫助的可能性。處于心理困境中的孩子更需要父母基于共情的關心和照護,由此逐步建立起對外界的信任感。
此外,大學生抑郁問題是對當前高等院校學生培養和相關制度的預警。2020年9月,《三聯生活周刊》-篇名為《績點為王:中國頂尖高校年輕人的囚徒困境》的文章對精英大學的“內卷”生態進行了深描,“中國最聰明的年輕人在極度競爭中,成功壓倒成長,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去年黃燈出版的《我的二本學生》中也刻畫了二本的年輕人“嚴酷的擇業競爭”和“日漸逼仄的上升空間”。高等院校亟須完善心理健康預防與干預體系,破除對抑郁的敏感和污名化。健康的社會、大學和家庭是直面大學生抑郁風險,幫助大學生走出抑郁困擾的根本途徑,也應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追求。
(責任編輯:母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