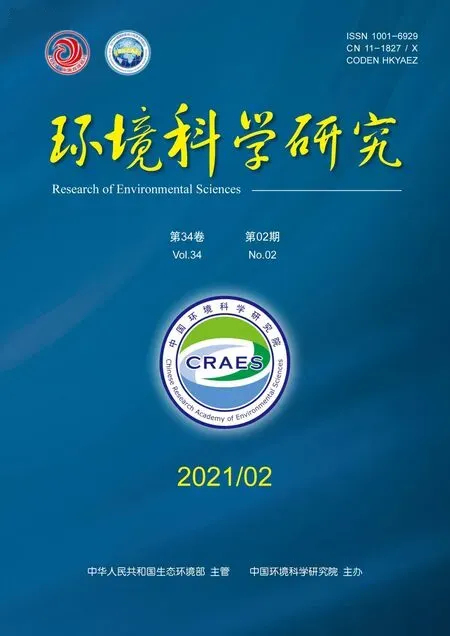土壤中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污染現狀及環境行為
陳詩艷, 仇雁翎*, 朱志良, Leo W. Y. Yeung
1.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長江水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上海 200092 2.上海污染控制與生態安全研究院, 上海 200092 3.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 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上海 200092 4.瑞典厄勒布魯大學科學技術學院, 人-技術-環境研究中心(MTM Research Centre),瑞典厄勒布魯 SE-70182
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perfluoroalkyl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s)憑借其優良的穩定性、表面活性及疏水疏油性,在工業和生活中大量生產、應用和排放. 由于PFASs在環境中的持久性,使其在全球范圍內各種環境介質中被廣泛檢出,如大氣[1]、水[2]、沉積物[3]、室內灰塵[4]、野生動物[5]和極地冰蓋[6]等,甚至在人體血液中也有檢出[7-9]. 毒理學研究發現其對內分泌、神經、免疫、生殖系統等系統都具有毒性和致癌性,危害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7]. 2009年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 sulfonic acid, PFOS)及其鹽類和全氟辛烷磺酰氟(PFOSF)被列入《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簡稱“《POPs公約》”)附錄B[10],隨后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 PFOA)和全氟己烷磺酸(Perfluorohexane sulfonic acid, PFHxS)也被列入候選名單[11],2019年PFOA及其鹽類以及部分可以降解為PFOA的化合物正式列入《POPs公約》附錄A[12],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如加拿大、中國和歐洲化學品管理局等)相繼出臺政策和措施對其進行管控[13].
土壤被認為是PFASs等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一個重要的匯[14-15],近年來許多國內外研究者對PFASs在土壤中的污染水平、分布特征、影響因素及其環境行為開展了一系列研究. 2010年研究者首次報道了上海市農業、住宅和工業區周邊表層土壤中PFASs的濃度[16],已停產和正在生產的氟化工廠周邊土壤中PFASs含量的差異也受到廣泛關注. 2020年有研究[17]發現,6∶2氯代多氟醚磺酸(6∶2 Chlorinated polyfluorinated ether sulfonic acid, F-53B)等新型PFASs在我國多個省份土壤中也有檢出,其檢出率甚至高于PFOS等傳統PFASs. 此外,除了PFASs自身的物化性質以外,土壤有機質含量、微生物作用、植物種類等都會影響其在土壤中的遷移轉化,一些易揮發的前體物質最終會轉化為穩定的PFASs,從而在土壤中長期存在. 該文以相關文獻報道為基礎,總結了PFASs在土壤中的污染現狀、遷移轉化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并提出了未來有關土壤中PFASs的研究可以關注的重點和方向,希望能夠對全面認識PFASs在環境中的賦存狀況與遷移轉化機制、更好地管控PFASs污染以及開展生態與健康風險評價有所助益.
1 常見的PFASs及其應用
PFASs是碳鏈上與碳原子相連的全部或多個氫原子被氟原子取代,末端帶有羧基、磺酸基等官能團,所形成的整體或部分含有CnF2n+1-基團的人工合成的化學物質,分為全氟烷基羧酸類(Perfluoroalkyl carboxylates, PFCAs)、全氟烷基磺酸類(Perfluoroalkane sulfonates, PFSAs)、氟聚醇類(Fluorotelomer alcohols, FTOHs)、全氟磺酰胺類(Perfluorosulfonamides, FOSAs)等[18],常見的傳統和新型PFASs的名稱、分子式和應用情況見表1[18-19]. 基于毒性和生物累積性的差異,相關機構對長鏈和短鏈PFASs進行了定義[18]:對全氟烷基磺酸類而言,碳原子數目≥6的稱為長鏈PFSAs;對全氟烷基羧酸類而言,碳原子數目≥7的稱為長鏈PFCAs;反之為短鏈化合物.

表1 常見的傳統和新型PFASs的名稱、分子式、應用及CAS號[18-19]

續表1
2 土壤中PFASs的污染現狀
環境中PFASs的來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來自于生產和使用氟化物過程中的直接釋放,二是來自于其前體物經過大氣遠距離遷移、沉降和生物轉化等作用的間接生成. 研究PFASs在不同區域、不同類型土壤中的分布與賦存特征,有助于全面地了解其地域分布、含量水平與組分特征,對該類化學物質的管理具有重要意義.
2.1 氟原子質量平衡分析
PFASs種類眾多,但現有分析方法能準確識別且定量的PFASs種類仍十分有限. 通過進行氟原子質量平衡分析,可以推算樣品中不同形式氟化物的豐度和濃度[20],從而為解析PFASs來源、探討其遷移和轉化等環境行為提供依據. 根據可提取吸附有機氟(EOF)與總氟(TF)的比值(EOFTF)以及已知PFASs與EOF的比值(PFASsEOF)可以推算樣品中PFASs的總體含量情況,同時也是進行未知PFASs篩查的基礎. 目前,有關土壤中氟原子質量平衡分析的研究較少,從已報道的數據來看,已知的PFASs僅占了環境中有機氟總量的小部分,未知氟化物仍占較大比重. 例如,中國遼東灣土壤中PFASsEOF和EOFTF分別為0.77%和0.02%[21],在淮河流域這兩個比值分別為0.30%和0.02%[22];在尼泊爾科什河二者分別為0.39%和0.02%[23]. 相比水[24]、血液[25]、野生動物[26]和海洋哺乳動物的肝臟[27]中的含量水平,土壤中已知PFASs的含量要低得多. 這既與PFASs的生物富集性有關,也受現有提取方法的限制.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優化土壤中PFASs的提取及分析方法,以便篩查出更多未知的氟化物,從而對土壤中的含氟化合物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2.2 土壤中的主要PFASs組分
PFASs的鏈長和結構決定了它們在環境中的傳輸能力和歸趨方式[28-29],相比于短鏈PFASs,長鏈PFASs在水中的溶解度和流動性較低,更容易吸附于土壤中的有機質上,因而長鏈PFASs在土壤中的賦存更為普遍[30],其中PFOS和PFOA是兩類主要污染物,但不同地區土壤中PFASs的具體組成特征存在差異. 例如,尼泊爾科什河沿岸土壤中檢出率較高的是PFOA和PFBS[23];韓國農業土壤中PFHpA和PFDA的檢出率最高,其次為PFOA[31];我國農業土壤中PFOS、PFOA、PFDA等均有檢出,但未檢出PFHxS和PFBS[32-33],在一些地區短鏈PFASs和前體物質也均有檢出,但濃度不高[34-36]. 目前關于我國土壤中PFASs賦存狀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和湖北、廣東、云南等少數中部和南部省份,其他區域的研究相對較少. 2020年有學者[17]在我國土壤中檢出了新型PFASs(如F-53B、HFPO-DA等),其中F-53B作為PFOS的替代品被頻繁使用,其檢出率(98.9%)甚至高于PFOS(85.4%),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內尚鮮見報道.
由于PFOS比PFOA具有更高的Kd(固液分配系數)值,導致PFOS比PFOA更容易吸附在顆粒物上[37-38],故土壤中PFOS的濃度往往比PFOA更高. 然而,實際土壤中PFOS的濃度并不總是高于PFOA,如中國渤海和黃海周邊[39]、中國天津于橋水庫[9]、韓國西海岸[40]和美國[41]等土壤中的PFOA濃度均高于PFOS濃度,這可能與降水的影響有關. 有報道發現,我國東部地區雨水中主要的PFASs是PFOA[42],因此推測降水會攜帶PFOA進入土壤,使得實際土壤中PFOA的濃度比PFOS更高.
2.3 土壤中PFASs的含量水平及其來源
表2列出了我國土壤中PFOS、PFOA和PFASs含量的總體水平. 分析發現,我國多數非氟化工生產地區土壤中PFASs的含量在pgg至ngg水平,與瑞典[57]、韓國[31]、馬耳他共和國[58]、烏干達[30]等國家和地區相當,且基本都低于由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提出的基于健康土壤中PFASs的最低濃度參考值(PFOS,6 mgkg;PFOA,16 mgkg)[59]. 在氟化工廠周邊或一些使用含氟制品集中的地區,土壤中的PFASs遠高于普通地區的污染水平. 例如,在遼寧阜新氟化工廠周邊花園土壤中PFBS的濃度(42.10 ngg)遠高于其他地區[21,56]. 不僅是中國,美國、日本和墨西哥工業區及污水處理廠附近土壤中PFAS的含量也高于其他地區,最高含量分別為129、35.5和10.80 ngg[41]. 美國某空軍基地消防員訓練區土壤中PFOS濃度最高達到了5.20×103ngg(平均值為21 ngg),PFOA的濃度范圍為11~2.0×104ngg(平均值為2.4×103ngg),此外還檢出了高濃度的PFASs前體物[60]. 可見,含氟化學品的生產或集中使用造成了所在地區土壤中PFASs的污染,未來需要關注此類污染土壤的修復.
由表2還可以看出,在我國一些非氟化工區土壤中的PFASs含量甚至高于氟化工區,究其原因:①可能是因為空氣傳輸,短鏈PFASs或前體物經大氣傳輸后經干、濕沉降進入土壤,在生物、化學等作用下會轉換成為PFASs,從而在一些無直接污染源排放的地區(如居民區、偏遠地區等)被檢出[61]. ②可能是因為當地未知污染源的排放. 除了傳統PFASs,新型PFASs的濃度也值得關注. LI等[17]分析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89個樣本時發現,6∶2 Cl-PF ESA的濃度〔平均值為(0.16±0.20)ngg,中值為0.08 ngg〕、8∶2 Cl-PFESA的濃度〔平均值為(0.61±0.19)ngg,中值為0.02 ngg〕已經與PFOS〔平均值為(0.19±0.50)ngg,中值為0.09 ngg〕相當,可見在我國新型PFASs的使用也越來越多.
2.4 不同類型土壤中PFASs的含量與組分
不同類型土壤因其理化性質、利用方式及周邊環境和人類活動的差異均會影響PFASs的組成及其含量水平. Lee等[31]在分析韓國不同類型土壤中PFASs時發現,森林土壤中PFASs總濃度(平均值為2.79 ngg)明顯高于荒地(平均值為1.18 ngg),隨著土壤中有機碳(OC)和有機質(OM)含量的增加,PFASs含量也增加. 尼泊爾森林土壤中PFASs的平均濃度(0.96 ngg)普遍高于種植玉米、蔬菜和水稻的農田土壤(0.44 ngg)[23],推測是因為林地土壤有機質充足,而農田由于受到有規律的犁耕和輪作可能會加速土壤退化,土壤中有機質含量降低,污染物更容易通過淋溶作用進入地下水. 有研究者[62]測定了深圳市76份表層土樣品,發現PFASs的含量受區域功能影響顯著,呈現工廠周邊(平均值35 ngg)?十字路口(平均值5.4 ngg)>居民小區(平均值2.3 ngg)?公園(平均值0.98 ngg)>城市背景(平均值0.49 ngg)的特點;

表2 我國土壤中PFOS、PFOA和PFAS總含量水平
其中,工廠周邊、居民小區、公園表層土中PFASs以中長鏈為主,而十字路口則中短鏈PFASs較多,主要是由于十字路口車流量大,車輛剎停啟動頻繁,輪胎等磨損碎屑可將橡膠等材料中的PFOA釋放到周邊環境中,產生較高污染.
3 PFASs在土壤中的環境行為
PFASs在土壤中的遷移、分布和轉化情況取決于物質的自身性質、土壤的理化性質以及物質和介質之間的物理、化學和生物等反應過程. 研究PFASs在土壤中的環境行為,深入了解其遷移轉化機制,明確其來源和歸趨,對于防控土壤中PFASs的環境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3.1 PFASs在土壤中的遷移分布
作為一種陰離子型表面活性劑,PFASs分子結構中的親水基(如羧基、磺酸基等)和疏水基(碳鏈)使其同時具有親水性和疏水性[18]. 土壤是由固、液、氣三相組成的復雜系統,PFASs在土壤中具有相對復雜的吸附-解吸過程. 研究表明,土壤中PFSAs濃度較PFCAs高,這是由于與羧基化合物相比,磺酸基化合物水溶性較低,且碳鏈越長,吸附潛力越高[63]. 如Higgins等[28]研究了8種長鏈PFASs在沉積物中的吸附行為,發現碳鏈每增加1個CF2基團,KOC(有機碳吸附常數)值即增加0.3~0.6個對數單位;碳鏈長度相同時,磺酸類比羧酸類在沉積物上吸附的多(約多0.2個對數單位). Enevoldsen等[64]采用Freundlich等溫曲線對6種PFASs在土壤中的吸附和解吸行為進行擬合,得到吸附和解吸的Kd(固液分配系數)值范圍分別為0.1~33和0.3~65 Lkg,說明土壤對PFASs具有高吸附、低解吸的特性,使其向地下水中遷移的傾向受到一定抑制. 也有研究[65]表明,目前廣泛采用的短鏈PFASs替代品在土壤中有較強的移動性,對地下水具有潛在風險.
除PFASs本身的特性外,土壤對PFASs的吸附受土壤pH、有機質、共存金屬、陰離子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有機質含量是最主要的因素. Milinovic等[37]發現6個有機碳含量較高的土壤樣品對PFOS、PFOA和PFBS的吸附程度都較高,同時發現吸附能力隨PFASs疏水性的增加而增加. MIAO等[66]也發現,PFOA的主要吸附過程是全氟碳鏈與土壤有機組分之間的疏水相互作用. 盡管沉積物對PFASs的吸附會隨Ca2+濃度的升高以及pH的下降而升高,但有機碳仍是影響吸附的主要因素[28]. F-53B的最大吸附量與土壤有機質含量呈正相關,而在Cu(Ⅱ)、Cr(Ⅵ)和硫酸鹽等無機離子存在的情況下,F-53B的吸附能力普遍下降[67].
3.2 PFASs在土壤-植物系統中的傳輸轉運
土壤-植物體系中植物吸收和土壤吸附是PFASs的主要歸趨方式,此外還有揮發、光解、水解和生物降解等過程[68]. PFASs從土壤固相被解吸到土壤間質水中,吸附到植物根系上,然后穿透根表皮,在植物蒸騰作用的驅動下從根部沿著木質部運輸到芽、葉等不同器官中[69-70]. 研究[71]表明,玉米、燕麥、小麥、土豆、生菜、黃瓜和胡蘿卜等作物都能吸收富集PFASs. 但若是土壤中存在較高含量的有機碳,則會降低PFASs從土壤到植物體內的遷移和積累能力[72-73]. 因此,PFASs從土壤到植物的遷移能力不僅取決于土壤中初始PFASs濃度,還取決于土壤中可淋出的PFASs量.
不同pH下植物對PFASs的吸收速率存在差異. PFASs是一類可電離的有機污染物,可以通過質子化或去質子化以離子或者分子形式存在于環境中,二者通過細胞膜的能力有所不同. 例如,酸根陰離子滲透膜的能力比相應的中性分子弱,一般含有弱酸陰離子的物質在植物體內的吸收具有pH依賴性[74]. Krippner等[75]發現,pH越高,玉米根部對PFDA的吸收速率越低. 這是因為PFDA酸度系數較高,在較低pH下具有更強的質子化能力,可以在給定時間段內以更高的速率被玉米根吸收. ZHAO等[76]報道了PFOS在小麥中的pH依賴性,發現在pH=6時有最高的吸收量,并認為小麥吸收PFOS主要是通過促進擴散和主動轉運的方式.
進入植物體內的PFASs通常傾向于在富含蛋白質的組織中積累,而非脂肪含量高的組織中. 由于不同植物的蛋白質、脂質、水分等含量不同,因此PFASs的積累分布情況與植物種類有很大關系. 例如,甜豆和番茄對PFASs的吸收無偏好,蘿卜和芹菜對短鏈PFASs的吸收較好,因為后者缺少根部和莖部之間控制水分、營養成分等物質進出的凱氏帶,短鏈PFASs可以隨水分自由輸送到植物各部分[72,77]. 有研究在玉米中未檢測到PFOA,但在其他植物如山藥根中發現了PFOA[30],推測是由于玉米比山藥有更高的脂質含量,從而抑制了PFOA的吸收[78]. 與玉米籽相比,小麥籽對PFCAs的富集能力更高,可能與小麥中蛋白質含量較高有關[56].
除了受到植物種類的影響以外,PFASs在同一植物不同器官(如根、莖、果實等)中的分布積累也略有不同,這與其物理化學性質(如碳鏈長度、官能團種類及位置等)有關. 如隨著碳鏈長度的增加,PFASs從植物根部到地上部分的遷移速率呈下降趨勢[70,72,77],這主要是由于長鏈PFASs具有較高的親脂性和相對分子質量,較難運輸,而相對分子量小、親脂性較低的PFASs更容易從根部向地上部分轉移[69,79]. 因此,長鏈PFASs主要分布在植物根中,而短鏈PFASs主要分布在葉片和果實中. 相同碳鏈長度的PFASs,其在植物各器官之間轉移的傾向性也有所不同. 例如,Stahl等[80]發現,PFCAs較PFSAs更容易從根部轉移到莖部,而PFSAs較PFCAs更容易從莖部轉移到籽粒.
3.3 PFASs前體物在土壤生物作用下的轉化行為
在土壤生物作用下,PFASs前體物質會在土壤中發生生物降解與轉化,是土壤中PFASs的主要間接來源. 例如,N-乙基全氟辛烷磺酰胺乙醇(N-EtFOSE)、N-乙基氟辛烷磺酰胺(N-EtFOSA)在好氧土壤中經過氧化反應、脫烷基、脫氨基等作用會轉化為PFOS[81-82]. 氟代酮磺酸(FTSAs)、FTOHs及多氟烷基磷酸二酯(diPAPs)可以通過生物、化學作用生成氟代酮羧酸(FTCAs)、氟代不飽和羧酸(FTUCAs)和PFCAs[83-84]. 不同的土壤環境及生物條件也會影響PFASs的轉化產物及轉化速率. 好氧環境下6∶2 FTSA轉化產物是短鏈PFCAs(C4-C6),通過脫硫、氧化產生中間產物6∶2 FTCA,在微生物作用下進一步生成PFPeA、PFHxA和PFBA[85-86]. 在靜態封閉和開放的土壤系統中,6∶2 FTOH的主要轉化產物與6∶2 FTSA相似,而8∶2 FTOH的轉化產物為PFOA和PFHxA[87],相比于開放的土壤系統,封閉系統中轉化產物的濃度更高,推測是因為開放系統中空氣流通加快了FTOHs的揮發[88-89]. 與無植物生長的土壤相比,小麥會增強10∶2 FTOH在土壤中的降解潛力,土壤中轉化產物為PFOA、PFNA、PFDA,在小麥根中轉化產物為PFPeA、PFHxA和PFDA,小麥芽中檢測到PFDA和PFUnDA,小麥中其檢出濃度較土壤中高[90]. 此外,ZHAO等[91]發現,N-EtFOSA在動物、植物或土壤中都會轉化為PFOS,但PFBS和PFHxS等短鏈化合物僅在植物中有轉化. diPAPs在不同植物存在條件下也產生了不同的轉化產物,如胡蘿卜存在的土壤中檢測到了PFNA、PFHxA、PFHpA、PFBA、PFOA等,然而在生菜中只有檢出PFOA[83]. 可見,PFASs前體物在土壤中的降解轉化主要受物質本身所含非氟化官能團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土壤環境條件和土壤中動物、植物種類的影響,但具體影響及作用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4 結論與展望
a) PFASs作為一種新興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已有的國內外關于其污染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體、灰塵、人體血液及尿液等介質中,而有關其在土壤中的污染狀況、分布特征及環境行為研究還很欠缺. 現有研究表明大多數土壤中PFASs含量在ngg水平,由于生產和使用情況不同,不同地區其同系物組成及含量水平存在較大差異. 我國關于土壤中PFASs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東部地區及氟工廠周邊,其組分以PFOS和PFOA為主. 在眾多外在影響因素中,土壤中PFASs的含量水平與土壤有機質含量和周邊人類活動的關系最為密切.
b) 土壤對PFASs的吸附受土壤pH、有機質、共存金屬、陰離子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目前土壤中檢出的PFASs主要以長鏈組分為主,由于提取和分析方法的限制,可以準確定性、定量的PFASs僅占土壤中氟化物總量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含氟化合物仍舊處于未知狀態. 因此,進一步優化土壤中PFASs的提取及分析方法,爭取盡可能多地鑒定未知的PFASs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一些新型的PFASs(如F-53B)在土壤中的檢出率很高,檢出濃度也比較可觀,值得進一步關注.
c) 在土壤-植物系統中,PFASs的傳輸主要依靠擴散及植物蒸騰作用,受物質濃度和環境pH影響,易于在蛋白質含量高、脂質含量低的植物和組織中富集. 短鏈PFASs比長鏈PFASs更容易隨水分從根部向地上部分遷移,相同碳鏈長度的PFASs,羧酸類更容易從根部向上遷移,這與物質的親水性大小有關.
d) PFASs前體物質會在土壤生物的作用下發生代謝與轉化,是土壤中PFASs的主要間接來源. 限于已有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對于PFASs在土壤中的行為機制和生物效應仍需進一步探索,未來可以從生態安全和健康風險的角度出發,開展更加系統深入的有關土壤中PFASs的生物可給性和生物可利用性研究,并進一步評估PFASs對人體的健康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