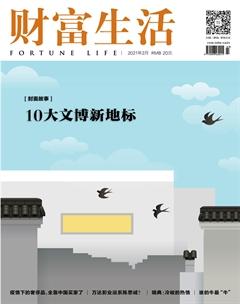10大文博新地標
盧娜 周一澤

自2013年起,擁有20多年歷史的世界著名設計網站Designboom,每年都會評選過去12個月里全球范圍內最受歡迎的優秀設計項目,幫助人們快速回顧一年來的好作品。在今年發布的“2020十大博物館及文化中心”榜單中,中國有四家入選,分別是景德鎮御窯博物館、順德和美術館、上海章堰文化館、北京白塔寺胡同美術館。
當我們走進這些文博新地標,近距離欣賞和領略人類文明與智慧結晶的同時,或許也能從中窺得文博場館建設、運營的新趨勢——
順德和美術館
安藤忠雄設計

廣東順德地處嶺南,它擁有很多頭銜——粵劇發源地、世界美食之都、中國家電之都。然而不同于北上廣這樣擁有豐厚藝術土壤的一線城市,在和美術館落成之前,順德的藝術生態卻較為貧瘠,幾乎沒有類似的藝術機構。
本著回饋家鄉的使命與造福大眾的愿景,何建峰家族想要投資興建一家非營利民營美術館,并希望通過關注從近代文化藝術思潮到國際視野下的當代藝術進程,建立起傳播的樞紐,挖掘跨文化的多元價值,為公眾呈現獨具魅力的展覽和多元開放的文化活動,讓藝術更好地融入當地社區。為此,何建峰家族邀請了全球設計美術館最多的日本知名設計師——安藤忠雄承擔和美術館的設計工作。

“我希望將中國南部地區延續千年的多樣文化融合在一起,并探討一種獨屬于嶺南地區的建筑形式。” 在談及和美術館的設計時,安藤忠雄這樣說,而他從中原古建筑的“天圓地方”及嶺南園景中,借助純幾何學立體的交錯而創造出具有嶺南建筑文化特征、呈現光影禮贊的建筑風景。


目前,美術館內藏有繪畫、書法、攝影和雕塑等500多種作品。根據安藤忠雄的設計理念,為了凸顯“和諧”的主題,和美術館的四層主體建筑由四個大小不一的圓累疊而成,像水波紋一樣由中心向四周擴散。這些“圓”以一定的偏心率由下往上逐漸擴大,立體的“圓”隨之偏移,在賦予各個空間明確的中心對稱的同時,豐富了序列的變化效果。主體建筑內,安藤忠雄首次挑戰在中庭設計清水混凝土雙螺旋樓梯。它既有方便觀眾的考量,觀眾進入不同樓層時,無需花費過多時間沿著圓形展廳尋找樓梯,同時也在美術館空間內部創造了一處令人屏息的圓形奇觀。
一座富有文化創造力的城市必定會擁有富有創造力的博物館,這里的人們“不僅建造了博物館,也填滿了博物館”,而對于順德來說,和美術館的開幕或許只是一個開始。
大象博物館?
曼谷項目工作室設計

大象在泰國有著特殊的地位,它們不僅是皇室典禮的一部分,還曾在歷史上作為戰爭動物幫助國王征戰四方。泰國人尊重這種動物,并與其建立起了獨特的關系。比起寵物或勞力,他們更愿意把大象視為家庭成員。在泰國東北部素林府(Surin)的少數民族——奎族(Kui)的村落中,這一紐帶可能更為強大。幾個世紀以來,當地人一直與大象共同生活,從出生至死亡,難分難舍。

然而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由于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素林府原本蔥郁的森林遭到了破壞,致使奎族人和他們的大象遭遇極端干旱以及食物、藥物的短缺。無奈之下,他們只得離開村落,前往旅游城鎮謀生,其中一些人的生活條件十分堪憂。
作為“大象世界”項目的一部分,大象博物館由當地政府發起,旨在幫助奎族人和大象重回他們的故鄉,并確保大象擁有合適的生存環境。該項目還包括一個休閑空間瞭望塔。
正如博物館的建筑師所說的那樣:“人類與被視為兒童而不是寵物的大象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這種文化和智慧,已在這片泰國擁有馴化大象數量最多的鄉村世代相承。”因而這里不僅僅是展出物品的場所,還要傾聽和體現現居于此的村民以及200多頭大象的心聲——體現人與大象間的家人關系而非對動物的殘忍利用,同時還有對未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美好憧憬。
瑞士愛彼制表博物館??
BIG建筑公司設計

2020年6月,由丹麥著名設計公司BIG為瑞士頂級鐘表制造商愛彼(Audemars Piguet)設計的全新螺旋形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愛彼鐘表博物館位于瑞士勒布拉蘇斯(Le Brassus)小鎮,從汝拉溪谷(Vallée de Joux)拔地而起,將愛彼創始人于1875年創立的首家制表工坊與一棟嶄新的玻璃幕墻建筑巧妙結合。
玻璃幕墻建筑整體采用雙螺旋式結構,與自然景觀渾然天成。玻璃結構的涼亭是對最古老的建筑的補充。新結構仿佛從地面升起,從地板到天花板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整個偏遠山谷的景色。屋頂上遍布草坪,夏日解暑降溫,冬天更似一塊巨大的牛乳卷般柔軟。綠色的屋頂在吸收水分的同時,還有助于調節溫度。而螺旋形的結構則是一種設計上的隱喻,彎曲的玻璃墻循著順時針方向匯聚,頗有一種在鐘表內行走、探索的新鮮感,“邀請”參觀者探索博物館是如何將歷史和創新融為一體的。
博物館內部陳列著一系列雕塑與模型,生動模擬著手表的內部運作,交互式展示的區域則開放給想要嘗試制表技術的訪客使用。可以說,這里既是一座博物館,也是愛彼的制表匠們的工作場所,設計包含傳統的工坊,游客可在這里觀察員工制作鐘表的情況。博物館跨越了兩個世紀,展示了300多塊古董手表,包括復雜化、小型化和非常規設計的制表技能。參觀者可以借此機會深入了解瑞士汝拉溪谷的制表歷史,探索愛彼的時計作品如何從勒布拉蘇斯走向全球。
此外,作為同一園區的一部分,愛彼正在建造一座新酒店,預計將于2021年夏季開放。
上海章堰文化館?
水平線設計


章堰村位于上海西郊的重固鎮,是上海古文化的發源地。經過歷史變遷,章堰村空心化嚴重,因而在新型城鎮化的政策背景下,生存、生長、新生,是實現“章堰文化館”以及改造、復興章堰村的三大要素。
對照中國現狀下的同類村落,主流方式不是推倒重建,不是修舊如舊,而是遵循歷史的發展脈絡,將當下的發展觀念和功能需求置入其中,重新梳理和組織布局、功能業態、新老關系等。
設計師認為,老建筑是章堰村的歷史,文化的沉淀,可通過加固、修繕等方法,讓老建筑以更好的狀態“生存”下去;破敗、無法再使用其內部空間的老建筑則需在“清理”破敗及無法使用的部分后,從中“生長”出與原老建筑有關聯的新建筑,使新老建筑共存;新建筑則是新時代與新功能的呈現,為滿足新的使用需求,設計方案也需“新生”出一些當代建筑。
為此,設計方案對章堰村的一系列建筑物進行了翻新。博物館包括三個展廳,每個展廳都圍繞著水露臺組織成單個空間,主題從“當代”到“傳統”到“未來”。建筑事務所將舊建筑與新建筑融為一體,并盡可能保留了原有的建筑。新老建筑和諧共存,由此產生的作品既滿足當代需求,又彰顯傳統意韻。
文化館基地包含了原村史館(清朝老房子)、章家宅(破敗的晚清老房子),及一部分空地。根據基地條件,文化館設計由三個具備不同特點的展示空間以及水院組成。其中章家宅為展廳一、村史館為展廳二,而村史館北側空地經過復原研究后,在原有基礎位置上新建了展廳三,其均質的金屬材料帶來某種“未來”感的體驗,與展廳一的“當代”、展廳二的“傳統”構成一段動態的體驗。此外,走出展廳三便是基地北側的空地,在保留空地上的大樹及竹林的基礎上新建了休息區和水院,供人們休息和討論。
休斯頓藝術博物館(擴建)?
斯蒂文·霍爾建筑師事務所設計

經過十年的規劃設計與施工,休斯頓藝術博物館擴建新場館——南希和里奇·金德(Nancy & Rich Kinder)中心于2020年11月21日向公眾開放。未來,該博物館將致力于展示國際化的現代藝術品和收藏品,展品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包括藝術收藏品、攝影作品、印刷品、裝飾藝術以及手工藝品等。
擴建的新場館由斯蒂文·霍爾(Steven Holl)和他的事務所設計,在建筑設計界,他獲得過眾多獎項,甚至有人評論說:“美國建筑界在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 Kahn)之后,整體太輕浮、太商業化,而斯蒂文幾乎以一人之功挽救了美國建筑師的尊嚴。”
那么被賦予如此高評價的斯蒂文·霍爾的作品究竟有何獨特之處?這棟新博物館或許能給出答案。
建筑以通透性為特色,首層在不同高度向外開放。7個花園劃分了建筑邊界,確立了入口點,切割形成了建筑立面。最大的花園庭院位于Bissonnet街道和主街道的拐角處,標志著新休斯頓藝術園區的入口點。當來訪者站在入口大廳時,其可以在四個方向看到不同的庭院,從而感受到一種特殊的開放感。
中心上方設計了一個全新的頂蓋,可從內部以180°欣賞到德克薩斯州天空的景色。相較采用人工且重復的照明設計方案,這里創造了一個更為有機且流動的美術館光環境。設計師參考了云朵的弧形線條的凹曲線頂蓋設計,使得天光可以從邊緣進入藝術館內部,滿足了頂光的照明需求。獨特的曲線造型,還使得光線能在內部進行漫反射,從而營造獨特的美術館空間體驗。
外立面材料方面使用了透明玻璃,利用其獨特的弧線造型,給美術館帶去了一絲柔軟。在夜間,這些透明的玻璃立面還會反射水庭院的景色,從而營造獨特的視覺效果。可以說,南希和里奇·金德中心的落成,其本身就為休斯頓藝術博物館增添了一件建筑藝術品。
角川文化博物館?
隈研吾建筑都市設計事務所設計


當代著名建筑設計師隈研吾新近在日本設計了一座整體式博物館建筑——角川文化博物館,它位于東京市中心以西約30公里處的“所澤櫻花城(SAKURA TOWN)”內,在2020年11月下旬向公眾開放。該項目還包括以動畫為主題的酒店、書店和可舉辦各種活動的室內展館,甚至還包括了神社,以及角川辦公室等規劃設置,同樣由隈研吾和他的團隊設計。
角川文化博物館總共有五層樓高。從外觀來看,就像從地面突然升起的奇幻巨石,是由大約兩萬片、每片約50至70公斤的花崗巖打造的奇幻建筑;建筑立面被切割成不規則的多面體,陽光灑落時的光影與一旁水池的相互映照,使建筑呈現變化多端的樣貌,看起來是動態的而非靜態。宛如地面奇幻巨石的外觀、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般的書架劇場。
一樓設有小型圖書館和1000平方米的畫廊,用于舉辦自然、科學、藝術、自然史、時尚、環境、社會等各種主題的展覽。第二層設有一間咖啡廳和一家商店,而第三層被整體專用于動畫的呈現。
第四層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挑高的圖書館,通過投影映射,可以變成一個“書架影院”。在這里,8米高的書架高聳入云,可容納約50000冊圖書。此外,另一個圖書館與另一個展覽空間相連接,五樓還有另一個畫廊和一個餐廳。
角川集團與所澤市均表示,博物館開放后,希望將這里打造成一個人人都想造訪、文化與自然共生的地方,同時也希望“角川文化博物館”能作為傳播日本動漫游戲文化魅力的總部。
北京白塔寺胡同美術館?
DnA事務所設計

在700年前,一座尼泊爾佛寺和它50米高的巨大白色寶塔在北京建成,從過去到現在,佛寺和白塔所帶來的宗教儀式與活動使建筑本身和諧地融入了周圍的胡同體系與四合院環境,并且最終成為了現代北京歷史文化的一部分。
白塔寺胡同美術館便位于北京市西城區白塔寺文化保護區內,鄰近魯迅博物館。在不同歷史時期,白塔寺胡同不斷產生新的建筑類型,逐漸融合構成了白塔寺現有的獨特系統。胡同美術館也是這個“系統”的再生計劃中的一部分:原建筑功能以居住為主,改造后將在胡同街區里植入公共功能,包括公共展廳和駐留藝術工作室等,為白塔寺帶來新的社區空間和文化交流。
根據胡同保護規定,在保留原建筑主要結構的基礎上,將其劃分為南側藝術家生活區和北側公共展區兩個部分:在南側起居部分,以置入功能盒子的方式,形成一層的書房、餐廚沙龍空間和二層的臥室,滿足居住的需求;北側是開放的公共展廳,樓板打通,結合二層工作室空間高度起落,提供胡同街區里難得的大尺度室內空間。建筑布局根據場地肌理和環境,結合胡同路徑和鄰居家的大樹,分別在東北角和西南角植入兩個角院,提供室內采光同時重新引入“院”的概念。室內空間,保留大面墻面的完整性,以部分樓板角落倒圓角切開的動作留出邊角縫隙,使光線滲入,地面處理與之呼應,成為豎向拉伸的自然角落。庭院與天窗的弧線,構成建筑室內外的連貫空間。
這種片段式的弧形語言以及光影效果一起,共同建構了空間里的白塔印象:白塔寺是這個街區的主導體量元素,然而受胡同尺度以及方向的影響,在這個胡同片區中行走時,白塔寺的呈現是時隱時現、斷斷續續的,帶來碎片化的記憶和印象。帶有植物棚架的屋頂花園,不僅是室內空間格局調整的延伸,更提供了胡同里難得的大面積屋頂活動平臺以及豁然開朗的視野,回歸到胡同生機勃勃的生活氛圍,也將給胡同社區生活帶來新的可能性。
博伊曼斯·范·伯寧恩博物館
公共藝術倉庫?
MVRDV設計

2020年9月,坐落于荷蘭鹿特丹博物館公園的博伊曼斯·范·伯寧恩(Depot Boijmans Van Beuningen)博物館公共藝術部分竣工,巨大的倉庫將存放館藏的151000件藝術品,并將全部對公眾開放,而它也會是第一個向公眾開放的藝術倉庫,以提供一種新型的博物館體驗。“這樣一來,大家可以共享通常被隱藏起來的事物。”MVRDV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建筑師Winy Maas這樣說。
該倉庫高為39.5米,盡管建筑的體量看似不大,但建筑面積也有1.5萬平方米。充足的儲藏空間不僅容納了博物館杰出的藝術和設計類藏品,還包括若干展覽廳、一間餐廳和榮獲獎項的屋頂花園。向下收縮呈碗狀的建筑形體,在地面層保證了穿過博物館公園的通透視野與流暢路徑,還能夠有效減少對地下水緩沖區的影響。
建筑表皮的鏡面部分面積達6609平方米,由1664塊玻璃拼貼而成,可以反射周圍的各種環境:來往的行人、公園繁盛的綠樹、空中的流云和鹿特丹充滿活力的城市天際線。然而,反射使得建筑本身能夠完全“消融”在周圍的環境中,在激活周邊區域的同時,也和相鄰的建筑建立起緊密的關系。
中庭交錯跨越的樓梯,以及懸掛式的玻璃陳列箱成為內部空間的亮點,后者將用來展示由博物館策展人挑選的展品。游客將在建筑中見到后臺的一般活動:修復,運輸,維護和保存藝術品。獨特的公私合作,私人藏家可以在此建筑物內租用空間,可以得到博伊曼斯·范·伯寧恩博物館對于藏品維護的專業知識。
博物館館長Sjarel Ex認為:“這是一座具有實際功能的建筑,既可滿足藝術品的維護工作,又能滿足公眾的觀賞需求。我們相信,將館藏公開化,能夠充分展示博物館對藝術品的重視和保護,這將是讓所有鹿特丹人引以為傲并能親眼所見的盛舉,因為他們也是這些珍貴收藏的擁有者。”
景德鎮御窯博物館?
朱锫建筑事務所設計


景德鎮被譽為世界“瓷都”,生產和出口瓷器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2020年新建成的景德鎮御窯博物館前身便是留存在此的世界唯一皇家瓷廠——景德鎮御窯廠。它不僅是明清兩代御用瓷器的專職制造場所,也是中國唯一古御窯廠遺址、全國10處大遺址保護展示示范園區。
新的御窯博物館的靈感來源于景德鎮的窯和瓷。早在2017年,法國戛納未來建筑獎(The Architectural Review)就授予了景德鎮御窯博物館“最佳文化建筑”的榮譽,這是全球唯一表彰世界范圍內尚未建成但富于創意的優秀建筑設計作品的獎項。
在建設過程中,項目遇到了總重量為734噸的明清時期的窯址,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要求,必須將其遷往5公里外的場地進行保護。窯址共六塊,最重的窯址重達214噸,這也創下了世界最大規模窯址群體遷移的世界首個成功案例。
在設計上,博物館通過多個單體拱券的組合聚集,用最簡單又富有感染力的拱的形式,抽象出窯的形態,又吸取了中國瓷器圓潤、簡約的曲線造型,以謙遜姿態,半藏于地下,呈現在世人面前。
入窯一色,出窯萬千。為實現設計“拱體表面磚體的顏色、厚度、材質呈漸變趨勢”的要求,項目部通過調整不同的粉料和熟料配比,定制了190萬塊響磚、窯汗磚、基磚、青磚和灰磚,同時搜集到90萬塊老窯磚,并前后進行了11次樣板試驗,對各種窯磚的比例和位置反復調整,僅窯磚干掛和砌筑就累計使用了280萬塊窯磚。
相信在今后,景德鎮御窯博物館定將是景德鎮對話世界的一張新名片,成為復興千年古鎮、重塑世界瓷都的新地標。
巴黎證券交易所-皮諾收藏館?
安藤忠雄設計

2020年10月,84歲高齡的著名法國奢侈品集團創始人弗朗索瓦·皮諾宣布,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巴黎證券交易所經由日本建筑師安藤忠雄改建設計,搖身一變成為博物館,并將在2021年1月23日正式開館,成為重振巴黎文化魅力的新力量。

距離盧浮宮僅兩個街區的巴黎證券交易所是座古典圓頂建筑,其最早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1889年成為巴黎證券交易所。現任巴黎市政府希望重新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當代藝術博物館,于是出資2100萬歐元購買下該建筑,于2016年與皮諾達成租用協議,將這座新古典建筑改建成一座地標性的當代藝術私人博物館,用于展覽皮諾從1960年開始的私人收藏。據悉,展品約有5000多件,總價值約12.5億歐元。
那么一座富麗堂皇的歐洲古典建筑要如何與安藤忠雄的現代極簡風融合呢?
安藤忠雄表示,重建歷史建筑,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在古建筑中加入現代藝術元素,因為這里的一磚一石中飽含的悠久城市歷史記憶,而他希望創造出一座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建筑。
巴黎證券交易所建筑秉承傳統建筑的對稱性原則,位于其中心的圓形大廳充分體現著這一點。安藤忠雄改造方案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原建筑的圓形穹頂之下,置入了一個直徑為30米、高度為9米的圓筒形的混凝土結構,作為美術館展覽空間。
改建后的巴黎證券交易所的玻璃圓形透明穹頂引入自然元素,光、藍天、白云、雨,成為建筑的一部分,穹頂下有歷史感的壁畫,浮雕式襯飾顯示交易所的莊重氛圍,與中間圓柱水泥墻形成繁華與簡約的鮮明對比,讓古典建筑包圍著新設計元素。
除了保留玻璃和金屬圓頂建筑結構,改造項目還修復了19世紀的全景壁畫古跡,內部沿走廊設有大小展覽空間、形成新建的多功能環形藝術場域,以及可容納200多位觀眾的表演空間,讓博物館在展示藝術品的同時,也成為傳統與現代融合的成功范例。
?王超:
博物館需要被“設計”

河南博物院的觀展游客以“5G+VR”技術體驗洛陽龍門石窟景區盧舍那大佛。圖/ 視覺中國
“生活需要設計感”,不知從何時起,這句話被忙碌的現代人奉為了圭臬。設計感似真似幻,乍虛還實,它可以被感知,但似乎又教人摸不著。當你評價一樣事物有設計感時,便是從形式上感覺到了它的內容,或者說,你因為了解內容而瞬間理解了它的形式語言。
有別于日常的或者自然的狀態,設計感是一種“人為”的痕跡,而這種人為痕跡把形式和內容進行了相互轉化。或者說,它是高于一般人為痕跡的一種理念痕跡,也是人類理解的表現形式。故而,從為了吸引眼球的產品外包裝,到偏重實用性的日用品,再到本就具備藝術屬性的建筑物、園藝景觀,甚至是傳遞信息和文化價值的文本,我們身邊一切的一切,都因設計感而變得更有“價值”。
王超任職于國家文物局直屬單位多年,在他看來,文博場館同樣需要設計感,而這種設計感并非拘泥于場館建筑外觀和內部結構的新建、翻修,也應當覆蓋策展方案、布展策略、宣傳理念、講解形式、文創開發、教育活動等各個方面。只有被精心設計,那些被陳列、被收藏的“物”才會活過來,有血有肉地活過來——
科技發展給博物館帶去了什么?
科技對博物館的輔助很大,從直接傳播來說,早在2016年,首都博物館就在“王后·母親·女將——紀念殷墟婦好墓考古發掘四十周年展”使用了VR/AR設備提升傳播效果,VR不僅能展示展品和文物本體,還能“呈現”它所處的環境。
傳統博物館的展覽將展品放置于展柜空間中,展示的是博物館“賦予”展品的環境。而經過學術研究和專業制作,通過VR營造的虛擬空間,可以呈現這件展品在“原生環境”里的狀態。這個“原生狀態”是博物館藏品在被博物館發現之前,人們使用這件物品時的狀態。這種狀態一旦離開原生環境就會失去,VR技術可以盡可能復現出這個虛擬環境,而博物館則可通過這個技術向觀眾傳達傳統展覽方式難以表達的信息,等等。
不過,由于VR設備比較昂貴,只有少部分博物館,或者說有實力的博物館才能用得起,大部分小型或是基層的博物館都要考慮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所以VR還沒有在博物館廣泛應用。
除了VR,還有哪些科技“改造”了博物館和博物館的宣傳策略?
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談科技,信息網絡技術對博物館的影響非常大。
首先是服務對象的轉變。以前博物館受到地理條件的制約,只能服務于前來博物館參觀活動的觀眾,人們只有來到博物館才能獲取知識和信息。現在隨著新媒體時代的發展,博物館都開設了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大型博物館都有自己的微博、微信公眾號,甚至開通了快手、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的賬號,開始主動制作內容發布到社交媒體上,觀眾不用付出交通成本就可以看到博物館想要展示的內容。
其次,新媒體的介入對博物館工作的流程進行了重構。數字化的介入對博物館工作理念和思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推動了整個博物館數字化的水平。現在的博物館每時每刻都能看到信息網絡技術和數字化的身影。比如宣傳方面,早期博物館的宣傳只有宣傳欄、紙媒廣告這樣的模式,現在,可以通過攝影、攝像等方式制作博物館藏品、展覽或者教育活動的數字化信息,再通過社交媒體在互聯網上分享給大家,大大提升了效率。
博物館在選題和策展方面會受到互聯網影響嗎?會有怎樣的趨勢?
事實上,博物館的選題很少受互聯網技術的影響,選題與策展大致還是遵循比較傳統的方法。因為博物館和其他的機構不一樣,它既有科研屬性,又有教育功能,所以博物館不會單純地因為觀眾喜歡什么就辦什么展覽,而是要結合自身的條件、研究成果和觀眾喜好,綜合考量來舉辦展覽。
博物館的展覽實際上可以看作博物館學術研究的一種表現形式,所以互聯網在宣傳和設施設備方面可以影響博物館,但是對于博物館核心的東西影響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大。但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它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重寫博物館工作的底層邏輯,到了那個時候還會有新事物、新情況出現。
綜合來說,國內博物館的發展近年來有哪些新的趨勢?
首先是博物館的擴建、改建和新建。目前國內很多大型的博物館都在擴建或者新建,比如已經改擴建完畢的河南省博物館和貴州省博物館,還有正在建新館的上海博物館和陜西歷史博物館。
博物館的展覽大多被分為兩個類型:一種是博物館最重要的展覽,我們稱之為“基礎陳列”,也就是以博物館自己的藏品為主,展示博物館最本質、最優勢的內容。這樣的展期大概可以持續3年~5年,甚至更久。另外一種叫“臨時展覽”,是指博物館使用自己的藏品,或者借入其他博物館的藏品辦展。這類展一般規模比較小,展期比較短,通常在三個月到一年。
博物館的基本陳列很少有實質性的改動。但隨著各大博物館的改擴建,會促使博物館對自己基本陳列做迭代甚至徹底更新,也讓博物館更加重視自己的基礎工作。
其次是展覽的設施設備越來越現代化、越來越精致,藝術設計和空間設計都越來越合理化、人性化。博物館展覽所使用的展柜、恒溫恒濕設備、支具等等都在向專門化發展,都會根據博物館的需求量身定制,甚至會影響這些設備背后科學技術的發展。
其三,策展正逐漸向小型化選題、深入化陳設的方向發展。比如,2015年南京博物院舉辦了“溫·婉——中國古代女性文物大展”,它以女性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的傳統文化,選題非常獨特(見右)。選擇的文物也并不追求一級文物和珍貴文物,而是用比較平常的文物來講述生動的故事。我認為這個形式是近年博物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不是一味追求宏大敘事,也不再一味追求精品文物的展示,而是趨向于用心講好一個故事,用情感來打動人。

海獸葡萄鏡琺瑯漆鏤空黃銅金屬書簽,河南博物院
博物館文創開發風頭正盛,您覺得文創產品會對文物或是博物館的知名度有怎樣的影響?

馬門溪龍浮雕水杯北京自然博物館
雖然文創的概念是近幾年才火起來的,但事實上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博物館就一直在做文創,只不過那個時候叫博物館商品。很多博物館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做得很成功了,比如北京自然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和故宮等。

綢繡花蝶團扇 清

雁形銀帶鉤 西漢
一般人覺得,既然文創是一種商品,那我們肯定會更關心它的利潤,但事實上,博物館的重點并不在于盈利。對于博物館而言,文創是用市場化的資源配置來宣傳博物館文化的方式,因而比起利潤,博物館更看重的是文創的覆蓋面,以及它是否能把文物的有效信息傳遞給公眾。
當然,文創帶動了博物館的IP化發展,而對于博物館IP的宣傳和推廣而言,新媒體有著天然的傳播優勢,它讓博物館搭上了現代知識經濟的快車。很多博物館開始做吉祥物,找“文物代言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因為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注重知識產權了。
聯名款、咖啡廳、名人講座和直播也屬于宣傳IP的方式嗎?
聯名當然算,我現在穿的鞋就是李寧和敦煌研究院聯名的。博物館的咖啡廳已經不是新鮮事了,蘇州博物館在2005年就已經開了咖啡廳,這還不是博物館行業最早的嘗試,但在博物館開咖啡廳主要也是為了滿足現代觀眾的休息需要。
名人講座也是博物館普遍采用的一種宣傳方式,它屬于博物館教育活動的一種,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很多博物館開始嘗試用直播的形式來舉辦講座。

李寧官方微博
網絡直播是現在流行的宣傳方式,博物館重視利用最新形態的宣傳手段是好事,可我發現博物館直播還存在一些問題。直播與視頻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它可以即時與觀眾互動,但博物館直播普遍互動性比較低,一方面是因為博物館直播中內容專業性較強,趣味性不夠高;一方面是受網絡直播平臺受眾群體的條件限制,直播的收看者沒法立刻消化直播內容進行反饋和互動。這可能是博物館想要在直播上做出效果時需要注意的問題。
博物館未來會在社會中扮演什么角色?
實際上學術界對此也有爭論,不同的學者、不同學派有不同的意見。我個人認為,博物館在將來的社會中會行使知識中心的職能,其邊界可能會超出“館”這個概念本身,每個博物館都會成為自己藏品涉及領域知識的載體。
博物館的核心是它的收藏,如果把博物館信息化、去結構化,成為一個“知識云”館,它將能以“云”的形態為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知識服務。
在知識云理念的影響下,博物館會形成獨具特色的知識體系和知識結構。未來我們去博物館參觀,甚至是通過虛擬世界訪問博物館,將不僅僅是去看展覽,還能通過各種方式學習到博物館知識庫里的其他知識。
請您展望一下博物館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個人認為有四點。
第一,省級博物館會越來越注重體現其所在省份的區域歷史和文化特色。以前我們的博物館對觀眾進行的是中國通史的教育,在博物館里面看到的內容都大同小異,現在隨著博物館的發展,省級博物館也都逐漸建立起了自己的“個性”,講述本省的歷史和文化,把講述中華文明宏觀歷史的使命賦予了國家博物館。
第二,博物館的類型越來越豐富。傳統博物館可以分為歷史文化類、自然科技類、革命紀念類和綜合類等,未來很有可能出現融合發展的趨勢,以一個母題為出發點,融合歷史、文化和自然等多方面內容。
第三,專題類的博物館會越來越多,內容越來越垂直。這當中,非國有博物館會發揮重要作用。
第四,基層的博物館會向文化綜合中心的方向發展。比如縣級、地市級博物館,收藏并不是它們的強項,所以可以選擇發揮自己的教育功能,通過舉辦一些教育活動和講座,以綜合性功能和“接地氣”來發展和傳播博物館的文化。
?張姍姍:
“科技+文創”是博物館發展的新方向
個人簡介

張姍姍
張姍姍,陜西西安人,入職文博系統10年,任職于陜西歷史博物館信息資料部,“漢唐網”微博編輯,連續三年獲得“全國十強文博新媒體”稱號,連續六年獲得陜西省政務微博“最有影響力獎”。
參與編輯書籍《陜西博物館叢書》《陜西古塔全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陜西卷》。出版個人作品《漢唐詞箋》。在十年內,探訪了長安各類遺址,從唐詩角度逛長安城,對長安有自己的見解。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自2010年開始,張姍姍負責管理文博系統新媒體賬號“漢唐網”微博已經有十年了。“陜西是中國歷史文化圣地,這一方厚土孕育了周秦漢唐文明,鑄就了中華歷史的璀璨篇章。” 從一開始,漢唐網微博的宗旨就是以傳承中華文明為使命,而漢唐網的名字也來源于此。
本著對文物和考古事業的熱愛,她加入了文博系統,“像是進入了霍格沃茨魔法學院,在這里學習了很多國家寶藏的‘魔法。”展廳里每一件文物都有特別的故事,本就很喜歡古詩詞的張姍姍恍惚間又像是回到了千百年前的時光,有盛唐的璀璨和精致,也有邊塞的雄渾與蒼涼。雖然這些詩詞和文物與她有著巨大的“時差”,但接觸起來依然覺得如沐春風,沁人心脾。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大眾對文化的需求與日俱增,而毫無疑問的是,博物館在社會中扮演著闡釋者的角色,向一代又一代人解答“我是誰”“從哪兒來”這兩大哲思。

鑲金獸首瑪瑙杯
“一個人、一個民族,找到自己的根脈才不會迷失方向,才會有文化自信,文化才可以出海,影響更多的人對中華文化的喜愛。所以我覺得博物館的未來不能拘泥于文物,今后在展覽上可以多辦一些貼近民眾日常生活的主題,讓大家在衣食住行中找到自己生活日常的發展脈絡。像各種工業發展的記憶、玻璃陶瓷等工藝的制作流程也都可以做成專業細分類型的博物館,展覽的感官表現形式也可調動視覺、聽覺、味覺、嗅覺等各個方面來做延展,使公眾更有興趣。”
秉持這一理念,張姍姍在陜西歷史博物館及漢唐網的工作中亦是如此踐行。作為中國第一座大型現代化國家級博物館,陜西歷史博物館館藏文物171795萬件(組),其中,一級文物762件(組),國寶級文物18件(組),其中鑲金獸首瑪瑙杯等12件為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通過科技賦能、文創引流,這座“華夏寶庫”正運用現代化的技術與理念,為公眾與博物館的互動帶去更多新穎有料的干貨。
近年來,陜西歷史博物館在科技“裝備”的運用上,有哪些好的實踐?

受訪者提供
最個性的科技裝備應該是我們的智能機器人“陜小博”。它最開始是為實現文物和信息資源的科學管理、傳播和利用,更好地讓文物“活”起來,陜西歷史博物館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梳理出來一套具備我館特色的觀眾行為分析模塊,并在此基礎上與多家第三方機構合作,共同參與研發出的智能機器人。
“陜小博”小名“婉兒”,是2019年9月開始上線運行的,很受小朋友們的歡迎。第一期的時候僅開放“調查問卷”的功能,為陜西數字博物館移動館和文物數字資產系統提供觀眾數據共享服務,幫助收集到“調查問卷”63510份、游客對話、問題建議和意見8395條。除此之外該系統還具備自動生成的觀眾行為數據、用戶畫像、熱點展品及用戶評論互動等功能,為更深入地了解游客參觀需求,收集對博物館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以機器人視角采集到的游客數據,為博物館未來在管理、參觀、學術研究、文化遺產宣傳、展陳設計、細節服務等各方面,制定長遠性的規劃時,提供參考依據。
數字博物館及陜西數字博物館實體體驗館也是在現代科技的支持下誕生的。我們在這方面起步較早,2011年著手實施數字博物館工程,到了2012年8月就已經上線了。運行以來,陜西數字博物館開設虛擬現實館、數字專題展等5大主體特色欄目,設立“文物故事”“交流與論壇”等多個輔助欄目,在全國眾多數字博物館中的網頁制作水平和數據庫完善度均首屈一指。
后來,在數字博物館的基礎上又衍生出了陜西數字博物館實體體驗館,這就是科技發展的神奇之處。陜西數字博物館實體體驗館在2016年2月建成,是在全省實體博物館優勢資源整合下改變博物館展覽形式和傳播手段的創新探索。可以通過數字影像技術感受全省一級博物館的虛擬現實,體驗省內各大博物館近期臨時展覽,與全省上千件精美珍貴文物通過新技術進行互動,還可享受陜西文物知識地圖帶來的電子饕餮,閱讀來自全省博物館出版物紙質圖書帶來的知識。
2017年5月,新的宣傳模式“陜西文物之聲網絡電臺”上線,這在全國尚屬首例。文物之聲網絡電臺是以語音、文字、圖片等多媒體形式,結合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手機微信公眾平臺等手段,匯聚管理與共享服務及融合媒體互動應用于一體,為網絡用戶提供支持多終端播放的語音節目和其他服務,支持通過微信、客戶端等參與節目互動,從而打造內容豐富、多媒介互聯互通并融合文物電臺、微信互動、APP應用和社會服務于一體的全媒體綜合應用服務平臺,自上線開播以來累計聽眾突破50萬人次,發布音頻數480條,累計收藏8614人次。
擁有VR體驗區的陜西數字博物館移動館在2018年上線,進入虛擬現實館的著名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等呈現在眼前,點擊陜西行政地圖所轄區內博物館便可以通過虛擬三維技術觀看。陜西數字博物館借助現代科技,使網友在互聯網上便能對博物館進行全面瀏覽,展出文物不僅有二維圖片還能360度觀賞。根據陜西數字博物館實體體驗館場地結合具體展示設備特點,還將唐18陵及陪葬墓出土的精品壁畫等文物,利用高清掃描和其他科技手段搭建唐墓壁畫特展展示軟件平臺,網友還可選擇感興趣的數字專題展進行觀賞,數字專題展以年月時間為排序,展示方式以二維圖片為主,選題很接近生活,如羊展、二十四節氣展等。陜西數字博物館“臨展與交流展”展現方式是以博物館為主體,展示其在世界各地所進行的臨展與交流展,點擊世界地圖中所標明的臨展地點信息便可呈現。“臨展與交流展”“唐墓壁畫高清數字精品展”已成為特色并得到網友一致好評。
截至目前,陜西數字博物館上線虛擬現實館共142座,其中2018年新上線3座,分別是梁代村芮國遺址博物館、大明宮國家遺址博物館、西安音樂學院博物館;數字專題展共100個、其中2018年制作上線20個,臨時展與交流展共96個、其中2018年制作上線13個,精品文物鑒賞欄目上線二維文物232件、三維文物46件;講壇與講解上傳文博講壇、歷博講壇、文博類培訓等88個講座視頻和31個省份博物館的講解音頻。
互聯網是如何改變博物館的宣傳方式和方向的?
2020年的新冠疫情,讓博物館也有了新的思考,開展了許多云展覽、云直播、數字博物館等內容,更加重視線上的力量。互聯網的出現,讓很多偏遠地區的人們連上網絡就可以無差別聆聽到各領域學者的講座,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需求。后續我們應該開發一些針對特定人群的講座,適合中小學生的一些講座,大學生的講座,文博從業者講座,考古學知識的普及方面還得下功夫,減少公眾對考古學的誤解。
在博物館文創方面,您有哪些心得體會?
近年來博物館文創發展勢頭很強,文創產品從美妝、文具、日用品等產品,進入了盲盒、解謎書等新奇特產品領域,“陜歷博”2019年的皇后玉璽交通卡這種古今科技結合的生活產品很受歡迎,2020年陜西歷史博物館與金士頓合作開發的鎏金竹節銅熏爐閃存盤也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所以“博物館+科技”本身就是一個文創產品開發的方向,隨著冬奧會的臨近,冰雪運動熱度急速上升,把博物館和運動健身結合起來,也是一個很好的走進大眾生活的途徑。
(本文僅代表受訪人個人觀點)

陜西歷史博物館2020 年底推出了盲盒,其靈感來源于館藏的各種青銅器,共八款。從左至右依次為: 鸮、饕餮、觥大、觥二、冷鸮、犧尊、鸮尊和鳳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