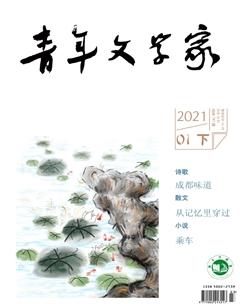在自然中孕生的愛(ài)
摘? 要:《額爾古納河右岸》是遲子建用百年的歷史變遷記錄一個(gè)民族的變化的小說(shuō)。通過(guò)小說(shuō)我們深刻的感受這個(gè)民族對(duì)自然的敬畏,他們?cè)谧匀坏暮椭C相處中走進(jìn)現(xiàn)代文明社會(huì),同時(shí)看到作者在表現(xiàn)鄂溫克族人的百年歷程與生命體驗(yàn)中, 帶給人們的仍是對(duì)生活與生命的清醇滋味,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這個(gè)民族的深深眷戀之情。遲子建是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編制歷史的舞臺(tái),小說(shuō)中充滿著對(duì)自然,對(duì)國(guó)家對(duì)民族,對(duì)親人的深深愛(ài)戀。
關(guān)鍵詞:中國(guó)長(zhǎng)篇小說(shuō);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
作者簡(jiǎn)介:黃艷(1982.9-),女,仫佬族,廣西宜州市人,本科,講師,研究方向: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
[中圖分類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21)-03-0-02
遲子建的文字,凄美憂郁、婉約清澈,字里行間流露出的天真爛漫的故事。她時(shí)刻關(guān)注底層民眾生存狀態(tài)。如她自己所說(shuō)“我希望能夠從一些簡(jiǎn)單的事物中看出深刻來(lái),同時(shí)又能夠把一些貌似深刻的事物給看破,這樣的話,無(wú)論是生活還是文學(xué),我都能夠保持一股率真之氣、自由之氣。”[1]再次讀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讀到了文字中對(duì)這個(gè)民族,對(duì)親人,對(duì)自然的深情感悟。
一、對(duì)古老民族集體大愛(ài)的深情回望
遲子建認(rèn)為“真正的歷史在民間,編織歷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yàn)橹挥袕乃麄兩砩希拍荏w現(xiàn)最日常的生活圖景,而歷史是由無(wú)數(shù)的日常生活畫(huà)面連綴而成的。”[2]《額爾古納河右岸》是一部具有深厚歷史意識(shí)的小說(shuō),雖然只有二十多萬(wàn)字,小說(shuō)以描寫(xiě)東北鄂溫克民族中的一個(gè)小族群的生活變遷來(lái)記錄這個(gè)民族的成長(zhǎng)故事、生存現(xiàn)狀及百年滄桑。
在鄂溫克族人的流傳中,這個(gè)民族發(fā)源于貝加爾湖畔,祖先居住的這個(gè)地方是一個(gè)四季如春的美麗世界。因?yàn)槎碥姷娜肭郑疟黄劝徇w至現(xiàn)在生存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在搬遷的過(guò)程中,一些氏族在歲月的侵襲中離散了,這使得本來(lái)就人數(shù)不多的民族人口更加稀薄。但是來(lái)到右岸后,這個(gè)民族依然堅(jiān)韌的快樂(lè)生活。這個(gè)民族的生活很簡(jiǎn)單,他們?cè)趶V袤的山林里以放養(yǎng)馴鹿和狩獵為生,跟著馴鹿尋食的蹤跡而遷徙,繁衍生息。他們住在一種叫“希楞柱”的用松木搭建的簡(jiǎn)易帳篷中,方便隨時(shí)遷徙,他們有專門(mén)的存儲(chǔ)食物的倉(cāng)庫(kù)“靠老寶”,像鳥(niǎo)兒的巢一樣搭建在樹(shù)上,如果族人過(guò)世了,則風(fēng)葬在大樹(shù)上,讓靈魂隨著風(fēng)回歸到自然中。他們穿的是獸皮,吃的是這片山林提供給他們的各種動(dòng)植物,他們順應(yīng)自然而生存,把握自然的規(guī)律,與自然和諧共生,他們對(duì)這片山林充滿著崇敬和深情,他們相信每一個(gè)生物都是有靈性的,草木能唱歌,馴鹿通人性,森林會(huì)說(shuō)話。他們虔誠(chéng)地遵從著最古老原始的自然規(guī)則,將所擁有的一點(diǎn)點(diǎn)滴滴都視為大自然的恩賜,盡自己所能去適應(yīng)自然,而非改變自然。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鄂溫克人感謝自然的給予的隨遇而安的的生活理念,群居生活的集體思想。林中遷徙,異常艱難。在這里我們清楚地看到一幅個(gè)人和群體和諧相處的畫(huà)面,自然而然展現(xiàn)出的群體關(guān)愛(ài)。這個(gè)畫(huà)面使得這個(gè)民族這茫茫林海中得以生存、延續(xù)和發(fā)展。
二、用愛(ài)的力量體現(xiàn)人性至美
王安憶說(shuō):“小說(shuō)是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藝術(shù),所以小說(shuō)必須在現(xiàn)實(shí)中找尋它的審美價(jià)值,也就是生活的形式。”[3]遲子建是一個(gè)清醒而質(zhì)樸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者,她常以詩(shī)性的目光來(lái)發(fā)現(xiàn)和預(yù)設(shè)生活中的人性之美,又在想象中消融其中不連貫的部分,使其進(jìn)入妖嬈嫵媚的藝術(shù)世界。遲子建不是被動(dòng)真實(shí)地反應(yīng)現(xiàn)實(shí)生活,而是將這個(gè)世界打碎,運(yùn)用想象與虛構(gòu),按著人性的要求來(lái)重新構(gòu)建文學(xué)的鄉(xiāng)土世界,將自己的個(gè)體生命融入作品中,把現(xiàn)實(shí)中的真實(shí)與精神里的真實(shí)相結(jié)合,《額爾古納河右岸》也不例外。
(一)對(duì)自然的敬愛(ài)
在這部小說(shuō)里,鄂溫克民族生活在山林里,他們?cè)谙硎艽笞匀坏亩髻n的同時(shí)也嘗盡了艱辛。他們生活比較簡(jiǎn)單、困苦,無(wú)法左右自己的命運(yùn),經(jīng)常要面對(duì)各種不期而遇的天災(zāi)人禍,但是他們總以平和的心態(tài)來(lái)對(duì)待命運(yùn),對(duì)生存的這片山林充滿著深情和敬重。小說(shuō)開(kāi)篇寫(xiě)到的“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看老了。”[4](P3)在一開(kāi)始,作者就把人和自然的命運(yùn)緊緊相連了。姐姐被凍死;父親林克在森林中遭到雷電襲擊而死;拉吉達(dá)的家人都被“黃病”奪去了生命;拉吉達(dá)在大雪天里尋找馴鹿被凍死;妮浩的女兒交庫(kù)托坎被馬蜂蟄死;瓦羅加死于熊之手;依蓮娜被河水沖走等等,這些死亡都是自然和自然中的生物造成的,可是他們卻沒(méi)有因此而對(duì)自然產(chǎn)生和馴鹿產(chǎn)生恨意和不滿,而是一如既往地愛(ài)著這片森林和馴鹿,他們?nèi)缡钦f(shuō)“雖然馴鹿曾經(jīng)帶走了我的親人,但是我卻還是愛(ài)它。” [4](P18)他們以動(dòng)植物的名稱為孩子命名,同時(shí)還像保護(hù)自己的孩子一樣保護(hù)馴鹿和一些小動(dòng)物,在游牧的時(shí)候,總會(huì)把住過(guò)的地方清理干凈,不留下“疤痕”,他們也不會(huì)坎燒鮮活的樹(shù)木,金得自殺時(shí)都不舍得在活的樹(shù)上吊死,因?yàn)樯屏嫉乃辉敢庖豢没钪臉?shù)和他被一起火葬,他們與動(dòng)物為友,與天地為伴,他們真心的對(duì)待森林中的一草一木,就如主人公說(shuō)的,他們和馴鹿“從來(lái)都是親吻著森林的”。[4](P247)火在這個(gè)民族也是被生命化的,它的燃燒是一朵盛開(kāi)的花,它在這個(gè)民族是溫暖的象征。而火最終也帶走了這個(gè)民族最后一個(gè)薩滿。這也是小說(shuō)中最為感人的一幕:為了撲滅森林的大火,年邁妮浩拖著沉重的步子跳起了神舞,她越跳越慢,最后慢慢地倒了下去,此時(shí),大雨也傾盆而下。她用自己的生命中最后一支神舞,換來(lái)了生機(jī)和族人的繁衍。依蓮娜是第一個(gè)鄂溫克族大學(xué)生,靠自己的能力在城市里成為畫(huà)家時(shí),她就創(chuàng)作了妮浩薩滿祈雨圖,用行動(dòng)來(lái)表達(dá)對(duì)自然的熱愛(ài)。
鄂溫克人順應(yīng)自然規(guī)律,像自然界中的動(dòng)植物一樣,從容應(yīng)對(duì)萬(wàn)事萬(wàn)物的新陳更替。他們認(rèn)識(shí)到有出生必有死亡,有喜悅必有憂愁,有婚禮必有葬禮。書(shū)中寫(xiě)到列娜死的時(shí)候不留刻意雕琢的痕跡,只是淡淡地說(shuō)了一句:“列娜已經(jīng)和天上的小鳥(niǎo)在一起了。” [4](P32) 那么的悲傷卻又是那么的豁達(dá)自然,仿佛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悄然變化,賦予著生命的跳動(dòng)感。他們其實(shí)就是這片大地山林的化身,與自然融為一體。
(二)人性真情回歸
遲子建多是對(duì)畸異人物、弱勢(shì)群體的關(guān)懷,來(lái)表現(xiàn)出他們?nèi)诵缘恼媲椤H缧≌f(shuō)中的“我”最喜愛(ài)的兒孫是安道爾和安草兒,安道爾小時(shí)候被果格力打到,卻沒(méi)有哭,而是開(kāi)心地躺著欣賞天上的云彩,把果格力的拳頭當(dāng)做瘙癢癢。他想給馴鹿在吃到鹽的同時(shí)又能喝水而把鹽撒進(jìn)河里,鹽被河水稀釋了,他傷心的認(rèn)為河水是個(gè)騙子,而從此再也不吃水里的食物,認(rèn)為河里的食物都是魔鬼。他被瓦霞設(shè)計(jì)與其發(fā)生了關(guān)系,使得瓦霞懷孕導(dǎo)致他被迫取瓦霞為妻,當(dāng)一切事情水落石出后,他卻沒(méi)有聽(tīng)母親的話與瓦霞離婚,原因是他不愿意瓦霞再去傷害別人。安草兒愚癡是遺傳了父親的,他為拉吉米插在小達(dá)西墳上的吹奏的樂(lè)器木庫(kù)蓮得到雨水的滋潤(rùn)而開(kāi)心,認(rèn)定它會(huì)生長(zhǎng)出一曲會(huì)唱歌的小鳥(niǎo)來(lái),他還大清早的為電影里的人煮鹿奶茶。他的天真給人們帶來(lái)了歡樂(lè)。
他們父子都是愚癡的人,如果他們生活在今天的社會(huì)中,一定無(wú)法適應(yīng)社會(huì)的冷漠和欺詐,無(wú)法生存與人際關(guān)系復(fù)雜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中,但是在山林中,他們卻能應(yīng)付自如,快樂(lè)坦然的與大自然依依而生。他們雖然愚癡,但是他們卻比任何人都真誠(chéng)、善良,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說(shuō),他們正是代表著這個(gè)民族的精神,守護(hù)山林、守護(hù)馴鹿、熱愛(ài)自然中的一切生物,真誠(chéng)待人,這些都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中所缺乏的。遲子建借助“我”的口來(lái)呼吁我們應(yīng)該回歸真誠(chéng)、善良的本真人性中。
三、自然孕生的溫暖真情
雖說(shuō)小說(shuō)應(yīng)該對(duì)于生活具有批評(píng)性和超越性,但是小說(shuō)更應(yīng)該是美的、溫暖的、能感動(dòng)人心的。我們看到遲子建的小說(shuō)中的世界是溫暖的,無(wú)論生活多么艱難,無(wú)論人生面臨怎樣的缺陷,她總能給我們展現(xiàn)心里中最溫潤(rùn)動(dòng)人的情感,在《額爾古納河右岸》里她對(duì)于愛(ài)情、友情、親情乃至動(dòng)植物與人之情的抒寫(xiě)成為小說(shuō)中最感人的篇章。
小說(shuō)中對(duì)親情的描寫(xiě)是浸透人心的。拉吉米對(duì)毫無(wú)血緣關(guān)系的養(yǎng)女馬伊堪的愛(ài),馬伊堪對(duì)養(yǎng)父拉吉米守候;其中最動(dòng)人的是耶爾尼斯涅對(duì)母親妮浩的愛(ài),為救母親可以替母親去死;妮浩對(duì)死去孩子所唱的每一首神歌中體現(xiàn)出她對(duì)孩子的愛(ài);依芙琳向善后為瑪克辛姆治爛瘡的舉動(dòng)以及“我”對(duì)別人的體貼和關(guān)心、在最后要搬離山上時(shí)所有人的不舍紛紛給我留下的紀(jì)念物,這些親情都在生活中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流淌著溫暖著人心。小說(shuō)中的愛(ài)情更是美麗感人,父親及伯父尼都薩滿對(duì)母親達(dá)瑪拉執(zhí)著的愛(ài),母親死后為了讓母親平安渡過(guò)“血河”到達(dá)幸福世界,寧愿自己融化在“血河”中,以此表示出他對(duì)達(dá)瑪拉母親深深的愛(ài);瓦羅加對(duì)我的愛(ài):“我是山,你是水。山能生水,水能養(yǎng)山,山水相連,天地永存。”[4](P170) “我”對(duì)拉吉達(dá)和瓦羅加的愛(ài)則是:“拉吉達(dá)是一棵挺拔的大樹(shù),瓦羅加是大樹(shù)上溫暖的鳥(niǎo)巢,他們都是我的愛(ài)。”[4](P142)就這樣簡(jiǎn)簡(jiǎn)單單的一句話,體現(xiàn)了濃濃的深情;還有小說(shuō)里羅林斯基對(duì)列娜的愛(ài);伊萬(wàn)對(duì)娜杰什卡的愛(ài);魯尼對(duì)妮浩疼愛(ài)等等,這些情感淺淺深深的不同人有不同的表達(dá),但是都是真摯的悄然的感動(dòng)著人心。除了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動(dòng)物和人之間的情感也是讓人感動(dòng)的,父親林克的獵犬伊蘭對(duì)主人的忠誠(chéng),父親死后想給父親殉葬,母親留下它之后,它再也不吃肉,以此來(lái)消耗身體的熱量,最終陪伴到母親死去。老達(dá)西的獵鷹奧木列為老達(dá)西獵食,和老達(dá)西一起與狼奮戰(zhàn)為老達(dá)西報(bào)仇,這些動(dòng)物與人之間是一種朋友關(guān)系,對(duì)人絕對(duì)的忠誠(chéng)。更可貴的是薩滿妮浩的舍己為人,一次次地放棄自己的孩子來(lái)救回族人甚至是與我們生命中毫不相關(guān)的人的性命,貫穿了整部小說(shuō)的兩個(gè)薩滿,她們的經(jīng)歷都讓人感動(dòng)不已,她們的命運(yùn)都是悲壯的。無(wú)論在任何時(shí)候,這種舍小我為大我的行為都會(huì)觸動(dòng)著我們的心弦。這些故事是對(duì)大愛(ài)無(wú)疆的闡述,是叩擊我們心門(mén)的震顫。
遲子建正是通過(guò)這緩緩的訴說(shuō),來(lái)體現(xiàn)她對(duì)于自然和這個(gè)民族的愛(ài)。我們的生活需要這樣的民族精神,她以默默溫情的愛(ài),展現(xiàn)了這個(gè)民族的堅(jiān)強(qiáng)、智慧以及對(duì)生活充滿著希望的不屈精神。在今天的社會(huì)生活我們遺失了很多東西,我們需要鄂溫克族這樣的生存哲學(xué),就是鄂溫克人的生存姿態(tài),一種簡(jiǎn)單卻偉大的哲學(xué)。我們一直在提倡建立和諧社會(huì)。然而,社會(huì)的和諧是依賴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鄂溫克人雖然以山林為生,順應(yīng)自然規(guī)律生活在山林中,小心翼翼地愛(ài)護(hù)著這片山林。今天我們無(wú)限制地掠奪自然,必會(huì)造成資源的枯竭。這不僅實(shí)現(xiàn)不了發(fā)展的目標(biāo),還會(huì)使地球變得不再適合人類生存。人與人、人與社會(huì)的和諧也就無(wú)從談起。我們應(yīng)重新審視人與自然關(guān)系之后作出的理性選擇,這是鄂溫克人帶給我們的啟示。
注釋:
[1]遲子建.寒冷的高緯度——我的夢(mèng)開(kāi)始的地方[J].小說(shuō)評(píng)論,2002(02).
[2]遲子建,胡殷紅.人類文明進(jìn)程的尷尬、悲哀與無(wú)奈——與遲子建談長(zhǎng)篇新作《額爾古納河右岸》[J].文藝廣角,2006(02).
[3]王安憶.生活的形式[J].上海文學(xué),1995(05).
[4]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M].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tuán)/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