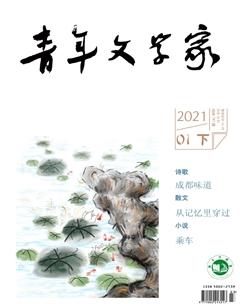國產動畫電影中的傳統文化元素改編與人物塑造
摘? 要:從《大圣歸來》《白蛇:緣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到《姜子牙》,從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到性格迥異的神話人物,傳統文化元素在國產動畫電影中屢見不鮮。互融互通,國產動畫電影以傳統文化為基石,在情節編排和人物形象改造上銳意創新,其對于傳統文化元素的改編更是打通了傳統和現實的壁壘,實現了寄情懷于歷史,展新貌于時代。
關鍵詞:國產動畫電影;改編;傳統文化
作者簡介:張應翔(1995.11-),漢族,福建南平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視傳播。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3--02
傳統文化有其成熟的內容體系架構,各類神話故事、民間傳說其中的故事背景、人物形象等都特征各異。不僅有其自帶的時代代表性和典型性,且都有本源可循,為電影改編提供了詳實的文本資料。近年來,國產動畫電影中的傳統文化元素特點鮮明且富有創新,而這其中《哪吒之魔童降世》與《姜子牙》兩部影片在對傳統文化元素的改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編排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熱議,關于兩部電影的評價也褒貶不一。
1.故事改編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簡稱《哪吒》)的超高票房無疑為國產動畫電影注入了一劑強心劑,也讓國產動畫強勢回歸大眾視野。同在國慶檔引起熱議的影片《姜子牙》一樣,二者在人物形象設計和故事架構上都與傳統文化元素改編有著密切的關聯,對傳統文化元素不同程度的改寫成為國產動畫電影的“態度標簽”。在故事內容上,影片《哪吒》在保留了哪吒這一神話形象基本的身世來源, 水淹陳塘關這一主要背景外,對一種主要人物的命運走向做了大幅度的改編。而這其中頂著兩只大黑眼圈,一口齙牙,相貌“丑陋”的哪吒則是導演為了突出影片主旨“打破偏見”最直觀的視覺化體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故事內核將哪吒的個人成長作為主線,將因被迫承受不公命運遭遇時乖張頑劣的哪吒,和堅守品性勇于和命運作斗爭堅毅有擔當的哪吒刻畫的棱角分明。電影《哪吒》中敖丙和哪吒生為靈魔兩珠的天定命運無疑是影片對于傳統神話中的故事原型做出的最顛覆性的改變,生來就是魔丸的哪吒在被世人當作怪物遭到唾棄,靈珠轉世的敖丙枉背家族仇恨成為了復仇的棋子。影片圍繞二人的身世展開,以旁人的成見和內心的堅守為內核,通過哪吒由最初的人人畏遠到后來的眾人敬仰這一過程中的心路歷程、成長經歷呈現出來。對父母言:“我的命我自己扛”,對朋友言:“你是誰只有你自己說了才算”哪吒勇敢頑強不服輸的精神有力地展現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影片主旨。不僅如此,輕松搞笑的情節和臺詞也是《哪吒》受到觀眾喜愛的重要原因之一。小哪吒朗朗上口的打油詩,一口四川口音,憨中帶著迷糊的太乙真人和哪吒的斗智斗勇,花樣整蠱村里的其他小孩,逗趣可愛又膽小的青銅器結界獸,都將哪吒“混世小魔王”的形象襯托的活靈活現。
《姜子牙》則以姜子牙同狐妖惡斗并“一戰封神”為背景,講述了姜子牙因在審判臺上救下了狐妖體內的人類元神而遭受到師尊的懲罰被困于北海之境,后在北海遇到小九并同她一起前往幽都山破除宿命瑣,轉世重生的故事。同《哪吒》對傳統動畫中對主要情節的保留改編不同,《姜子牙》中的主要人物小九是一個全新的人物,影片的主要情節圍繞著小九和姜子牙陪伴小九尋父展開,小九同妲己相生一體,一善一惡的宿命連接是影片的主要矛盾所在。從小缺乏家庭溫暖,一直被當成狐妖追殺的小九在姜子牙身上感受到了溫暖和陪伴。二人孤獨的相互理解和依賴成為了影片主要的情感線索,責任、友情、信念和善惡交織的現實為影片關于“蒼生”和“一人”的敘事線索埋下伏筆,也使得中年姜子牙面對現實困境的進退兩難,對個人情感和道義的堅守與掙扎,對權威的挑戰和初心的堅守的形象更具體可感。
2.人物形象
同有著極重的黑眼圈,笑起來占據整張臉一半的大嘴,滿口齙牙的幼兒時期的哪吒不同,解除封印后的哪吒紅發沖冠、俊朗邪魅,腳踩風火輪持槍而立,給了觀眾極大的視覺沖擊。電影中,幼小的哪吒代表著偏見,村民們對哪吒的厭惡源自對于魔珠的恐懼。但從穿著紅肚兜的小哪吒挨打后委屈的眼神以及從海夜叉手中救回小女孩后對她友好的回應可以看出,哪吒是一個內心善良的孩子。村民們的偏見讓哪吒不得不用暴力的方式同他們保持距離,以保護自己免受傷害。惡語是鋒利的刀,偏見是人心中看不見的墻,哪吒以大局為重,心胸寬廣用實際行動守護了陳塘關百姓們的安全是對偏見最好的回擊,使得哪吒勇敢堅強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影片中另一位主要人物靈珠轉世的敖丙在形象設計上則一襲白衣獨立,溫潤如玉。和哪吒的周身烈焰紅不同,敖丙的外觀同他龍族太子的身份相契合,藍眸藍發,氣質脫俗,同女性對與古風翩翩公子的審美期待相契合。敖丙生性善良溫和,同哪吒一樣重情重義,同樣孤單長大的二人惺惺相惜,把彼此當成最好的朋友。從小生活在父親和師傅控制下長大的他只知道一味地遵師命、聽父言,而在自己心中卻從未有過自我,這也是敖丙這一形象的悲情所在。本是要扮演救世靈珠救百姓們于水火,卻輕信了鼓動水淹陳塘關。雖對其的性格刻畫有著由善到惡再回歸本心的過程,但或許是受影片篇幅所限,對于其性格轉向的具體因果、內心活動并未做出具體的呈現。同哪吒堅守本心,努力戰勝偏見的具體可感對比,敖丙的人物性格塑造上就略顯單薄,讓其成為了類似情節推進作用的存在,削弱了角色自身的情感張力,稍顯遺憾。
和家喻戶曉的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的老者形象不同,影片《姜子牙》中的中年姜子牙剛正不阿,堅毅隱忍的形象無疑為影片增添了濃厚的現代氣息,冷酷寡言、能力超群正義勇敢的姜子牙是影片英雄形象的直觀體現。面對狐妖身世堅持斗爭的小九是影片中最具沖突色彩的存在,為了保護自己她不得不變得對外人帶刺和冷漠,但她的內心也不過是個渴望親情和向往平常人安穩生活的普通人。呆萌可愛的四不像不僅僅是影片中童趣可愛的存在,為救姜子牙強行變身最終灰飛煙滅的結局里是它的姜子牙難舍難分的患難之情。無辜送命的冤魂思鄉情切,威嚴冷漠城府極深的師尊,為彌補錯誤救出族人的九尾,《姜子牙》中人物設計無不體現著當代人的生存境遇,親情、責任、算計和晦暗,有著其獨特的現實隱喻。
中年姜子牙在同狐妖之戰大獲全勝后一戰封神,權力、地位、美譽一有具有,卻因救下小九之舉而被困罰北海孑然一身。被地位和榮譽所裹挾的姜子牙是當代青年人在職場生存困境的影射,是維護自身的利益以求升還是犧牲他人的利益以護己是每一個被生存壓力束縛的中年人、青年人都會面對的殘酷現實抉擇。姜子牙對道義和善意的堅守,對現實的不屈無疑是影片想要向觀眾傳遞的精神內核。但影片從傳統動畫中姜子牙輔佐周武王反商伐紂的故事背景中跳脫出來,主要著墨于描述姜子牙和小九之間的糾葛牽掛則給人以略顯單薄之感。同哪吒以親情和個人成長為紐帶,為父老鄉親犧牲以一己之力拯救陳塘關不同。姜子牙為小九一人舍棄蒼生的情節走向中二人的情感基礎僅僅從克服萬難一同殺敵上體現,失去了傳統動畫中狐妖與人神一族的對立,武王伐紂的歷史背景支撐,故事的背景和精神內核就不免顯得單薄,并且難以讓觀眾產生合乎情理的認同感。
3.結語
傳統文化元素憑借其既有的識別符號使得觀眾對于電影的共識處于大致相同的文化認知水平上,對于故事中的人物和情節具有一定的熟悉度,這就使得導演無需過多的著墨于交代人物關系和人物出場同情節的跳接性問題,從將更多的精力放置在提升影片的可看性和自圓內在邏輯的完整性。當前在國產動畫電影中,含有傳統文化元素的國產動畫電影表現相比其他類型的動畫影片普遍較為亮眼。一方面是作品中保留了對舊有角色的人物特點,如姜子牙被罰北海時的獨立垂釣,還是《哪吒》在對哪吒的外貌進行大幅度改創的同時保留了其風火輪、混天綾,火尖槍的戰斗型武器裝備,都無形中增添了觀眾對中年姜子牙和“丑萌”哪吒的角色認同感。另一方面包涵傳統文化元素的國產動畫電影在形式、情節、題材、人物等元素的創新程度上更為豐富,不論是以新導向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還是以歷史為根基傳經典重現傳統文化的價值魅力,傳統文化元素都為國產動畫電影提供了更深的文化內涵以及更寬闊的傳播視野,國產動畫電影中的傳統文化元素自帶的歷史感和厚重感驅動了觀眾對于傳統文化的情懷感和自豪感。最后,在既有觀眾基礎上,中華傳統文化在各年齡層的普及度和認知度上都較高,通過配合春節檔、暑期檔等“合家歡”的時期上映,邀請具有影響力的明星劇宣,一既符合現代化特征的角色和故事內容改等方式,刻板傳統文化元素影片對受眾吸引力不足的短板正逐漸改善。
國產動畫在運用傳統文化元素時,還須做到融會貫通。如果不能將各種元素充分融入劇情和影像,那就成了民族元素的拼貼,非但不能提升作品的文化品位,反而會適得其反,影響到敘事的進程和文化價值的發揮。[1]同其他類型影片因地域差異而產生的文化認同偏好不同,觀眾對于動畫電影的接受維度在偏重故事內容熟悉度,和可觀賞性要求的基礎上青睞于更具吸引力的內容,這也就對動畫電影的內容創作、情節合理性、故事節奏把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其中,對歷史性和虛構性都較強的內容,相比通過實地取景后期制作,特效妝容真人演繹,動畫電影在場景重現多元化和角色設計擬合度上可操作性更強,為呈現傳統文化中既有的宏大故事體系架構提供了更多的還原空間。但在對傳統文化元素的改編的動畫電影中,突兀、生硬的人物設計,情節改編不僅不能讓觀眾產生共鳴,還容易喪失傳統文化中豐滿的角色形象和歷史內涵,遺失內容原型在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和現代價值。綜上,《哪吒》和《姜子牙》等國產動畫電影的出現,在重塑經典人物的基礎上賦予了影片嶄新的文化價值和傳播價值,更好地提升了傳統文化元素在國產動畫電影中的原創性、文化性和傳播性。雖當下傳統文化元素在國產動畫電影中的藝術呈現和原創價值上仍舊存在內涵不足、節奏不佳,情節平淡等缺陷,但《哪吒》與《姜子牙》的嘗試和突破仍舊彰顯了國產動畫電影的文化價值與商業潛能,為開啟中國自己的國漫封神宇宙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參考文獻:
[1]張書端,馬楠楠.中國動畫電影民族性的表達困境及其進路[J].電影文學,2020(18):12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