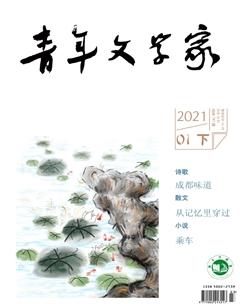對電影《英雄》中秦王形象的誤讀分析
史光恒
摘? 要:張藝謀執導的電影《英雄》可以作為國產電影中鮮有的誤讀案例,這種對影片的誤讀范圍頗為廣闊,幾乎涵蓋了全部的觀眾甚至影評人。而其主要表現是將秦王定義為正面人物,以及將影片中的秦王與真實歷史上的秦始皇一概而論。在本文的研究中,將針對該片是否在歌頌秦王以及影片中大量的誤讀現象進行詳細的分析,進而給予觀眾新的角度來審視影片。
關鍵詞:電影;《英雄》;誤讀;秦王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3--03
對于影片《英雄》中的誤解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認為影片對秦王呈現歌頌與褒義的情感表達;其次,認為該片呈現出的敘事牽強,邏輯上不合理;還有就是認為《英雄》是文本較為空洞的視覺展現,對于感官享受的追求較高,而其中的內在思想感情較為缺乏;綜上所述,由于觀眾難以有效地明確電影中表達的主題思想和風格特色,將其判定為純粹的商業電影。本文針對關于對觀眾對于秦王的誤讀這個問題展開詳細論述,而對于這個人物形象,觀眾所產生的普遍觀點多為秦王是整個故事中的最終獲勝者,或者其身上肩負國家興亡之使命,同樣與影片中其他主要人物暗合“英雄”這個敘事主題。然而實際上,秦王的人物形象并非是正面的,導演通過敘事和影像語言已然將秦王復雜的心理變化和性格特征表現在銀幕之上了,想要厘清對于秦王這一人物形象的誤讀,就必然要進行一系列的深入分析。
1、秦王的心理:恐懼之下的智慧
從影片伊始,對于秦王的性格和心理就有著細致入微的表現,譬如通過秦王之口來敘述多年以來為應對刺殺危機其所實施的極為嚴密的防范方法。因而,不難推斷秦王在影片中所展現出的智慧,其實并非意在展示其頭腦上的優勢,而是在營造秦王遭遇多次刺殺之后的心理,即對所有人都充滿著絕對的懷疑,尤其是在三年之前經歷了飛雪、殘劍的刺殺危機后,秦王的內心敏感程度則更加嚴重,總而言之,風聲鶴唳的環境造成秦王多疑的性格。這種性格特點在影片中的表現正是導演利用了視聽語言所營造出的氛圍,在景別上規避了中近景鏡頭,而是將距離拉遠,讓這個萬人之上的君王孤零零地置身于空蕩、寂靜的宮殿之中,身邊別無他人。樓閣殿宇的宏大氣勢與秦王一人的孤單和寂寞之間構成了極為強烈的對比,同時,在光線、色調上的使用加固著這種孤獨和寂寥之感,同時也表現著秦王的恐懼心理。
因而,在如充滿著壓力的恐懼和懷疑之下,秦王對于無名的到來當然無法呈現出放松、愜意的狀態,而是加重了心中的恐懼和懷疑,原因在于他無法清楚、確鑿地判斷出無名的真實動機,到底是因取了三位高手性命而單純領賞,還是另有所圖?繼而秦王自然會進行推斷,如若為了領賞,那么無名殺死一位高手即可,之所以要殺死三位高手,則一定與懸賞令上嘉獎勇士上殿步數的條款有關,即必須殺死三位高手,無名才能將與秦王的距離縮短到十步以內。正因如此,當無名告知秦王自己的招式名稱為“十步一殺”時,秦王得以確信自己的生命再次遭受威脅,雖然表面上故作淡定,然而實則他的心理已經從懷疑轉為確定,并積極地思考應對之措。
而觀眾之所以會對秦王這個人物形象產生誤讀,原因則在于忽視了視聽語言所暗含的信息,片面地將塑造秦王形象所使用的鏡頭、調度視為對宮廷森嚴秩序和帝王君臨天下的營造,沒有正確解讀影像之下的內在涵義。此外,觀眾同樣被秦王鎮定自若的表演所迷惑,此處的表演其實有著二重性,其一是秦王這個人物形象對于掩飾心中懷疑和恐懼的表演;其二則是演員陳道明在表演角色時使用的技巧和功力。無論從哪個角度解讀,秦王的表演是成功的,否則無法迷惑面前意圖取他姓名的刺客無名,然而秦王的表演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迷惑了觀眾,由于對視聽語言沒有徹底解讀,觀眾無法了解秦王的心理特點,因而造成了誤讀,認為影片中所展現的秦王是一個正面形象,光明磊落,從容不迫。
2、秦王的策略:句句攻心
秦王在與無名會面之后,會出現一系列的心理變化與波動,譬如說,會思考眼前這個人是否是來取自己性命的殺手,被無名所殺的高手們是否是自愿赴死的,特別是殘劍的死格外令秦王疑竇叢生。殘劍作為一個曾經有意刺殺秦王的人,怎么會突然放棄了這個想法,以及究竟發生了怎樣的事情導致殘劍、飛雪接連斃命。對于秦王而言,這些撲朔迷離的事情值得詳細的思考,秦王作為一名政治家,閱歷自然是十分豐富的,推導出事件之間的關聯和本質對他而言并非難事。特別是關于殘劍的為人和性格,不僅是秦王反復思考多次的事情,也是秦王唯一能夠較為把握的信息,因此必須以此作為武器,來去印證無名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秦王與無名之間的每一句交流都是為了保證自身的安全,秦王對于幾個劍客之間的關系洞若觀火,單刀直入下能夠更好地觀察到對方的第一反應,進而掌握整體事態的變化情況。秦王在判定了無名到來的真正目的后,再度產生了疑惑,那就是對方既然是來行刺的,也成功地進入到距離自己十步以內的距離,可以說有十足的把握來行刺了,然而對方卻并沒有果斷出手。那么,接下來如何保住自己性命,這是秦王所要仔細謀劃的,而秦王的應對方式就是用語言進行心理施壓,以求無名自己主動放棄刺殺行為。
秦王心中非常清楚,對于無名這樣的俠士,對其示弱求情是無法奏效的,所以只能用語言作為進攻的武器,以求攻破無名的心理防線。故而,秦王首先挑明了無名的心理狀況,即“殺氣在亂”,然后再狡黠地將無名拉到了自己的身邊,當然是心理上的靠近,即表達最了解自己的居然是刺客。接下來,秦王所表現出來的不是對自己性命的擔憂,雖然這是他內心的真實所想,但是他的言語則要表現出心懷天下的大氣,并不斷給無名的心理施加壓力,最終使得無名陷入如果成功刺殺秦王,那么自己則仁義皆失,有違俠義之名。
所以當秦王似乎開悟一般地感嘆道:“……劍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殺,就是和平。”他的動機實際上就是想讓無名放棄刺殺計劃,而不是真的在談論劍法或者和平。而觀眾想要對秦王的心理以及策略進行深層次的解讀,就不能忽略導演所使用的一系列視聽語言,譬如能夠映襯秦王緊張心情的鐘聲,以及通過近景、特寫鏡頭所展現秦王面部表情細節。只有對這些視聽語言進行透徹解讀,才能真正體會到秦王的真實心理,明白秦王在這段情節中并非心懷天下,而是時刻擔心自己的性命是否安全。
3、秦王的對照:無名
通過對視聽語言和秦王心理的分析,不難發現,在秦王與無名之間,不僅僅存在著戲劇上的張力,而且還形成了極為明顯的對照。特別是厘清了觀眾對秦王的誤讀之后,我們能夠發現這個人物極為多疑、狡黠,并沒有心系天下的可貴品格,秦王的種種表現皆為障眼法,雖然其中的確有真情流露的成分,但歸根結底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一條性命。因此,這部影片的本意當然不是歌頌虛構的秦王或者真實的秦始皇,而是在借助虛構的故事和人物設定來探討人性。
與秦王相比較,無名則更為光明磊落,作為刺客他已經做好了只身赴死的準備,而且他所敢于付出的并非只是自己的性命,還有其他幾位俠義之士的生死之托。秦王擔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而讓無名痛苦的則是權衡朋友的囑托和天下人安危孰輕孰重的問題。所以當我們真正讀懂故事中人物的真實心理動機,才能體會到無名身上的無畏精神和犧牲精神,對比之下,更加襯托出秦王的自私和虛偽。由此,觀眾才能對秦王做出一個正確的評價,那就是秦王的種種表現并非是在憂心國民,而是為了保證自己生命安全的一系列策略。因此,倘若觀眾完全讀懂了二人的真實心理,也就對故事內涵有了更深層次的把握,無名面對秦軍所發射的成千上萬支利箭面不改色,這種“視死忽如歸”的氣魄和情懷更加映襯出秦王的自私和心機。
然而,觀眾對于秦王這一人物的誤讀卻又情有可原,因為影片中所交代的信息的確是將虛構的藝術形象秦王和歷史中真實存在的秦始皇混同了起來,特別是影片結尾處通過字幕交代的信息其實在升華主題的同時,對觀眾形成了誤導,因此有評論稱張藝謀在“贊揚、謳歌秦始皇”也不足為奇。
結語:
綜上所述,《英雄》影片中借用的“秦王”的歷史形象從本質上來說并不具有真實性和還原性。觀眾對于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認識所出現的局限,一方面是因為對于電影試聽語言的解讀不夠深入,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影片中所要表達的情感和交代的信息呈現出了曖昧不清的現象,進而引發了對于秦王的認識偏差。實際上,對這種誤讀進行分析的價值正是在于提醒相關從業者在塑造人物時應考慮到受眾的審美能力和對信息交代的準確性、完整性,進而創作出更為精良的藝術作品。
參考文獻:
[1]任興燕,李維剛.問影音格致別樣紅——《秦頌》、《荊軻刺秦王》、《英雄》視聽影像比較[J].文藝生活·文藝理論,2015(11):128-128.
[2]李嘉,劉海燕.真實的與唯美的《荊軻刺秦王》與《英雄》的電影聲音風格[J].電影藝術,2005(2):106-109.
[3]熊文佳.從電影本體心理學分析影片的隱藏含義——以張藝謀《英雄》為例[J].藝術評鑒,2020(1):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