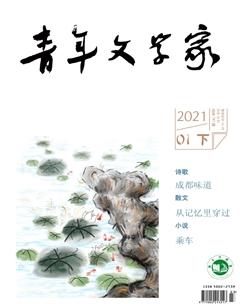淺析張愛玲對女性蒼涼形象的建構(gòu)及其成因
摘? 要:張愛玲的文學(xué)成就決定了她在文壇中的地位,她是研究現(xiàn)代文學(xué)必不可少的作家之一。張愛玲的作品多運用悲涼的意象,華麗的語言,她以冷色的筆觸細致入微地刻畫了眾多悲涼女性形象,讀她的小說猶如喝一杯苦咖啡,越品味道越濃。張愛玲的作品之所以彌漫著濃重的悲情色彩,這和她不幸福的早年經(jīng)歷以及與胡蘭成的失敗婚姻是分不開的。當然,究其根本,離不開張愛玲敏銳的生活洞察力以及當時動蕩不安的社會大背景。本篇論文將立足于張愛玲的典型小說,分析她筆下女性形象的扭曲表現(xiàn)以及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
關(guān)鍵詞:張愛玲;悲涼的人生觀;女性人性的扭曲;封建吃人制度
作者簡介:張元元(1993-),女,漢族,山東省聊城市人,本科,聊城市東昌府區(qū)外國語學(xué)校語文教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3-0-02
一、對張愛玲“建構(gòu)女性蒼涼形象”原因的解析
(一)“建構(gòu)女性蒼涼形象”之早年經(jīng)歷
心理學(xué)表明,早年的成長經(jīng)歷對塑造一個人的性格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起關(guān)鍵性作用,張愛玲可謂是在無愛的家庭中出生、長大的,這對她的創(chuàng)作風格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張愛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的名門望族,她的父親張志沂與她的母親黃逸梵被兩個家庭安排在一起,父親吸鴉片、逛青樓,是典型的民國遺少,母親是追求西方生活的新式女性,兩人的愛情注定不會長久。果不其然,在張愛玲四歲的時候,母親去國外留學(xué),在張愛玲十歲的時候,父母就協(xié)議離婚,而張愛玲隨著父親生活。后來,父親娶了繼母后,家庭關(guān)系變得更加糟糕,父親不僅不關(guān)愛張愛玲,還對她暴力和監(jiān)禁,繼母又總是挑撥事端,家庭沖突不斷,以致在張愛玲幼小的心靈里,父母都已遠去。她成了心理上的棄兒,很無助地長大。
在早年時期,家?guī)Ыo張愛玲的只有孤獨、冷漠和恐懼。遠走他鄉(xiāng)的母親,吸毒、苛刻的父親,心狠手辣的繼母對她的幼小心靈造成極大的傷害,她感受到的家只有無盡的蒼涼與冷,張愛玲的作品是反映她對“家庭”認知的一面鏡子。讀她的作品,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不論是在富裕的公館家庭,還是北京的大院,亦或是貧窮的小家庭中,都找不到一篇歌頌?zāi)笎酆透笎鄣淖髌贰O喾矗碜鳌督疰i記》中刻畫了一個陰險毒辣的母親形象與殘疾的父親形象。[1]在《半生緣》中,張愛玲將顧曼楨的母親塑造為軟弱、可憐、封建愚昧的形象,而父親過早的去世更是缺席了兒女的成長。《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離婚后回到娘家,母親竟對她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你跟著我,總不是長久之計,倒是回去是正經(jīng)。領(lǐng)個孩子過活,熬個十幾年,總有你出頭之日。”在白流蘇最需要安慰與溫暖的時候,腐舊的母親卻想再次將她推進無底的深淵,白流蘇的哥哥也是勢利眼,在妹妹有利用價值的時候百般諂媚,在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便各種嫌棄。總之,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到處彌漫著家庭的蒼涼傷懷,充斥著各種矛盾、心酸與無奈。張愛玲早年的成長經(jīng)歷使敏感的她過早的思考婚戀問題與女性存在的價值,在中學(xué)期間就發(fā)表短篇小說《不幸的她》。與眾不同的出身與經(jīng)歷在她潛意識中生長出悲觀的家庭觀、婚戀觀,悲涼的女性命運觀與人生觀。
(二)“建構(gòu)女性蒼涼形象”之精髓體驗
張愛玲曾經(jīng)說過,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于一個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結(jié)婚了。[2]在她二十三歲,事業(yè)正直巔峰時,卻碰到了傷她最深的胡蘭成。她與胡蘭成那段讓人不禁哀嘆的轟轟烈烈卻又極其短暫的婚姻,曾經(jīng)照亮了她,卻也成了她內(nèi)心深處最痛、最蒼涼的記憶。張愛玲情竇縱開、全情投入,胡蘭成左右逢源、背情棄愛,這種愛戀從一開始就是畸形的,但是胡蘭成給了張愛玲不曾擁有又一直渴望擁有的溫暖與溫柔,所以她深陷其中,即使后來胡蘭成背叛了她,她居然可以不假思索地拿出新得來的稿費來幫助落難的胡蘭成。張愛玲曾經(jīng)說過:“‘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然而它的人生態(tài)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歡壯烈。我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這種反差巨大的對照就如胡蘭成的背叛與她的癡情。[2]這段全投入式的失敗婚姻的體驗對她情愛小說的創(chuàng)作以及女性悲情形象的塑造起到升華作用,張愛玲本就是極其敏感的人,這次深入骨髓的婚戀使她更深刻地體味到什么是蒼涼與悲壯。
(三)“建構(gòu)女性蒼涼形象”之根源
張愛玲出生于1920年的上海租界,此時新文化運動已經(jīng)開始,處于租界的人們相對于其他地方而言則更早地接觸到新文化與新思想,人們一方面極力追求自由的戀愛,自由的婚姻,向往男女平等,但一方面又無法徹底擺脫封建的倫理枷鎖。他們流動于封建舊思想與新文化新思想之間,成為了一個個改造不徹底的、披著新思想外衣的舊思想者。生于沒落貴族家庭的張愛玲表現(xiàn)更甚。豪門家族的沒落不同于小康之家通常的沒落,對后代子孫的心理投影有很大的差別。[1]張愛玲既受到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影響,又生活在一個時尚鮮活的大都市,接受的是新式教會學(xué)校,傳統(tǒng)文化與新文化在她心中交織在一起,具有更深刻的內(nèi)心矛盾。在她的作品中寫了一批遺老遺少,一批半新半舊的人物。他對那些人又恨又同情,又嘲諷又憐憫,這些都可以看出她與舊營壘的精神關(guān)系,以及內(nèi)心感情的深刻矛盾。[1]《半生緣》中的淑惠在面對自己喜歡的姑娘時,明知道翠芝也是喜歡自己的,卻礙于世鈞與翠芝定下親而逃避到國外留學(xué),他雖然有新式婚戀的思想但終究沒有行動,只停留在了思想層面上;在《傾城之戀》中,白家祖上曾盛極一時,可是白家因循守舊、坐吃山空,落得日子過得捉襟見肘,白家為解除窘境,便把白流蘇嫁給了企業(yè)家族的腐朽少爺唐一元,新時代女性白流蘇在大封建家庭面前也只能是一個軟弱的無抵抗主義者,對家庭安排的服從導(dǎo)致了她遍體鱗傷的悲劇。縱觀張愛玲早期的作品,多取材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反映了租界上層社會與中層社會人們的愛恨糾葛、親情冷暖,揭示了社會和人性的本質(zhì),塑造了她筆下人物特有的蒼涼感與悲情命運。
二、女性蒼涼形象的典型
(一)扭曲的人物形象——曹七巧
張愛玲的作品《金鎖記》被傅雷稱為張愛玲最完滿之作,《金鎖記》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最杰出的小說之一,作品講述的是,曹七巧作為一個心靈手巧的純真少女,卻被迫賣給了姜家大院的殘疾人二少爺?shù)墓适隆S捎陂L年對哥哥嫂子的埋怨,對愛情的極度渴望,對情欲的壓抑以及對財欲的向往,她的性格逐漸變得刁酸刻薄、扭曲,最終成為了不折不扣的被封建吃人制度吞沒了的守財奴。張愛玲將七巧個性中由怨恨轉(zhuǎn)為嫉妒再到報復(fù)的性格特征寫到了人性的極致,具有強烈的震撼力,引發(fā)讀者深深的思考。[3]這是她的可悲,亦是時代的可悲,究其原因,在于傳統(tǒng)的封建思想在人們內(nèi)心深處生根發(fā)芽,可以說,女性的悲劇命運的根源都離不開封建吃人的制度和金錢的枷鎖。張愛玲曾經(jīng)說過“我的小說中除了《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其他全是不徹底的人物”。的確,張愛玲對曹七巧的刻畫猶如魯迅先生對孔乙己的刻畫,是如此的徹底,沒有一點死角,讓我們即使拿著放大鏡去審視這些人物依然找不到可憐之處。
(二)喪心病狂的蒼涼形象——顧曼璐
在讀《半生緣》前半部分時,不得不承認顧曼璐的人物形象是非常討喜的,雖然她的性格潑辣蠻橫,而且去當了舞女,但她做事的初衷是為了一家老小的生計與弟弟妹妹的學(xué)業(yè),為了養(yǎng)活一家人,她放棄了與豫謹?shù)膼矍椋欠浅?删纯蓯鄣娜宋镄蜗蟆5窃趶垚哿岬亩鄶?shù)小說中,愛情以及婚姻會變成一個女人的埋葬場,在感情里原本單純、可愛的女性逐漸變得可恨可惡,失去人性,活成了變態(tài)人。顧曼璐也沒有逃脫人物編排的厄運,婚后的顧曼璐性情變得急躁、多疑。丈夫祝鴻才也漸漸露出本性,在外花天酒地,甚至對其愛答不理,形同虛設(shè),導(dǎo)致曼璐對生活不公的憤懣和仇恨不斷在心中滋長、蔓延,她為了保住有名無實的婚姻,將這憤懣和仇恨最終都傾瀉到她的妹妹顧曼楨身上,監(jiān)禁、控制妹妹為祝鴻才生下一個男孩,姐姐的策劃一手毀掉了妹妹的幸福。我認為張愛玲運用全知視角敘述故事,無疑是將自己對愛情的認知與參透人性后的感悟錄入文本之中。書中所展現(xiàn)的不只是愛情與親情的悲劇,更是在封建氣息濃厚的父權(quán)社會中女性遭受精神迫害與人性扭曲的真實寫照。
三、結(jié)語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4]張愛玲的作品猶如《金鎖記》的結(jié)尾,雖然張愛玲已不在了,但張愛玲的作品帶給讀者的震撼力確是無盡的巨大的,讀她的作品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感受到一種蒼涼的情調(diào),她對女性人性的刻畫細致入微,女性悲情命運引人深思,他的作品對我們研究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悲慘命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張愛玲的文本策略深刻反映了她本人以及她所生活的時代。
參考文獻:
[1]宋家宏.張愛玲的“失落者”心態(tài)及創(chuàng)作[J].文學(xué)評論,1988(01):105-112.
[2]牛曉霞.開在塵埃里的花——從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戀悲劇探析其情感訴求[J].名作欣賞,2015(26):51-53.
[3]王瑞;時曙暉.《金鎖記》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分析[J].牡丹,2019(26):94-96.
[4]張愛玲.金鎖記[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