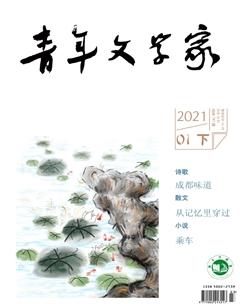巨鰲意象的演化
摘? 要:本文論述了鰲的三個演變階段,即作為創世之神,大地之神和求仙的象征。
關鍵詞:巨鰲;意象
作者簡介:張金栓(1978.2-),男,河北省定興縣人,學士,保定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講師,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教育。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3-0-02
鰲在中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論述了鰲的三個演變階段,即作為創世之神,大地之神和求仙的象征。
一、巨鰲作為創世之神
《淮南子·覽冥》云:“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以足立四極。”說者謂本節所載中心內容在“治水”,其說然否,姑置不議。但斷鰲足立四極一語,人皆以為此一故事之細枝末節,而罕見有深詰者。《論衡·談天》云:“鰲,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謂鰲為獸,于古籍未見他例,待考;但言“四足長大”,已點明鰲非一般動物。關于此節,《意林》卷三引《論衡》佚文“鰲必長大,則女媧不能殺之,必被其殺,何能補天”。雖屬理性疑問,但已點出鰲形之巨,此數條已足證鰲在原始先民心中,為巨大無比的神物。而鰲的神性,當系先民神龜崇拜而來。《說文》中龜鱉鰲俱為從“它”部。又鰲字據《說文·黽 部》“鰲,海大鱉也。”《古小說鉤沉》輯《玄中記》:巨鰲,巨龜也。知鰲鱉龜三者可互換。這一點,是探究鰲創世神原形的一個關鍵。《御覽》引《洛書》:“ 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法地。”又引《禮統》:“神龜之像,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二寸,明告吉兇,不言而信。”神龜神鰲所指本為一事,故此處所引龜的特性亦即鰲的特性。其法天象地、列宿四時等語已儼然有一個創世神形象呼之欲出。《淵鑒類函》引《蠡海集》:“龜之前爪五指,陽也;后爪四指,陰也。故為陰陽之大用。或日前五后四,五湖四海也。”又引《說苑》:“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負陽,上隆法天,下平法地,運轉應四時,蛇頭龍頸,左睛象日、右晴象月,知存亡之吉兇之變,千歲能與人言。”此處所引,補充了神龜五湖四海與日月的象征,極為重要。而《蠡海集》所引“神龜五色”,很可能與“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有一定關系,惜書闕有間,未能考出。故《拾遺記》:“(星)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明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當是同樣觀念。綜合以上所引《淮南子》《御覽》《淵鑒類函》等材料,我們可以發現如下對應關系:
據上表發現,鰲的各部位正與天地日月列宿丘山江海四時相對應。這與創世大神盤古、燭龍正具有同樣的特征。《山海經·海外北經》:“鐘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大荒北經》:“(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寢、不食、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鐘山,章尾山為一山,燭陰,燭龍為一神,袁珂先生云:“燭龍之神格,蓋與開辟神盤古相近,其為盤古原型之一。”盤古神話見《五運歷年紀》:“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岳,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發 為星辰,皮毛為草木……”將燭龍神話與上引巨鰲(龜)形象對比,我們發現,二者深層結構是一致的,據此判斷,巨鰲在古時為開辟神之一,正是已經亡佚了的化生創世型神話。關于上述判斷,尚有下列材料支持:《文選·張衡<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屃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李善注引《遁甲開山圖》“有巨靈胡者,遍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這一故事尚見于《水經注》卷四。這里有三點應注意:(一)云巨靈屃赑,正是“巨靈鰲”的意思,王逸注《天問》“鰲戴山抃”句:“有巨靈之鰲”正指此。(《天問》所注已是巨鰲形象的第二階段,詳后)而“屃赑”據楊慎《升庵外集》卷九五:“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躍是也。”故知屃赑實為龜(鰲)之屬。二謂遍得坤元之道,坤為陰、為雌,而《說文·部》說龜“廣肩無雄”;(三)“造山川,出江河”正是創世活動。有此三條,我們可論定,巨靈屃贔的神話正是古傳鰲化生創世神話的殘留。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理解龜“同天地之性”(《說文·龜部》)“可卜天地之終始”(《御覽》引《柳氏龜經》)等說法,因為龜(鰲)便是天地本身的化身啊!
二、論鰲為大地之神
鰲為地神是巨鰲母題發展的第二階段,可惜這個情節在古籍中湮沒了,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巨鰲戴山”的神話遺留。《楚辭·天問》“鰲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鰲,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此處蓬萊,《列子·湯問》作“五山,”說歸墟中有五山,隨波流動,不能暫峙,仙圣訴于上帝,帝“命禺強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關于鰲與禺強的關系,《山海經·大荒東經》:“黃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禺京處北海,是為海神。”郭璞云:“即禺強也。”郝懿行云:“莊子(《大宗師》)《釋文》引此經云:“北海之神,名曰禺強,靈龜為之使,”[9]此處靈龜,即《天問》《列子》所謂巨鰲。而禺強,禺京實即《莊子·逍遙游》中的鯤,文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若禺強為鯤之說成立的話,此則寓言可以發現如下幾組關系
這里我們找到一組有趣的結構,古人觀念里,北方是“幽冥無日之國”,魚、鯤、水、下都是陰性,消極的象征,因此,恰如王孝廉、葉舒憲所指出的那樣,鯤(禺強)所居的北冥,正是地獄的所在。也因此,神話才說禺強“字玄冥”“黑身手足”“為大疫厲鬼”。
上述判斷的一個佐證是,鵬即鳳,而卜辭云“帝使鳳”,“帝”古指“天帝”,鳳既與鯤對立,鯤自屬“地帝”即冥界主宰無疑。假如對禺強神格的判定無誤的話,也就理所當然斷定:作為禺強之使的靈龜(巨鰲)自是地府之神。巨鰲作為地神,有兩個子母題,一為巨鰲負地;二為地府使者。這一結論我們可以在文物資料中找到支持:馬王堆西漢非衣帛畫展示了三界情景,下方長形白色物為大地象征,下方一巨人負地,兩旁是兩只巨鰲。這個巨人為禺強,巨鰲即禺強所使的“靈龜”,它反映了巨鰲作為大地之使的事實。”
三、巨鰲與求仙
神仙觀念似可溯源于殷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已有精美的玉羽人出土。但巨鰲與求仙觀念發生關聯,最早的文獻可能是戰國中晚期的《天問》:“鰲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引《列仙傳》,此書舊題劉向著,向著書多依舊聞,故保存古說的可能性較大。王注:“《列仙傳》:有巨靈之鰲,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中,”雖末明言鰲與求仙的關系,但既出自《列仙傳》則求仙內涵不言自明。
巨鰲與求仙觀念尚可于文物中求證。
(一)為西漢時鰲斗拱,斗拱模制,空心,三層。負載于一蛙身之上,而蛙又負載于鰲背上,斗拱柱兩側各伸一獸頭,正面繪有西王母圖像志。關于西王母,我們知其為仙人象征,這一觀念由《大人賦》《漢武故事》《西王母神異傳》等典籍可證。而蛙,鰲(龜)也都有長壽的文化內涵。《抱樸子內篇·對俗》:“蟾蜍壽三千歲”又《仙藥》篇“肉芝者,謂萬歲蟾蜍。”而龜之長壽則屢見文獻。因此我認為上述斗拱表現的主題為求仙長壽。這是巨鰲與求仙觀念聯系的物證之一。
(二)1993年江蘇東海尹灣西漢墓出土的一繒繡衾被,在被稱作“幢”的飾物上,畫有一只鰲,居衾被頂端中央,四周繪有光芒,論者以為“喻長壽或作仙人導引。”此說甚確。若我們將其放在巨鰲求的母題的大環境中來看,“長壽導引”正是求仙。此處之鰲或許正是已仙話化的黃帝(天黿)的象征。
(三)為沂南漢末畫像石墓,墓中室西柱頂端刻西王母像,王母像下為巨鰲戴山。西王母是神仙象征,故此處巨鰲戴山自是求仙主題無疑。張衡《思玄賦》云:“登蓬萊而容與兮,鰲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已明確地將鰲與長生聯系起來。
巨鰲與求仙發生聯系,從民族心理層面而言,我認為當來自于古人對龜長壽和復活的認識。《說文》:“龜,舊也;”《洞冥記》卷二黃安生神龜,二千年一出頭,已見五出頭矣;《御覽》引《柳氏龜經》“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說苑》龜“千歲能與人言。”都是神龜長壽觀念的反映;龜甲破裂而能迅速愈合,自然引起古人的興趣,這與對復育、蟾蜍鹿的信仰在內涵上是一致的,本質上應是一種生命崇拜。
至于鰲(龜)能復活則亦不史證。《天問》鯀“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左傳》作“黃能”,實當為黃熊,乃三足鱉之屬。又《蜀王本記》:“荊人鱉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貝蜀王杜宇,立以為相。”《抱樸子內篇·辨問》“鱉令流尸而更生”,正可作鱉(鰲)復生之堅證。正是因為鰲長壽、而死后復活的特征,才將鰲視與求仙聯系,仙境因而也才設在巨鰲所負的蓬萊,員嶠諸山。而巨鰲負山神話正是求仙母題演化的一個契機。
參考文獻:
[1]漢·劉安 《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1954年.
[2]袁珂《古神話選擇》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年.
[3]漢·王充 《論衡》 北京: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 1954年.
[4]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 1963年.
[5]魯迅《古小說鉤沉》《魯迅全集》1948年.
[6]宋·李日方《太平御覽》《四部叢刊》本1977年.
[7]清·張英、王士禛等纂《淵鑒類函》 中國書店影同文書局本 1985年.
[8]前秦·王嘉撰、梁·蕭綺錄《拾遺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9]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