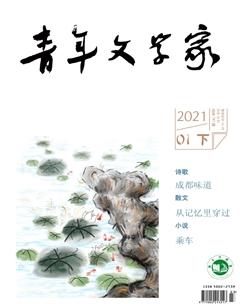《子衿》主旨淺談
張倩倩
摘? 要:《鄭風·子衿》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詩經名篇。歷來學者們都以傳統經學的解詩方式對其論述,很早就被定義為“刺學校廢”、“學子之歌”等主題,然而從其文本詩義來看,很顯然是一首婉轉動人之情詩。本文重點對《子衿》中的重要字、詞進行釋義,并在此基礎上對歷代詩旨的分歧予以一定的分析。
關鍵詞:青衿;挑達;經學;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3-0-02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曹操《短歌行》中這句膾炙人口的詩句流傳頗廣,詩中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即來自《詩經·鄭風·子衿》篇。《子衿》全詩三章,每章四句,其言: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一、詩中幾個重要字詞
詩中“青青”是“青”之疊詞,為“衿”之顏色自不待言。
那么“青衿”中之“衿”為何物?我們且看“衿”字左邊“衣”字旁就可以知道這是和衣裳相關的。其一種解釋,“衿”:衣領。《傳》云:青衿,青領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
另有一種解釋,“衿”:衣帶。劉毓慶先生言:詩歌首章言“子衿”,次章言“子佩”,當有聯系。衿疑即佩衿,《爾雅·釋器》:衿謂之袸,佩衿謂之褑。郭注:佩玉之帶上屬。《方言》曰:佩衿謂之裎。郭注:所以系玉佩帶也。紟、衿通。《廣韻》:裎,佩帶也。佩衿即系瓊琚等物的帶子。下章之帶,即帶子上所系的佩物。《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如此一來,“衿”指佩帶。“子衿”即子所贈之佩帶。
“挑達”常常被解釋為獨自徘徊的樣子。歷來學者皆出于符合經義之需要而解釋“挑達”,或是從《傳》“往來相見之貌”之解;或是以為“廢學后輕佻之態”;又或是認為“廢學遨游無度之態”。暫時拋開經學桎梏,何不以詩歌之文本意義出發,理解為是詩中主人公赴約時心里焦急、欣喜之心情在走路姿態的外現,以及等待戀人時之踱步之態,這樣豈不更符合詩義。
二、關于《子衿》詩旨的分歧
關于《子衿》詩旨,以現存的文獻來看,在漢朝以前,毛亨《毛傳》中就有:“《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1]認為其主旨是刺“廢學”的諷喻詩,這是最早也是最經典的經學詮釋。后來東漢經學大師鄭玄所作《鄭箋》,代表了漢學體系之下的新儒學體系,其在繼承《毛傳》“亂世廢學”之觀點為背景,在此基礎之上對詩中字詞進行訓釋,并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到唐時孔穎達《毛詩正義》,在前二者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擴展補充,引用史實印證了《毛傳》的觀點,而且還詳實了《鄭箋》的內容。于此,一脈相承而來的觀點深入各學者心中。
宋儒及宋以后的經師,縱然對漢唐時幾乎成為共識的“刺廢學”這一詩旨時或否定,甚至脫離了詩歌歷史化、政教化這一軌道,以詩之文本為出發點,探尋詩歌本義,然而終究是沒有徹底拋棄經學式的解詩思路,在各自時代背景下,或弘揚舊說,或自立新論,現擇其要者,列以下數種:
1、“禮樂不可廢”說。持此觀點的學者人數眾多,這個說法源自《毛傳》發展而來,其后《鄭箋》、《孔疏》也都如此。宋《毛詩講義》:“學者于學校不修之時,而猶思麗澤之貌。”[2]元胡一桂認為鄭國雖然是亂世,但禮儀猶在人心,才會有詩中悠悠思望之切,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后來的段玉裁、范家相各在其《毛詩故訓傳定本》、《詩瀋》中也表示《子衿》詩旨該為“禮樂不可廢。”
2、“教者勸學”說。宋戴溪明確提出詩歌該出自“教者”,認為《子衿》乃教者對于學者荒嬉于學業而憂心。“教者勤而學者怠……世治則后生拳拳于長者,世亂則長者懷念于后生。”[3]戴溪后,楊簡在《慈湖詩傳》中也認同此觀點。清姚際恒在《詩經通論》中論述《子衿》也持此觀點。后來有很多學者如田澄之《田間詩學》、張沐在其《詩經疏略》、王心敬在其《豐川詩說》中都以傳統儒家教習為出發點,來論述師生之間應往來相習,認為《子衿》是師傷弟子廢學,不見而念之深切的詩歌。
3、“育才也”說。明李資乾在其《詩經傳注》中首次提出:青衿,育才也。并與《風雨》詩義結合來論述《子衿》。清時陸奎勛在《陸堂詩學》中、張敘在《詩貫》中論述時都將《子衿》與《泮水》相連屬來論詩旨,認為是“思學士而刺之。”傅恒《御纂詩義折》、姜炳章在《詩序補義》中都以“育才”為《子衿》之旨。
4、“鄭子產不毀鄉校”說。明何楷:“《子衿》,鄭子產不毀鄉校也。《序》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意亦近之,而特未明此詩立言之旨。 愚按:鄭時有毀鄉校之議,故至鄉校者頗少,子產意在使夫人游焉。論學之余因之議論國政而知其所行之得失。所以通篇皆屬望生徒來游之語。”[4]
5、“留者念其去者而責”說。明曹學佺在《詩經剖疑》、清李塨在《詩經傳注》、胡承珙在《毛詩后箋》中都從《鄭箋》論述中之“去、留”二字作為出發點,認為學子都應在學校之中,己留彼去所以思而責之。
6、“學子不相見而思”說。宋歐陽修《詩本義》認為: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在一起居住,學子互不相見而產生思念之情。宋李樗、黃櫄《毛詩李黃集解》言:學子在學校有留有去,可見學校并無盡廢,學子朋友不得相見而歌。宋范處義《詩補傳》中說學子往來于城闕,不得相見。賀貽孫《詩觸》:“學校廢則朋友疏矣,故思而望之,思其服而相見其人……”[5]可見歐陽修此說頗受認可,很多日韓學者如:伊藤善韶《詩解》、冢田虎的《冢注毛詩》、成海應的《詩說》、李炳憲的《孔經大義考》、金魯謙的《龍園雜識》等都繼承了歐陽修的看法。
7、“賢者傷世”說。呂祖謙曾引程頤《伊川經說》卷三《子衿》篇,認為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所以“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棄絕於善道乎?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于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焉?故悲傷之而已。”[6]
8、“淫奔之詩”說。宋朱熹打破傳統經學之說,首開以情、以文本說詩,提出“淫奔詩”之看法,但在其《白鹿洞賦》中又自相矛盾。然而,宋時朱熹理學地位強固,以至于后來元朝時許謙、劉謹,明朝季本、清朝冉覲祖、姜文燦等人皆從其說。即使如此也依然有如明時戴君恩在其《讀風臆補》中、郝敬在《毛詩原解》中提出質疑。
9、“男女相與之淫女之詞”說。此說實則基于朱熹。呂祖謙之弟子輔廣:“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一二章致思而微責,三章切責而深思。”[7]元代朱公遷、明代鄒泉、許天贈、顧起元等人贊同此說,并在著作中直接引用。
10、“朋友相責”說。此說倡于上第六條之“學子不相見而思”。宋王質在其《詩總聞》中提出《子衿》詩是兩位賢者由于思念而辭,義為:在位之人求賢于在野之人。后來的陳啟源、李光地等人也認同此說。
11、“思君子”說由日本皆川愿提出。“思婦”說由日本山本章夫首提。此兩說為日本學者們個人之見。
12、“寄衣”說由清牟庭首提,他認為是古時候學子游學于外,家中妻子為丈夫寄衣以御寒。此說與前人、后學者意見均不同,可謂立意頗新。
13、“愛戀詩”說在現代文學家眼中是最主流的共識。聞一多、高亨,余冠英、聶石樵、程俊英、劉毓慶等學者都認為《子衿》為男女相悅之情詩。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詩無達詁”,種種說法都是從《毛傳》初始定義發展而來,有的學者皆從舊說;有的繼承舊說并弘揚擴展;也有的學者非駁舊說,持慎重的態度不確定其義;也有學者另辟新意,然而求新、求異都不是解詩正道。在“愛戀詩”之觀點產生以前,大部分學者都是以傳統經學的解詩方法來論述《子衿》之主旨,只有少數幾個像朱熹一樣的學者突破了這種模式,然而在朱子強大的理學背景之下,《子衿》被認為是一首“淫奔詩”。幾乎沒有人從詩歌的文本之義出發去解釋論述。因此《子衿》一直以來都是以“詩經”的面貌示人,而非“詩歌”。
三、怎么讀《子衿》
我們不妨脫離經學解詩模式,簡簡單單的讀詩之文本,便會自然而然覺得這是一首情詩。主人公癡迷的想念著心中的那個人,他青綠的衣領、佩著玉的綬帶讓人沉醉。約好了時間,卻看不見他,心情失落、惆悵……愛之既深、責之愈切,對于他失約的情況,心中可以設千萬種原因為他開脫,但終因見不到對方而無法諒解。因此兩次設問“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寧不來?”然而最終還是無可奈何,只能一個人獨自徘徊于城闕,以抒發自己心中之感慨,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這首戀歌多么纏綿悱惻、多么婉轉動人,寥寥數語,便讓幾千年來的讀者都能感同身受,可見古人之語言智慧。
參考文獻:
[1][唐] 孔穎達.毛詩正義.卷四.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13頁.
[2][宋] 林岊.毛詩講義.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第78頁.
[3][宋] 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第816頁.
[4][明] 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第 844頁.
[5][明] 賀貽孫.詩觸.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6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33頁.
[6][宋]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第429頁.
[7][宋] 輔廣.詩童子問.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33頁.
[8]劉毓慶、賈培俊、張儒《詩經百家別解考》山西大學百年校慶學術叢書.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