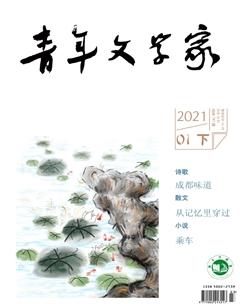沉默的欲望
摘? 要:父親因不能忍受現實世界巨大的壓力,又無處傾訴,只能選擇自己搭建起一個“異托邦”,作為典型的現代主義小說,在敘事的形式上對傳統小說是一種顛覆或沖擊,在這里,類似于父親這樣的形象,已經不再是活生生的個人,而是“個體”,社會的觀念和結構,為每一個人預設了思想和行動的空間邊界,逾越邊界的個體,是不會被傾聽、被理解的。這種個體,不會被消滅,而是被壓抑、控制在邊緣地帶,因此,和主流空間若即若離。本文將從《河的第三條岸》文本出發,結合福柯的異托邦理論,分析文字背后的深意。
關鍵詞:主體失語;福柯;異托邦
作者簡介:韓江楓,女,漢族,吉林長春人,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3--03
那是一個霧氣蒙蒙的清晨,父親拖著一艘含羞木制的船,帶我沿著河岸一直往下走。我聽見水波聲由遠及近把水汽帶到岸邊,滋潤了我的身體。飛鳥輕輕掠過水面,驚起點點浪花,青綠色的水面上,笨重的鴨子成群結隊地游過。我看向父親,他今天好像異常嚴肅,又格外沉默。到了河邊,他坐上了那條含羞木做的小船,我以為是好玩的游戲,趴在巖石后偷偷看他,但卻不是。父親欺騙了我,拋棄了我,我一輩子都為此懊惱……
試想一個孩子在一無所知的情境下被父親拋棄,該是多么痛苦的遭遇。故事中的父親就是這樣一言不發地離開家庭,用含羞木自制的小船獨自一人泛舟大河之上,去追求“河的第三條岸”卻不遠離,只是徘徊,直到兩鬢斑白。“我”終于鼓起勇氣勸說父親回家,說要接替他的位置。得到允諾之后“我”卻接受不了陌生的父親,落荒而逃。父親再也沒有回來,而“我”直到彌留之際也沒有解開這個心結。全文重心理描寫,多象征,這也是若昂·吉馬朗埃斯·羅薩小說一貫的特點。
一、主體的失語
文中處處充斥著詭秘的沉默,我們聽得見河水的流淌,聽得見岸上人模糊的閑言碎語,卻聽不見真心交流的聲音。拉康認為,主體之間是永遠沒有辦法直接交流的,語言不可能直接到達他者。因為在象征層面上,存在著一堵“語言之墻”。這種“語言之墻”在文中一方面體現為作者相信讀者與故事的主體能夠達到一種默契,這種默契來自相似的生命體會和社會經驗;另一方面是因為話語總是不能完整表述主體意識,而無聲的嘶吼反而更具有沖擊力。《河》中,沒有只言片語能直達父親,只能依靠這些虛影去臆測了。即使是“失語”的父親,他對于家庭、對兒子,對妻子仍然表現出一種牽掛。聯系這個時代,我們暫時可以這樣理解:父親因社會責任過于沉重而選擇漂流,也正因家庭責任的牽絆、不舍親情和愛情而不忍走開。作者用讓人物失語的方式,把人物之間關系的復雜性以及主體的欲望最大程度的表現出來。
唯一直達人物的鮮活是在結尾,“我”已老去,又到河邊,對著父親的背影莊重地發誓:“爸爸,你在河上浮游得太久了,你老了……回來吧,你不是非這樣繼續下去不可……回來吧,我會代替你。就在現在,如果你愿意的話。無論何時,我會踏上你的船,頂上你的位置。”父親答應了,“他聽見了,站了起來,揮動船槳向我劃過來。他接受了我的提議。他舉起他的手臂向我揮舞——這么多年來這是第一次。”被社會異化的父親身上終于流露出了人性,他“揮舞手臂”、迫不及待地向新世界奔去。兩個人的執念沖破了空間在此會面了,再向前一步,也許執念都能得以了結。但是,“我突然渾身顫栗起來。我不能……我害怕極了,毛發直豎,發瘋地跑開了,逃掉了。因為他像是另外一個世界來的人。我一邊跑一邊祈求寬恕,祈求,祈求。”不僅令人懷疑,兒子拒絕婚姻、拒絕接納的真實原因:究竟是為了等待父親回來,還是不愿意承擔起責任?欲望扭曲蠶食著他們的心,內心的和解,才應是他們最后的追求。
可以想象,父親一定嘗試過與家庭、與世界溝通,但溝通永遠無法直達并總以失敗告終,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選擇緘默、選擇漂流、期待一個新世界的到來。他渴望別人的理解,徘徊不離開就是為了等一個答案,兒子的那番話已經搭起了一座橋梁,當他以為兒子終于愿意和他溝通,幫他分擔憂愁之時,兒子卻突然落荒而逃,那么父親只能又一次回到冰冷的河流之上繼續漂泊。
二、社群的驅逐
而這一切沉默都來源于意識形態的控制與壓力,父親劃舟離開后,小鎮上議論紛紛,“每個人都嚇壞了。從未發生過,也不可能發生的事現在卻發生了。親戚、朋友和鄰居議論紛紛。
“幾乎每個人都認為(雖然沒有人說出來過)我父親瘋了。也有人猜想父親是在兌現曾向上帝或者圣徒許過的諾言, 或者,他可能得了一種可怕的疾病,也許是麻風病,為了家庭才出走,同時又渴望離家人近一些。”麻風病的意味在西方文學遠遠不止是疾病本身,更象征對人的厭棄。“從詞源上說,患者意味著受難者。 但令人恐懼的還不是受難,而是這種受難使人丟臉。……當疾病的傳染性使那些本該前來助一臂之力的人惟恐避之不及,甚至連醫生也不敢前來時,這是對病人的公民權的剝奪,是將人逐出社會……”[1]麻風病人還未來得及得到救助,就已成了偏離社會環境的“他者”。“河上經過的行人和住在兩岸附近的居民說,無論白天黑夜都沒見父親踏上陸地一步。……母親和別的親戚們一致以為他藏在船上的食物很快就會吃光,那時他就會離開大河……”不僅如此,就連父親信任的母親也請來牧師驅走父親身上的魔鬼,叫來兩個士兵來威脅他,又找來新聞記者拍照。所以無論是家庭內的私人空間還是社群中的公共空間,在本質上都屬于“意識形態”的空間,意識形態的觸角、權力的觸角幾乎無處不在,它們定型了城市人的生存狀態。
在常規空間的定位失敗,使得他找不到自我,無法進入規約社會,無法遵循規訓空間的秩序,無法忍受對個體的禁錮和馴服。面對社會的壓抑,父親選擇了沉默。反抗無異于以卵擊石。“河的第三條岸”就是他心中自由的象征——即使永不存在,也絕不會存在于如今的世界里。他想借由自由與充滿變化的水來達到對夢想的無限接近,但文章結尾兒子的反應說明了一切,無異于關上了父親永遠隔離于另一個世界的最后一扇門,“我不該這樣,我本該沉默。”這是“我”得到的最后啟示。
三、前往“異托邦”
福柯早就認識到,時代充滿了焦慮,是因為現代空間是以圓形監獄發展起來的,現代人的話語、行為等都在監視之下,有特定的規范。“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筑。……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監督者,在每個囚室里關進一個瘋人或一個病人、一個罪犯、一個工人、一個學生。通過逆光效果,人們可以從瞭望塔的與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觀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這些囚室就像是許多小籠子、小舞臺。”[2]這是一種由“看”衍生出的權力運作方式——“全景敞視主義”。福柯認為“看”也是權力建構的方式之一,在“看”的同時也在“被看”,這種看與被看的二元統一機制無處不在,學校、工廠、監獄、瘋人院實際上都變成了“異托邦”,是游離于真實空間的“異質空間”,這種空間是權力運作的基礎。所以福柯洞察到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特殊空間場所其實都具有異托邦的性質。
父親和兒子都為自己的執念奉獻了一生,兒子的執念是等待,從“我”目睹父親離家,就一直在反思、責怪自己“我有什么不對?我到底有什么罪過?”不思婚娶,從未離開家鄉;父親的欲念不是尋找,只是拒絕。拒絕現實生活的瑣碎,拒絕敞開心扉,拒絕上岸,甚至拒絕遠方,這種與世界若即若離的“拒絕”,作為隱喻,事實上構成了福柯所言的“異托邦”——一種與中心和主流對峙的被壓抑、被凝視的“非正常”的生存狀態。“烏托邦”是徹底否定現實的,或者說是在現實的彼岸的,是一個“不真實的空間”。而“異托邦”則能解釋這個矛盾或闡釋的難題。它是一個社會或者文明結構,用以安置異己性思想、觀念、存在等的實體,是真實存在于社會結構內部的,比如瘋人院、監獄——尤其是瘋人院,那些不被理解的,便被判定為癲狂,被安置在特定的場所,它同正常狀態的社會和人保持距離,但并不是完全沒有聯系,它同所謂“正常的社會”或“正常的人”對照,用以確證后者自身的合法性。異托邦脫離于所有其他的場所,卻真實存在,比如學校、工廠、監獄、瘋人院等。它的聲音和欲念,不被理解,卻證實了中心和主流的“正常”與“合理”。因此,這些欲念無異于作繭自縛,最終毀了自己。拉康認為,在需要得不到滿足而轉向需求時,需求將欲望與語言形式的條件聯結起來,從而泄露了欲望的真實意義。欲望超越了需求,它將走得更遠,因為它是不可能被滿足的,所以欲望是永恒的。在當時壓抑天性的社會中,真正的欲望和需求無法得到表達。因此只能被動地等待,他們把靈魂封閉,期待自由的光可以照進來。但是福柯卻沒有給“異托邦”的性質以明確好壞的規范,父親的離開是好是壞我們不得而知。尋找第三條岸可能是光明的,《圣經·創世紀》中一開篇就說,神先創造水,再創造天地萬物,可見水的原初生命力量,水還有潔凈、凈化的含義,在《圣經》《新約》中,“洗禮”最初是指施洗約翰在約旦河中施的洗,它是一種悔改的記號。入教的信徒需要在額上、身上施灑圣水,以洗去“原罪”,獲得全新的生命。父親乘的小舟也可能如希伯來人的洪水再生神話諾亞方舟那樣,帶走黑暗和悲劇,帶來新的光明與希望。文中描述道,“船的影子像一條鱷魚,靜靜地從水上劃過。”非洲的某些部族至今仍因鱷魚的勇猛和兇殘,它遠超其他種族的耐心與韌性,而將鱷魚奉為圖騰,男子舉行成年儀式時,在前身體各處留下的形如鱷魚皮紋樣的刀痕,鱷魚也是重生的象征。
但即使水面風平浪靜,水面下也可能是暗流涌動的。“父親的河流”帶有神秘的支配感和令人生畏的色彩,是希望和危險并存的。父親去尋找河的第三條岸的行為,我們眼中是永遠實現不了的,他想借由自由與充滿變化的水來達到對夢想的無限接近,這是不現實的,最后的結局只能是潘多拉的魔盒。就像電影《楚門的世界》影片結尾,楚門不想再在桃源島上忍受虛偽的生活,準備離開時,基斯督同他說,“你是真的,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看你,聽我勸告,外面的世界和我給你的一樣虛假,有一樣的謊言,一樣的欺騙,但在我的世界,你什么也不用怕,我比你更清楚你自己。”幻覺終將破滅,父親在這個自我構建的異質空間中,既無法保持自己的本性,也無法認同現實社會文化,最終導致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父親被困在尋找、漂流、封閉的人物狀態里,作者將人物的個性隱去和抽離,成為一個模糊的,轉喻的符號。這是社會的群像,在各個角落,都有這樣無奈的人存在,被壓抑、被忽視是大部分人的普遍生存狀態和生存困境。每個人都曾尋找過釋放欲望的出口,但最后都像這一對父子一樣,沉默無處訴說,宿命般地令人扼腕。從父親、到兒子、到母親、到姐姐、抱持傳統思想的其他人,無一例外地都是被現實壓抑的可憐人。人類的抗爭永遠也沒有盡頭,只能在矛盾中尋找一條稍為柔和的路……對于此,柏拉圖建議我們“把向上的旅程以及對地上事物的思考理解為一個靈魂向著可知領域的向上旅程。”離理念世界越近,那么靈魂越“向上”,便離“至善”越近。雖道阻且難,卻是追尋自由的路上必經的。
注釋:
[1]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2][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修訂譯本.劉北成,楊遠嬰譯4版.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9.第224頁.
參考文獻:
[1][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修訂譯本.劉北成,楊遠嬰譯4版.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9.
[2][法]米歇爾·福柯.另類空間[J].王喆,譯.世界哲學,2006( 6) : 52-57.
[3][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等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