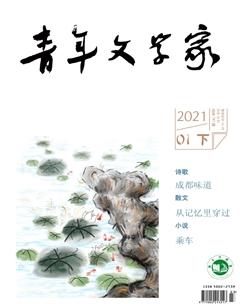溫特森小說互文性特征的成因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9年西安歐亞學院校級科研項目“珍妮特·溫特森小說的互文性特征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9XJSK12)。
摘? 要:珍妮特·溫特森的小說文本具有典型的互文特征,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溫特森的人生經歷、“影響的焦慮”,讀者的誤讀、批評性閱讀,以及當時社會的兼容并包思想、互文創作風氣。
關鍵詞:溫特森小說;互文性;“影響的焦慮”;誤讀
作者簡介:郭海玲(1985-),女,河南南陽人,西安歐亞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3--02
珍妮特·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1959-)是英國當代作家之一。她擅于在小說文本中運用引用、戲擬、重寫等互文手法,將眾多文本編織進一張巨大的互文之網中,使其小說文本呈現出典型的互文性特征。為了深入了解溫特森小說的互文性特征,本文從作家、讀者和社會三大層面來挖掘其小說呈現互文性特征的原因。
一、作家層面:人生經歷、“影響的焦慮”
溫特森一出生就慘遭生母遺棄,年少時又被養母驅逐,兩次被遺棄的經歷讓溫特森的內心傷痕累累,這種難以療愈的“棄兒”情結使她的小說中多次出現棄兒形象。比如小說《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給櫻桃以性別》和《時間之間》講述的都有棄兒的故事。這些小說中的棄兒形象構成了互文關系。與養母決裂后,溫特森開始在精神病院、殯儀館等地打零工。這段艱辛的謀生經歷為她提供了豐富的寫作原材料,其中精神病院、殯儀館等意象就被作家寫進了《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激情》中,當然,這可以從溫特森的訪談中得到印證:“……我也喜歡殯儀館,我并不害怕尸體,也不畏懼死亡。在那些地方,遇到了那么多的人,我盡可能以此構想我的世界。”[1]她所說的“構想我的世界”指的就是構思她的小說中的世界。很明顯,“棄兒”經歷、謀生經歷這些刻骨銘心的記憶都在她以后的小說中得到了再現或重構,使其小說幾乎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作家個人經歷的烙印,從而呈現出或隱或現的互文特征。
除了獨特的人生經歷,作家的小說創作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她以往閱讀書籍的影響。美國文學理論家布魯姆從心理層面對這種影響作了詮釋:“當代詩人或作家就像一個具有俄狄浦斯戀母情結的兒子,面對詩的傳統這一父親形象,在受前代偉人影響與壓抑的焦慮中,只能采取各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誤讀方式來貶低前人或否定傳統,達到樹立自己形象的目的”[2],詩人是這樣,小說家也莫不如此。溫特森的小說也是受前人或前文本影響之下的產物。對溫特森而言,《圣經》是她創作的靈感源泉,她曾坦承《圣經》帶給自己的“影響的焦慮”:“我對《圣經》太了解了,如果不去處理我與這本書的關系,我自己都會感覺很荒謬。”[3]p89她的多部作品都將《圣經》作為潛在的對照文本,從而使這些作品呈現出互文性特征。例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小標題全部借用了《圣經》的章節名,有著明顯的顛覆、解構意味;在《重量》中,溫特森將《圣經》作為一種深厚的傳統來接受,借以進行自我的重建;《時間之間》的人物、情節、主題都對《圣經》進行了化用。
總而言之,對于文學遺產,溫特森的態度是:“我要從這份遺產中汲取最多的養分,然后盡我所能將其效用發揮到最大” [3]p99。在自身人生經歷的基礎上,溫特森一直盡可能地博覽群書,并將生活經歷和文學素養轉化為寫作的材料資源,在這種影響和轉化的過程中,她的作品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相互呼應、相互指涉,從而顯現出典型的互文性特征。
二、讀者層面:誤讀、批評性閱讀
探析文本的互文性成因不能只考察創作方,接受方即讀者同樣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正如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言:“一切文學作品都由閱讀它們的社會‘重新寫過,只不過沒有意識到而已;事實上,沒有一部作品的閱讀不是一種‘重寫”[4]。的確,任何讀者在閱讀一本書時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生活閱歷、感知能力、知識儲備等,因此,閱讀過程難免會引發讀者的有關記憶和聯想,這些記憶和聯想反過來又會影響讀者對文本的理解。讀者可能會把自己的相關文本記憶、世界觀、價值觀等融入到對當前文本的理解中,甚至還可能附加上新的寓意。文本通過讀者閱讀所生發的意義來自他在閱讀過程中帶入的全部文本的相互交叉、相互影響的作用,這就必然導致或深或淺的“誤讀”,按照布魯姆的觀點:“影響意味著,壓根兒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則取決于一種批評行為,即取決于誤讀或誤解……”[5]這種“誤讀或誤解”可以理解為創造性閱讀,是讀者主動參與文本意義的建構的過程,隨之便產生了文本的互文性。由于一貫喜歡用意識流、時空交錯的非線性敘述手法,再加上對各種文學記憶的信手拈來,溫特森的小說要求讀者有一定的文學背景,且具備較強的深層挖掘能力和知識遷移能力,這樣他們才能依憑文學傳統的寶庫來觀照溫特森的小說文本。正因如此,溫特森的所有小說文本就不可避免地落入龐大的互文之網中。
此外,不同的讀者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文學記憶和批評能力,因此他們對同一文本必然有著深淺不一的理解,也必然會解讀出各自相異的互文現象,正如薩莫瓦約所言:“互文性的矛盾就在于它與讀者建立了一種緊密的依賴關系,它永遠激發讀者更多的想象和知識,而同時,它又遮遮掩掩,從而體現出每個人的文化、記憶、個性之間的差別。……所以對互文的感知可能會是變化和主觀的。”[6]這就是說,讀者的誤讀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因此他們對小說文本的互文現象的解讀也勢必包含了主觀性。例如,同是對《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互文解讀,遼寧師范大學的王飛飛發現了該小說與傳統生活方式、神話傳奇等的互文關系,而蘇州大學的關碩則發現了該小說與“美女與野獸”、“小紅帽”、《簡愛》的互文關系。由此不難看出,不同的讀者會產生不同的感受和理解,隨之挖掘出不同的互文網系,而不同的互文網系自然又使同一部小說催生出不同的思想意義,小說文本也因此得以展現出多姿多彩的互文現象。
三、社會層面:包容思想、互文創作風氣
英國自17世紀以來鮮有暴力革命,人們的思想較為保守。20世紀60年代,甲殼蟲樂隊、搖滾音樂、背離傳統的嬉皮士和詹姆斯·邦德偵探小說風靡全國,各種新思想、新潮流噴涌而出,極大地沖擊了保守的英國文化。到了80年代,兼容并包思想早已滲透到了社會和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社會大風氣的轉變勢必會對身在其中的所有個體產生影響,溫特森自然也不例外。這種包容并蓄的思想反映到她的小說創作中,就轉化成為林林總總的文本雜糅,使其小說呈現出多種文化、多種觀念相互對話、相互參照的互文現象。
國外的新思想、新潮流也時刻沖擊著英國的傳統意識。20世紀60年代,囊括象征主義、意識流、互文性等理論流派的后現代主義在西方世界迅速風靡。英國著名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戴維·洛奇曾說:“6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十年,……我第一次接觸了從歐洲大陸傳來的文學理論,它開創了整整一套有關小說寫作的后現代技巧和策略”[7]。后現代主義強調的文本互涉、文本開放性、反諷、組合、變體等特性與互文性特征契合,這些后現代技巧與策略極大地解放了包括溫特森在內的當代英國作家的小說創作。與此同時,美國后現代主義作家約翰·巴思、唐納德·巴塞爾姆、威廉·加斯等人的理論和文學作品開始在英國文學界發生化學反應,這些作家作品中運用的互文性策略和反諷、戲擬、元小說等創作手法對英國作家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溫特森的小說創作正是始于這一時期,她的大多數小說作品采用的時空交錯、意識流、開放式結尾等表達方式和戲擬、引用、改寫等創作手法明顯是受到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和美國后現代作家作品的影響。
當代英國小說界的創作風氣也對溫特森小說互文性特征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英國當代很多小說家都接受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洗禮,多傾心于小說寫作風格和手法上的創新,其中不乏運用戲擬、改寫、暗指、反諷等互文性策略進行創作的作家。還有一種情況是,作家本人無意運用互文性策略進行寫作,但其作品卻表現出或隱或顯的互文性特征。這意味著,互文性已經成為英國當代小說家構思和寫作小說時不可或缺的法寶,難怪戴維·洛奇說:“互文性與英國小說的根源緊緊纏繞在一起,而且,在小說編年史另一頭的當代小說家傾向于利用——而非抗拒——互文性”[8]。的確,在英國當代文壇,互文性寫作可謂蔚然成風。這樣的互文創作風氣對溫特森自覺進行互文寫作或無意地使其小說呈現出互文性特征自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結語:
本論文從作家、讀者、社會三大層面梳理了珍妮特·溫特森的小說文本中呈現互文性特征的原因。從作家的角度探討,溫特森的人生經歷、“影響的焦慮”使她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將自身經歷與相關書籍投射到她的多部小說中去;從讀者或研究者的角度分析,讀者的誤讀和研究者的批評性閱讀都有可能將相關文本記憶融入到對當前文本的理解中,從而挖掘出溫特森各部小說的若干互文關系;從社會的層面講,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兼容并包思想和互文創作風氣也對溫特森小說的互文性特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李乃清.溫特森“危險”女作家[J].南方人物周刊,2011(32):87-88.
[2][美]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M].徐文博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45.
[3][英]奧黛麗·拜爾格.寫作就是高空走鋼絲——珍妮特·溫特森訪談[J].蒲火譯.延河,2016(5):89,99.
[4]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6. p.11.
[5][美]哈羅德·布魯姆.誤讀圖示[J].轉引自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J].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316-317.
[6][法]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M].邵煒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81.
[7][英]杰西·扎內威茨.戴維·洛奇訪談錄[J].丁兆國編譯.外國文學動態,2003(5):18.
[8][英]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M].盧麗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