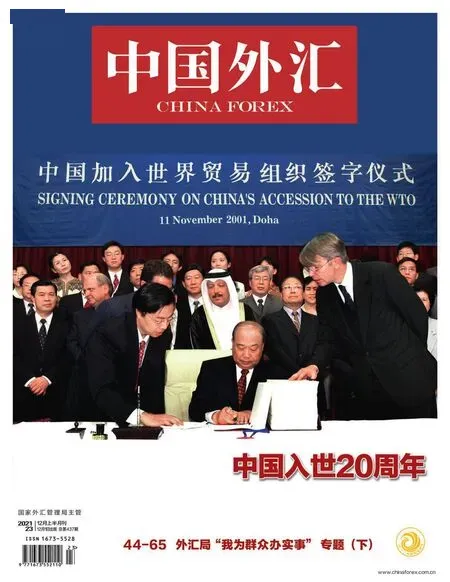全球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情況的統計分析
文/田園 編輯/張美思
2021年7月1日,世界銀行公布了2020年高收入至低收入水平的門檻和大部分國家(地區)的人均國民收入。當前我國正處于從中高收入邁向高收入水平的關鍵時期。梳理1987年以來全球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情況,可以為我國提供一定的經驗與借鑒。
世界銀行逐年動態調整國家分類標準
1989年世界銀行公布現行國家分類標準,對1987年的各國人均國民收入(世界銀行用Atlas方法計算)進行了劃分:480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水平,481美元至1940美元之間的為中低收入水平,1941美元至6000美元之間的為中高收入水平,高于6000美元的為高收入水平。為保持標準的穩定性和一致性,世界銀行在1987年的基礎上根據通脹水平進行了動態調整,并逐年公布各收入水平的門檻值。1994年開始,世界銀行開始使用特別提款權(SDR)平減指數代表世界通脹水平。SDR平減指數是依據SDR籃子貨幣所占權重及其對美元匯率,對SDR籃子貨幣發行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平減指數進行加權得到的。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后,中國因素也在SDR平減指數中體現。
世界銀行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人均國民收入在1045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水平,1046美元至4095美元之間的為中低收入水平,4096美元至12695美元之間的為中高收入水平,12696美元及以上的為高收入水平(見圖1)。

圖1 1987年以來各收入水平門檻變化
各國經濟發展中的中等收入階段尤其值得關注
2007年,世界銀行基于客觀現實,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認為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增長放緩乃至停滯的風險要比其他階段大,從而導致趕超放慢甚至倒退。站在一國的角度,“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時間過長或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大多數文獻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確實存在,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速下滑與內生動力不足。
世界銀行公布現行分類標準以來,1987年時不是高收入水平、經過發展達到高收入水平且保持相對穩定的國家(地區)共有28個。以人口規模劃分,人口超過1000萬的大國只有6個,分別是歐洲的葡萄牙、希臘、捷克和波蘭,以及亞洲的韓國和南美洲的智利;其中只有韓國的人口超過5000萬。以是否發生過階段性倒退劃分,9個國家(地區)曾出現過達到高收入水平后,短暫回到中等收入階段的階段性倒退,大多數是受危機拖累,如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匈牙利、克羅地亞和拉脫維亞在歐債危機后,都發生過階段性倒退,后又重新升至高收入水平(見表1)。

表1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地區)
一度達到高收入水平后退回至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地區)有8個。除美屬薩摩亞群島(世界銀行不單獨公布美屬薩摩亞群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和赤道幾內亞(該國在1987年處于低收入水平,2007年達到高收入水平后,2015年跌回至中高收入水平并維持至今;其人口不足150萬,1996年在領海內發現了大量石油資源后,經濟快速增長,但是絕大多數石油收入被政府要員及執政集團掌握,因此該國國民總體經濟收入水平不高)外,俄羅斯、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都是在2015年退回至中等收入階段,至今仍未成功跨越。強勢美元周期下這些國家貨幣貶值是重要驅動因素。巴拿馬、毛里求斯和羅馬尼亞因經濟結構單一等自身因素疊加疫情沖擊,在2020年退回至中等收入階段(見表2、圖2)。

表2 退回至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地區)

圖2 阿根廷和俄羅斯實際匯率變動
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大部分是前蘇東國家。除小國、島國和資源型國家外,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克羅地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國家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選擇加入歐盟,實現了較快增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緊密的貨幣金融合作和歐元區提供的穩定匯率環境,是這些國家實現經濟跨越的重要保障。
結合上述各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經驗可以發現,匯率是聯結宏觀經濟和微觀主體的重要變量。宏觀層面,國家之間的經濟基本面強弱是決定匯率的基礎因素,長期匯率上升意味著該國經濟向好,是實現跨越的保障;下跌則與國內通脹相伴,吞噬經濟增長。微觀層面,短期過度波動將影響市場穩定,尤其是本幣升值通過貿易渠道惡化出口,反而拖累經濟增長。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通脹與發達國家差異大、名義匯率大起大落,尤其容易出現易跌難升、跌多升少的趨勢性特征,弱化了自身經濟增長的成果,阻礙了發展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