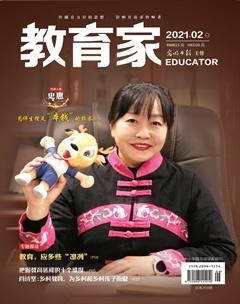肖詩堅:鄉(xiāng)村教育,為鄉(xiāng)村和鄉(xiāng)村孩子而做
周麗


2020年,肖詩堅出現(xiàn)在多個有影響力的教育論壇和訪談現(xiàn)場,分享她在貴州大山里踐行三年多的鄉(xiāng)村教育新模式——鄉(xiāng)土人本教育。她所創(chuàng)辦的田字格興隆實驗小學(xué)(以下簡稱“興隆小學(xué)”)被稱為“大山里的未來學(xué)校”。這種結(jié)合中國鄉(xiāng)村需要和鄉(xiāng)村兒童特點創(chuàng)建的教育模式,吸引了包括新東方創(chuàng)始人俞敏洪在內(nèi)的諸多教育人的到訪與關(guān)注。
鄉(xiāng)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對于鄉(xiāng)村學(xué)生而言什么是“好的教育”?肖詩堅在興隆小學(xué)發(fā)起的這場教育實驗,為推動鄉(xiāng)村教育振興及發(fā)展提供了一種新可能。
探尋鄉(xiāng)村教育的出路
肖詩堅是跨界教育人。在擔(dān)任興隆小學(xué)校長之前,她有著不凡的履歷:北京大學(xué)社會學(xué)系畢業(yè),曾就職于國務(wù)院農(nóng)研中心發(fā)展研究所。而后又留學(xué)丹麥,經(jīng)營跨國公司,在商業(yè)上有著卓著成就。生長于大城市的她與鄉(xiāng)村沒有天然的連接,但社會學(xué)的出身和農(nóng)研所的工作經(jīng)歷,讓她始終把“關(guān)心農(nóng)村、研究農(nóng)村”以及“投身公益事業(yè)”作為自己的擔(dān)當(dāng)與使命。
2010年,肖詩堅創(chuàng)立田字格助學(xué)公益機構(gòu),為貧困地區(qū)的孩子提供助學(xué)和支教服務(wù),并于2012年在貴州省威寧縣哈喇河鄉(xiāng)海拔2500米的大山中創(chuàng)辦了田字格第一所鄉(xiāng)村小學(xué)。歷時7年,田字格先后助力了1700余名農(nóng)村高中貧困生。然而,最終這些孩子“真正能考上大學(xué)的卻不足10%”。并且,跟蹤這些農(nóng)村孩子的“后大學(xué)時代”時,肖詩堅發(fā)現(xiàn),“很多娃的命運并沒有因上大學(xué)而改變,他們面臨就業(yè)難、在城市生存難的困境。而此時,他們對鄉(xiāng)土也沒了感情和依戀……”
感到“教育離鄉(xiāng)村孩子越來越遠,鄉(xiāng)村孩子也離教育越來越遠”的肖詩堅不禁思考:鄉(xiāng)村教育到底是為誰而做?
在肖詩堅看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們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基于城市的人才需求進行選拔,從培養(yǎng)目標、教材、考試、教學(xué)內(nèi)容到學(xué)習(xí)方法等,無不是從城市出發(fā),嚴重忽略了鄉(xiāng)村兒童的需要。
“中國有9000多萬鄉(xiāng)村兒童,他們是不是基礎(chǔ)教育、鄉(xiāng)村教育最重要的服務(wù)對象?關(guān)心他們的生命,關(guān)心他們生命的價值、存在的價值、未來成長的道路,這是不是我們應(yīng)該去思考的?”
反思田字格多年的支教實踐,肖詩堅不得不告訴自己:支教只是給“奄奄一息”的農(nóng)村教育補充了點維生素,沒有改變問題的根本。
鄉(xiāng)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2016年的一場公益年會給了肖詩堅啟發(fā):鄉(xiāng)村教育應(yīng)該扎根在鄉(xiāng)村,需要在鄉(xiāng)土之中孕育而生,而不是簡單地從城市移植。“鄉(xiāng)村教育的出路在于是否能夠創(chuàng)造并擁有專屬于農(nóng)村的教育,屬于鄉(xiāng)村孩子的教育。”
2017年2月,田字格與正安縣教育局簽署協(xié)議,接手興隆小學(xué)。次月,肖詩堅“拋家舍業(yè)”、放棄上海的優(yōu)越生活,帶領(lǐng)田字格的6名成員移師這所僅剩70多名學(xué)生的村小,一頭扎進了鄉(xiāng)村教育改革的試驗田。
籌備階段,肖詩堅和團隊用時半年,出國學(xué)習(xí),請名師指導(dǎo),深入村莊,走進課堂,在不斷的實踐和修正中,逐步創(chuàng)造出一套“屬于農(nóng)村、屬于孩子”的教育理念和課程體系——鄉(xiāng)土人本教育,志在培養(yǎng)“立足鄉(xiāng)土,敬愛自然,回歸人本,走向未來”的新一代鄉(xiāng)村子弟。
喚醒“不一樣”的鄉(xiāng)村孩子
“村長,什么是高科技?”
“為什么我們村叫興隆村啊?”
“為什么是村長開會?”
“村里有多少人家?”
“村里有多少垃圾桶?”
“村里的水電哪里來啊?如果沒有水電的話,需要找誰?”
“村里的垃圾都是怎么處理的?”
……
這是一堂鄉(xiāng)土課上一、二年級的孩子們?nèi)ゴ逦瘯柕膯栴}。
鄉(xiāng)土課是興隆小學(xué)“5+1”課程體系中的“軸心課”之一。在興隆小學(xué),師生們以天地為課堂、以萬物為師,充分利用鄉(xiāng)村和自然的優(yōu)勢,讓身邊的一切——五谷蔬菜、節(jié)日節(jié)氣、山川河流、民俗風(fēng)情、家族祠堂,都成為孩子們的教學(xué)資源。
鄉(xiāng)土課以主題式教學(xué)形式開展,每學(xué)期一個主題,融合了語文、科學(xué)、美術(shù)、音樂、自然及民俗文化等學(xué)科內(nèi)容,“只要是適合孩子們認知發(fā)展的都會放進去”。擔(dān)綱鄉(xiāng)土課教學(xué)和課程開發(fā)的孔美介紹,三年來,興隆小學(xué)高中低年級分別開展了“大山夢工廠”“興隆植物樂園”“興隆的飛禽走獸”“興隆留守人”“興隆二十四節(jié)氣”“大山·家”等多個主題學(xué)習(xí)及活動。孩子們走進村莊內(nèi)外,去茶園農(nóng)場、百草園勞作;去縣城博物館研學(xué);去聽風(fēng)聽雨、觀察動植物;去采訪留守的老人、村委會的干部……教學(xué)形式也多種多樣:小組合作、自主探究、戶外教學(xué)、表演、分享、混齡……這些通常在城市學(xué)校里才能見到的先進教學(xué)方式,興隆小學(xué)的孩子們早已熟稔并樂在其中。
生命課是興隆小學(xué)的另一大“軸心課”。
2020年12月25日,一場生命課答辯會在興隆小學(xué)立人堂舉行。這一學(xué)期的生命課在五、六年級開展,17名學(xué)生參與。學(xué)期初,孩子們發(fā)散思維,羅列了數(shù)十個想要探究的生命問題。經(jīng)過反復(fù)篩選,自主選擇,最終形成了5個課題小組:“植物為什么會變色”“動物為什么會變性”“兔子是怎么來的”“氧氣消失5秒,地球?qū)鯓印薄巴列l(wèi)二上有沒有生命”。研究過程中,孩子們自主查閱書籍、搜索網(wǎng)絡(luò)、寫報告、做PPT,有的還做實驗。最終,每個小組都提交了一份一兩千字條理清晰的論文,并面向全校完成了答辯展示。
除了軸心課外,興隆小學(xué)的“5+1”課程還包括語文、數(shù)學(xué)、英語等國家基礎(chǔ)課,晨誦、晨禮、暮省等日修課,公共事務(wù)、校園經(jīng)營、農(nóng)耕課等共同生活課,以及木工坊、手工坊等自主修習(xí)課。
不過,在肖詩堅看來,興隆小學(xué)之所以能打動很多人,不在于豐富多彩的課程和新穎的教學(xué)方式,而源于一種獨屬于興隆的文化——“這種文化就是共同學(xué)習(xí)、共同生活、共同勞動的文化”。
在興隆小學(xué),處處體現(xiàn)著“共建、共享、共治”:百草園的戶外教學(xué)體驗區(qū),由教師、學(xué)生、家長共同施工搭建;開心農(nóng)場里的蔬菜,均由孩子們參與栽種、打理并在收獲后出售給學(xué)校教師;手工作坊的商品也都是學(xué)生創(chuàng)作及經(jīng)營,收入所得支付學(xué)生合理的“工資”,利潤則用于學(xué)校建設(shè)和研學(xué)活動……
興隆小學(xué)的學(xué)生有三分之二是留守兒童,其中還有三分之一來自破碎家庭。與想象中留守兒童的內(nèi)斂、拘謹不同,孩子們大方、自信、活潑開朗、熱愛鄉(xiāng)土,這是來此訪問學(xué)習(xí)的人普遍的感受。
在鄉(xiāng)土人本教育的滋養(yǎng)下,興隆學(xué)子呈現(xiàn)出了“不一樣”的生命狀態(tài)——
“蝴蝶的家在葉子里/地球的家在空中/我的家在閉眼中”——這首詩的作者阿福,剛?cè)雽W(xué)時是個令人頭疼、“上課都要拉著他的手,否則會跑掉”的淘小子。三年下來,如今的阿福會積極舉手回答問題、熱心幫助他人,并且是班上英語學(xué)得最好的,還是肖詩堅和許多老師眼里的小詩人。
曾對學(xué)習(xí)興趣缺缺的小艷子,在三年的鄉(xiāng)土課里變得陽光、自信,升入了縣城初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班上“唯一從農(nóng)村來的”。
有來訪嘉賓問孩子們“未來想做什么”,一個五年級男生堅定地回答:“我希望考上大學(xué),然后回來,把家鄉(xiāng)和學(xué)校建設(shè)得更美麗。”
……
“雖千萬人吾往矣”
孩子們身上散發(fā)的種種希望和美好,讓肖詩堅欣喜著、感動著。但這場創(chuàng)新教育試驗所面臨的困難不會被感動消融——肖詩堅“缺經(jīng)費”“缺老師”“缺生源”。
目前興隆小學(xué)加幼兒班共7個年級,教學(xué)團隊15人,其中6位是地方編制教師,其余為田字格招募的志愿者。田字格的教師和專職人員的薪資、課程體系建設(shè)等經(jīng)費主要來源于機構(gòu)募款。想方設(shè)法為學(xué)校“輸血”“造血”成了肖詩堅和團隊的一大工作。
相對于資金而言,田字格更缺教師。肖詩堅坦言,由于鄉(xiāng)土人本教育理念及教學(xué)方法新穎,對教師的要求較高,一些習(xí)慣了傳統(tǒng)教法的地方教師對田字格倡導(dǎo)的教學(xué)形式并非十分篤定。學(xué)校語數(shù)之外的課程,主要靠田字格教師支撐教學(xué)。而田字格對于志愿支教的要求是三年起。同時,隨著鄉(xiāng)土人本教育進入對外推廣期,田字格對執(zhí)教和課程開發(fā)人員的要求也提高了——招聘的教師必須有兩年的教學(xué)經(jīng)驗。盡管田字格在不斷提高志愿教師的待遇,但這些“門檻”無疑還是讓絕大多數(shù)人望而卻步。
生源問題同樣擺在眼前。興隆小學(xué)現(xiàn)有的學(xué)生維持在田字格接手時的人數(shù),這主要得益于生源的回流——目前的71名學(xué)生中,有18名是從縣城和外省城市轉(zhuǎn)來的。但農(nóng)村生源日益萎縮的現(xiàn)實不容回避——眼下,本村、臨近村只剩下3名適齡兒童。肖詩堅表示,下一屆,學(xué)校或要向外鄉(xiāng)、縣城及外地招生。
中國鄉(xiāng)村教育的改革之路道阻且長,這場大山里的教育實驗意義何在?或許如田字格的教師田艷莉所說:“做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也正如俞敏洪與肖詩堅的問答:
“你覺得中國鄉(xiāng)村教育有出路嗎?”
“艱難,特別艱難。無論這條路的曙光在哪里,都需要有一些人知道,路就在腳下。”
肖詩堅依然抱定著最初的信念:“雖千萬人吾往矣。”
播種鄉(xiāng)村教育的希望
支教不是改變鄉(xiāng)村教育的根本之計,肖詩堅深知“鄉(xiāng)村教育最終還是要靠鄉(xiāng)村教師來改變”。
2020年秋,田字格聯(lián)合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正安縣教育局發(fā)起了“鄉(xiāng)土村小:農(nóng)村小學(xué)教育質(zhì)量提升計劃”,面向正安縣的村小推廣鄉(xiāng)土人本課程中的鄉(xiāng)土課及日修課,同時開展“種籽教師”培訓(xùn)。
“鄉(xiāng)土課最大的意義在于學(xué)生能夠再次去了解自己土生土長的家鄉(xiāng),了解家鄉(xiāng)本土的人情、地貌、特色、文化,學(xué)會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學(xué)會表達自己對家鄉(xiāng)的愛,增強與家鄉(xiāng)的情感連接。”新州鎮(zhèn)老城小學(xué)的年輕教師譚雙敏是“鄉(xiāng)土課”的先行試水者。從起初的茫然、無助、灰心,到現(xiàn)在有序、熟練開展鄉(xiāng)土課程,如今,鄉(xiāng)土課已成了老城小學(xué)學(xué)生最期待上的一門課。譚雙敏也從中體會到:“教師要學(xué)會發(fā)現(xiàn)學(xué)生身上的潛在點,懂得合理地激發(fā),讓學(xué)生知道自己身上的可能性。”
“鄉(xiāng)村教育更多看重的是應(yīng)試成績,忽略了孩子的全方面發(fā)展,鄉(xiāng)土課正好彌補了這一塊。”樂儉鄉(xiāng)金葉小學(xué)的鄭利利也是首批“種籽教師”中的一員。實施鄉(xiāng)土課一個學(xué)期,她欣喜地看到,一些在其他學(xué)科課上深受打擊的學(xué)生,在鄉(xiāng)土課上重獲了自信,煥發(fā)了新的生命光彩。此外,鄭利利還將鄉(xiāng)土課運用的教學(xué)方式遷移到了語文教學(xué)中,并希望帶動更多鄉(xiāng)村教師踐行這一教育理念和教學(xué)模式。
目前,“鄉(xiāng)土村小”項目已惠及20所村小的1800名孩子、近百名鄉(xiāng)村教師,并計劃于今年擴展到50所村小。肖詩堅相信,越來越多的“種籽教師”將成為鄉(xiāng)村教育的希望。
采訪后記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國的鄉(xiāng)村學(xué)校在不斷消失和凋敝,一些村莊已經(jīng)沒有了村小,保留下的村小也多在殘喘掙扎。國家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提出,要推動城鄉(xiāng)義務(wù)教育一體化發(fā)展,高度重視農(nóng)村義務(wù)教育,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zhì)量的教育。田字格致力打造和推廣的鄉(xiāng)村教育模式或許就是一條振興鄉(xiāng)村教育、振興鄉(xiāng)村的新路徑,因為這種模式不僅關(guān)注鄉(xiāng)村后代的培養(yǎng),更是為了讓這些后代能夠立足自己的鄉(xiāng)村,關(guān)心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甚至有朝一日可以回來建設(shè)家鄉(xiāng)。
與此同時,田字格也在探索鄉(xiāng)村教育更多的可能性。肖詩堅提到,興隆小學(xué)2021年的目標之一是建設(shè)“村莊里的學(xué)校”,他們擬通過面向城市兒童開展夏令營、擴大學(xué)校農(nóng)場綠色產(chǎn)品對外銷售等方式,加大城鄉(xiāng)交流,以學(xué)校和教育的力量進一步帶動村莊的發(fā)展和振興。
肖詩堅最后補充道:“探索鄉(xiāng)村教育新模式的意義,并不局限于教育創(chuàng)新本身,更重要的是,通過振興鄉(xiāng)村教育探索出一條振興鄉(xiāng)村之路。因為,保住村小才能保住鄉(xiāng)村及鄉(xiāng)村文化,而中國的鄉(xiāng)土文化才是中國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