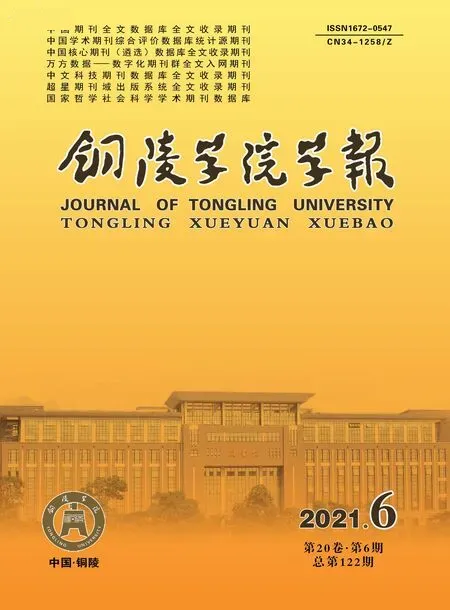銅陵古青銅器設計中的象征手法及其現代啟示
趙正光
(銅陵學院,安徽 銅陵 244061)
銅陵,位于江淮地區的皖西南部,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是我國重要的銅產地和銅文化發源地之一。銅,古稱“金”或“吉金”。銅陵在先秦時代聚集了淮夷和百越人,屬吳越文化,尤其是吳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銅陵至今的方言尚有一部分屬于吳語的分支。同樣的,銅陵出土的周代青銅器也有一些體現出了較為典型的吳越特征,隨著之后的勢力更迭,銅陵的青銅器呈現出更為多元的本土特點,在象征意義上也更為豐富,給予現代設計很多靈感和創意元素。
一、銅陵在銅文化歷史上的交通位置
銅陵處于古代銅產地的中點,本地出土的青銅器大多來自各個朝代的墓葬,也有在古礦冶遺址被發現的,數量不算太多但涉及禮器、食(水)器、兵器、樂器和農具等各個類別,造型獨特,工藝精美,帶有鮮明的地域色彩,文化內涵豐富。時代從商代開始,春秋戰國階段最多。造型紋樣上既有與北方青銅器皿相似的元素,又有南方銅器所特有的清秀風格,還有一些反映當時部族,國家文化特色的內容,面貌較為復雜,有兼收并蓄又獨具一格的特點。其形成原因可能與南北方的交流有關——當時著名的“東南索金”“印燮繁湯,金道錫行”,都顯示出北方中原諸國對南方小國的資源掠奪,在掠奪的同時又帶來了先進的冶煉技術,這才使得當地的青銅器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當然,這里筆者還忽視了一個問題,即銅是當時國家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不僅用于衣食住行,還代表著軍事力量,天子諸侯威儀等。周代的銅器“戎生編鐘”和“晉姜鼎”的銘文記載了在西東兩周朝代更迭交替之時,中原大國晉國曾派遣千乘大車到江淮地區換取“吉金”,湖北隨州的曾侯墓中出土的“曾伯漆簠”上的銘文也佐證了這一事件。在2000多年前千里跋涉,橫穿南北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由此可見銅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易德生先生在《周代南方的“金道錫行”試析——兼論青銅原料集散中心“繁湯”的形成》一文中提出了幾個很重要的概念:由于煉制青銅所需要的礦產大多集中在南方,因此北方大國對南方小國進行侵略,以掠奪或交換資源。其運輸線主要有兩條,一條途徑江漢地區,經湘水到岳陽,后到武漢黃陂,經麻城,繁湯而入中原;一條則途徑江淮地區,自江西始,順江至銅陵、南嶺,經六安到繁湯后入中原;或自銅陵過廬江后從合肥進入中原。易先生還提到了“郁永郴等對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的部分銅器進行了鉛同位素的檢測,他們認為,指證銅料的錫青銅鉛同位素數據,其與安徽銅陵、江西瑞昌、江西銅嶺和湖北大冶銅綠山的均有疊合”[1],我們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南方古礦區是如何向北方輸送原材料的。同時,結合以下幾個因素,筆者大膽地提出一個與易先生的論斷不相同的新設想:即古代的江南地區很有可能以開采原銅礦為主,煉制器具為輔,江西和安徽地區的銅礦沿著長江進入今天的湖北省境內,然后才流入中原諸國。中原諸國掌握著當時先進的青銅器鑄造技術,通過戰爭和文化、貿易等交流,又返回來影響了江南的鑄銅技術發展。之所以進行這樣的推測,原因有三:1.據銅陵市政府網站2020年公布的數據,“銅陵目前發現的青銅器……數量有100多件”,這對于一個自古以來就產銅的城市來說,并不算多。江西省博物館的官方數據顯示,在新干大洋州商代青銅器出土后,雖然顛覆了“青銅文化源于中原,江南地區沒有發達青銅文化”這一傳統觀點,但是也僅有475件藏品。而長江中游的湖北隨州博物館,據官方統計,有文物10,183件(套),其中青銅器占了絕大多數。更靠北的中原大省山西,具李夏廷先生的《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銅器縱覽》一書中所說,“傳世和流散境內外的晉地(制)青銅器數量很多,尤其是東周晉器,在……幾乎隨處可見,私家收藏更數不勝數。”“原太原市電解銅廠……當年原料多來自民間收購的廢銅,內含大量古代銅器和古錢幣……20年間從準備回爐冶煉的廢銅中挑選出……等數十噸銅器……,成為山西博物館系統藏品的一個重要來源”[2]。據官方數據,山西博物院擁有青銅器藏品2,200余件,鄰省的陜西歷史博物館青銅器藏品數量更是達到了驚人的3,900多件。南北方青銅器數量上的對比十分懸殊。2.銅陵出土的青銅器在形制、紋樣和鑄造工藝上看,各種鑒,匜,饕餮紋爵、饕餮紋斝以及獸面紋大鼎等,和北方的銅器風格基本一致。其中的饕餮紋爵、斝呈現出明顯的商代早期的風格,對研究商文化的南遷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參考山西省博物院藏商早期饕餮紋爵,1990年平陸前莊出土;山西博物院藏商代饕餮紋斝,1959年石樓出土)1991年出土于銅陵縣順安鎮的獸足弦紋甗,甗、鬲連體,中間沒有箅子,方形雙耳。甗口高腹深,腹部裝飾雨花弦紋,鬲為經典三柱足式,獸面紋飾足,與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甗形制相似,對商代文化疆域的界定有著重要支撐作用。3.銅陵地處長江沿岸,又長期隸屬于吳國。吳地水資源豐富,自古以來吳國人就更習慣水上交通。若是溯流而上,沿長江經湖北中轉,那么湖北長江沿岸城市大量出土青銅器就解釋得通了。
二、銅陵出土的代表性青銅器
那么銅陵出土的青銅器中是否存在迥異于中原、能夠表現出強烈地域特色的作品呢?答案是肯定的。1979年銅陵市鐘鳴鎮出土的西周龍柄盉,上部盆形敞口,頸部裝飾有一圈紋理,下部為經典的仿鬲式三足。鋬曲長,鋬頂端為一龍首狀。雙目圓睜,極具威儀。這件盉的高度和柄的長度接近,給人精致典雅,輕松活潑之感,一掃鼎,鬲之類的器具給人帶來的凝重壓迫之感,奠定了南方青銅器輕盈優雅的格調,是后世的茶壺、酒壺的雛形。而更早在銅陵火車站出土的鳥形紐蓋鼎,于平蓋上塑一鳥,與北方的蓋鼎動輒三只動物立于蓋上有著極大的不同,孤鳥獨立,更顯霸氣。另外在紋飾上,銅陵出土的青銅器也有明顯區別于中原銅器的特征,如分解或簡化竊曲紋,使用云雷紋作為主體裝飾,工藝呈現出精巧纖細的特點,繩紋、弦紋大量使用等。后世的陶瓷也延續了其中的某些特點。
銅陵在春秋中晚期處于吳楚交兵的腹地,因此在文化和藝術觀念上呈現出了多樣化的特征。在出土的春秋中晚期兵器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期風格的變化。比如早期銅劍延續吳劍風格,分為短劍,扉耳劍,有格扁莖劍等,不少器型類似吳王闔閭,夫差劍。后期則與楚器械相似,受楚文化影響較大,如銅劍扁莖無格,收血槽;銅戈長胡直內,狹長援,鋒端呈三角形等。史料記載,公元前516年,楚國再次伐吳,兩軍交戰于銅陵鵲岸,即今銅陵縣鵲頭山一帶。吳楚間不斷的戰爭雖然帶來了極大的破壞,但也從另一方面促成了南方銅器的融合,促進了南方特有風格的形成。
之后,漢設“銅官”,銅陵屬丹陽郡,出土過“丹陽銅鏡”。之后分屬宣城郡,淮南郡,南陵郡等。南唐時期“銅陵”作為地名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宋滅南唐之后直到清代,銅陵一直屬于池州府(路)。之后歸省直屬直至建國后建市,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代表性的器物。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銅陵市文管所征集的唐代銅熨斗。這是一款長柄的圓形熨斗,平底寬口,斗與柄連接的地方呈葵花形,類似葵花紋銅鏡,或者稍晚時出現的宋代葵形碗。風格上與中原或北方的呈現出不同特點,把南方銅器的精致秀美很好地展現了出來。另一件具有代表性的銅器是民國時期的四喜銅娃。兩個天真爛漫的銅娃系著肚兜,手持芭蕉扇與金元寶,呈現出木板年畫中嬰戲的歡樂祥和的氣氛。在作者的精美構思下,兩個娃娃從不同角度轉化成四個孩童,通過孩童的四肢連結,都給人以一種錯覺。即無論是上下左右,無論觀者從哪個角度觀賞,娃娃首尾相連構成了四個完整的戲耍孩童,類似于今天設計構成基礎課上理論的實踐版本,觀念十分超前,甚至有美麗的傳說與明代才子謝縉有關。四喜娃娃的前身為“四喜人”,“四喜”這一觀念則來自著名的“人生四喜”論斷,即“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據史書記載,在古代婚嫁禮俗中,“四喜人”被作為“喜神”供養,是人們祈禱平安喜樂的寄托,其在民間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漢族古代男子有在腰間佩玉的習慣,來象征一種對自己的期許或是一種祈禱性的裝飾,有祈福避災的作用。連《禮記》都記載過“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從側面印證了古人佩物之風的盛行。那么到了宋代以后,隨著瓷器和銅器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具有玉雕特性的陶瓷掛件,銅掛件。當時的玉器十分貴重,有時甚至象征階級,瓷器和銅器雖然在起因上都是為了模仿玉器的某些特性(外形,光澤度,質感……),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瓷器和銅器,玉器互相影響,逐漸形成了有自身藝術特色、風貌的藝術作品。人們的配飾品種也開始逐漸增多,到了清代民國,各種材質的新奇配飾層出不窮,四喜銅娃原本就是配飾的一種。原作娃娃肌體豐滿,活潑可愛,又結合銅工藝品的特色,皮膚質感表現得尤為出色,反映出當時工匠高超的智慧和技藝。
三、銅陵古代地方特色銅器的象征手法對現代設計啟發
銅陵古代地方特色青銅器代表了當時南方青銅器的發展水平和風格,而其中蘊含的象征意義,則是最寶貴的財富。眾所周知,古代中國有著自成一家的象征系統,如牡丹,喜鵲,仙桃,花瓶,蝙蝠等。同時,不同象征元素的疊加,也能衍生出新的含義,如馬上騎著猴子(馬上封侯),蝙蝠和銅錢(福在眼前),蜘蛛和人的腳(知足常樂)等……這些象征元素與對應的意義,在今天看來,都或多或少與語言的諧音有關。而其實中華民族最早對象征元素的使用,是在陶器、文字和青銅器中。遠古人類在陶器上畫抽象的幾何圖案來表現心中所想,之后在動物的骨骼和龜甲上刻畫已經形成體系與共識的文字(甲骨文),隨后這兩種象征手法被一起運用到了青銅器上面,不但形成了新的文字風格(金文),也使得抽象的幾何紋樣變得更加豐富多樣和立體化,甚至出現了寫實的傾向。象征手法可以借助事物之間的某種聯系,借助象征體(具體的人或物),來表現出某種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可以使藝術作品展現出高于表象的深層意義,同時也可以給藝術家、設計師以新的靈感和啟發。在我國藝術史上有許多經典圖像包含著象征手法,比如八卦,五行等,利用最樸素的圖案組合來推演世間萬物的變化,是古人天人觀的一種體現。而在藝術品,尤其是銅陵本土青銅藝術品分析中,筆者把象征的意義分為三類:(1)青銅紋飾組合的象征意義;(2)青銅器形態的象征意義;(3)銅器中文字的象征意義。同時,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也延伸出這些象征意義、手法的使用對于現代藝術作品的啟發。
(一)青銅紋飾組合的象征意義及現代價值
在銅陵本地出土的青銅器中,包含有很多的紋飾。其中最主要的是饕餮紋,云雷紋,竊取紋,夔龍紋,鳳鳥紋等等[3]。其中的饕餮紋樣式與中原銅器相似,具有普遍性特征,利用猛獸的抽象連續形態,展現出一種神秘的威力和獰厲的美。而云雷紋則是古人對自然的領悟,結合各地收藏,發現有拍印、壓印、刻劃、彩繪等表現技法,通常以四方連續或二方連續式呈現。它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上。到了商周時代,云雷紋被大量使用在青銅器上,但是大多數時候作為地紋的襯托。而銅陵在出土的一些器皿上,云雷紋居然被用作主體裝飾。這是對紋飾主次關系的一種新的藝術探索。而在國寶級的竊取紋大鐃中,竊取紋局部被分解或簡化,中間間以乳釘,也呈現出迥異于中原銅器的新面貌。這又是對紋飾組合排列的新創意。這些新的理念在今天“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顯得格外珍貴。藝術品分析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挖掘其變化的規律及想法,這樣方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國家博物館的文創在這兩年取得了大眾的認可,原因就在于借鑒了古代藝術品變化的某些規律。比如,就紋飾而言,從上古時代到今天,其中變化不知凡幾,但是很多紋飾之間的搭配、主次關系一直在被沿用。而國博文創推出了一款貼紙(見圖1),把歷代的各種物件上的紋樣印于其上。在消費者的實際使用過程中,可以被剪裁,拼貼,隨意搭配,把以往很多不可能并置在一起的紋樣組合在一起,產生了新的視覺效果和表現力并帶動了潮流,各大博物館紛紛效仿,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國博文創一炮而紅,為之后的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這一切,其實就是源自對古代藝術演變概念的思考。不同地域同一藝術種類的演變規律,是現代設計的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

圖1 國博青銅紋樣文創貼紙
(二)青銅器形態的象征手法表現及其現代價值
青銅器的形態特征和紋飾元素一樣,都源于古人對世間萬物的領悟與概括。以銅陵出土的龍柄盉為例。盉是古代漢族調酒的器皿,通過它來調節酒的濃淡。其形狀多樣,通常來說具有圓口,深腹,前流后鋬的特點,有時為三足,有時為四足,皆為模仿動物形態,以期引起觀者不一樣的心理體驗(三足為胖鳥,四足為野獸,前者憨厚,后者威猛)。青銅盉出現在商早期,一直延續到春秋戰國。起先器型敦厚凝重,紋飾威嚴神秘,僅為貴族使用。隨著時代的變化,之前的莊重與沉悶被輕松與典雅替代,呈現出平民化的趨勢。秦漢之后,盉變化為尋常的酒器,茶器為普通百姓日常使用,圖2的前三幅圖呈現了到20世紀為止盉的一些變化,最后一幅圖則是現代設計師按照盉的形態象征進行的家居擺件設計。設計師模仿盉的三足著地,但把抽象的足演變為具體的,肌肉飽滿的腿。同時,古代盉的龍柄在歷史演變過程中也逐漸抽象化,龍的概念被手柄的實用功能所替代。在這件現代作品中,設計師又用手替換了手柄,但依然模擬出了原始盉的造型氣質,是現代設計對古代青銅器形態象征意義的一次好的探索。

圖2 盉的演變
(三)銅器中文字的象征意義及現代創意展現
在銅陵出土的青銅鼎中,有一些帶有神秘,模糊文字的,今人已難以辨識,讓人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想解讀、了解歷史的真相而不可得。當代藝術家徐冰就這一文化隔膜問題進行了實驗性創作。在作品中,它賦予漢字的部首、偏旁以獨立的意義,通過重新組合“創造”了一些“新的漢字”。這些字在我們看來無疑是熟悉的,但仔細端詳,卻又無一識得。這種熟悉的陌生感與我們在觀看青銅器銘文時遇到的情況如出一轍。這件作品被命名為《天書》,最后以一種讓人震撼的、“布坊”式的形式展現。既突出了作品的美感,又增加了神秘的氣氛,烘托出了主題“文化隔膜”。

圖3 徐冰《天書》

圖4 《天書》展覽現場
四、小結
在銅陵的悠久歷史中,能帶給我們現代啟示的資源十分豐富。而隨著未來考古工作的推進,可能還會出現更多。作為當代的藝術家、設計師,應當善于從祖先的遺產中汲取靈感,從不同的側面,結合自身的知識與現代科技,進行大膽地實驗與創新。只有這樣,文物的意義才能真正地體現出來并福澤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