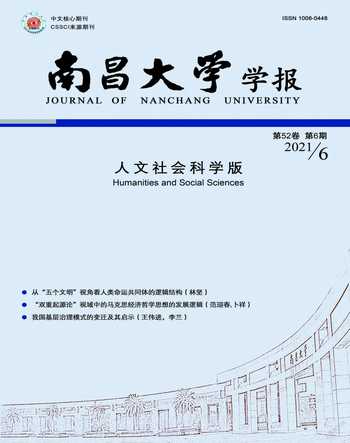論“半費之訟”的法律本質
劉劍凌
摘 要:“半費之訟”本質上是法律問題而非邏輯問題。在辯論中,師徒二人預設了法官應對判決后可能引發的新案進行裁決,這違反了不告不理原則。根據不告不理原則,法官的審判職權只存在于審判過程中,判決后審判職權自然終止。因此,“半費之訟”的法官在判決后對可能由此引發的新案無權裁決。師徒二人的預設錯誤是“半費之訟”問題產生的根源。運用不告不理原則,以是否起訴為時間節點,可以將訴訟與民事糾紛、法官與非法官、法官職權與法官職業明確區分開來,從而將師徒二人的二難推理合法而自然地攔腰切斷,“半費之訟”也就可以得到徹底解決。
關鍵詞:“半費之訟”;不告不理;二難推理;預設;前提分析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448(2021)06-0065-08
一、問題的緣起
2 400多年前,古希臘有一名哲學家叫普羅泰哥拉,他是智者派的開創者和代表人物,以傳授辯論術和演講術為生。有一次,他招收了一名學生歐提勒士(一說愛瓦梯爾),教他法律和辯論術。事先,二人簽訂了一份合同,規定歐提勒士先支付普羅泰哥拉一半學費,另一半則等歐提勒士畢業之后第一次出庭幫人打官司并且勝訴之后再付;如果第一場官司歐提勒士打輸了,則證明普羅泰哥拉教學無方,另一半學費就可以不交。
但歐提勒士畢業之后并不幫人打官司,也不交另一半學費,普羅泰哥拉終于等得不耐煩了,于是向法庭起訴。雙方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展開了激烈辯論。普羅泰哥拉說:
“如果這場官司我打贏了,那么按照法庭判決,你應該付給我另一半學費;如果我打輸了,那么按照合同規定,你也應該付給我另一半學費。這場官司我或者打贏,或者打輸,總之,你都得付給我另一半學費。”
孰料,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歐提勒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反駁道:“如果我打贏了這場官司,那么按照法庭判決,我不必付給你另一半學費;如果我打輸了,那么按照合同規定,我也不必付給你另一半學費。這場官司我或者打贏,或者打輸,但不管是贏還是輸,我都不必付給你另一半學費。”
傳說這場官司當場難倒了法官,這就是法學史、哲學史和邏輯史上著名的“半費之訟”。
關于“半費之訟”的真實性,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萊布尼茨也曾在《法學中疑難案件的研究》中討論過;羅素則在其《西方哲學史》中認為這個故事是杜撰[1](P10)。還有一些難以考查來源的說法,如有說是師徒二人的“苦肉計”,目的是推廣他們發明的“二難推理”。對于“半費之訟”的真實性,我們無法考證和確定,所以,我們的態度是假定其為真,把它當作一個真問題來處理。
至于“半費之訟”應當如何解決,歷來方案眾多,莫衷一是。通過對已有解決方案的分析,我們認為,要解決“半費之訟”,首先必須澄清幾個關于“半費之訟”的元問題:1.何謂“半費之訟”之解?2.“半費之訟”的性質是什么?3.“半費之訟”是否為合同規定意義下的第一場官司?4.“半費之訟”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么?只有徹底澄清這些問題,“半費之訟”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
二、何謂“‘半費之訟’之解”
古往今來,想解決“半費之訟”的人不計其數,但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人深入探討過何謂“‘半費之訟’之解”。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看到,因為沒有明確“‘半費之訟’之解”的確切含義,許多人的解決方案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因此在解決“半費之訟”之前,首先明確“‘半費之訟’之解”的確切含義是必要且重要的。
最常見的一種觀點是,解決“半費之訟”,就是(幫)老師拿到另一半學費。于是他們的解決辦法是促成合同條件的成就。方案之一是老師先敗訴,之后再起訴;方案之二是老師構造一件虛假的“悖反”訴訟[1](P14)。這樣就符合合同規定,老師可以拿到另一半學費,“半費之訟”也就“完美”地解決了。
這種觀點顯然是把自己代入老師的角色,或站在老師的立場。但我們要問:“你為什么要站在老師的立場?為什么老師必須拿到另一半學費才算‘半費之訟’的解決?”原因似乎是出于一種“樸素”的正義感;即既然老師付出了勞動,就應當獲得報酬,否則對老師不公平[1](P14)[2](P16-17)。
但是,這種觀點不能成立。
第一,古希臘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即商業發達,加之當時民主制度興盛,年輕人要想出人頭地,就必須學習法律、演講術和雄辯術,由此催生了專門教授此類技藝的職業教師——智者。普羅泰哥拉便是代表人物,以此為生。為了顯示自己的強大實力,招攬更多學生,他自愿在學生學成并有所成就之后再收取另一半學費,這本質上是一種商業營銷術,與現在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的營銷術并無二致。我們不能接受一個天價保過班的學員在沒有通過考試時要求培訓機構返還學費,而培訓機構以“我們付出了勞動”為由拒不退還。同理,老師作出了類似承諾,這是老師為了賺錢而甘冒風險、自由處分自己權利的行為,是合法有效的,事與愿違自然自己承擔后果,所以不存在對老師的不公。用康德的話說,老師理性、自由地做出自己的選擇,如果你不尊重他的選擇,那是你對他的理性、自由、權利和獨立人格的不尊重。此外,我們還可以推測,既然老師可以對歐提勒士進行“半費”營銷,那他之前或之后是否也對其他學員進行過“半費”(或其他)營銷并從中獲利?以其職業論,這顯然是可能的。如此,更不存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那么老師就沒有道義上的優越地位。
我們認為古今商業營銷術并無本質區別。
第二,古希臘實行彈劾式訴訟制度,原告與被告雙方地位平等[3](P17)。老師與學生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加之老師并無道義上的優越地位;因此,既然認為老師拿到另一半學費才算“半費之訟”的解決,那么人們自然也可以說學生不交另一半學費也是“半費之訟”的解決。但顯然兩者相互矛盾,一個蘊含矛盾的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
第三,這種方案假定了法官與老師的一致。這有可能但不必然,因為法官和原告有各自的立場和目標,法官的立場是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其目標是實現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告的立場和目標是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兩者并不必然一致。對老師而言,無論他有何種訴求,其最終實現都必須經由法官認可;如果法官不認可,其訴求就不能實現。
第四,這種解決方案顯然默認了本案為合同規定意義下的第一場官司,而默認是合同規定意義下的第一場官司則又默認了“幫人”包括學生本人,但“幫人”是否包括學生本人歷來是本案爭議的焦點,未論證或未充分論證即直接采用顯然缺失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礎。
第五,這種方案明顯是在改題。本案已經歷起訴、受理、審理環節,下一環節是法官判決,原告與被告所能做的只是等待判決,已無其他操作空間,這是本案的“既定事實”。而這種方案不顧這一“既定事實”,想時光倒流回到案發前,“先知先覺”地“預料”到法庭上的僵局,并提出應對之策,這是在改題,他們所解決的已不再是“半費之訟”,至多算是從中總結的經驗教訓。
有少數人站在學生的立場來解決“半費之訟”,方案是學生主動輸掉官司,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理由同上第二、三、四、五條。
另一種“半費之訟”的解決框架是陳波提出的。他說:“假如你是法官,這師徒倆的官司打到你面前來了,你怎么去裁決這場官司?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假如你是一位邏輯學家,你又怎么分析這師徒倆的推理?它們都成立或都不成立嗎?為什么?這是一個邏輯問題。”[4](P11)
顯然,對“半費之訟”的解決,陳波作出了法律與邏輯的區分,這種區分看似自然,實則沒有準確把握“半費之訟”的本質。
第一,作出這種區分的依據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因為本案涉及法律和邏輯,所以就要作出法律與邏輯的區分?作者沒有解釋依據,或許在他看來這屬顯然。至于目的,是想徹底解決“半費之訟”還是想從理論上徹底說清“半費之訟”?似乎是后者。如果是后者,那應屬于對“半費之訟”的研究。研究不同于解決,解決是解決問題本身,而研究的范圍可以更加寬廣,可以超出問題本身,比如從中獲得啟示,總結經驗教訓或產生其他意外發明、發現等。實際上,對許多問題的研究,其意外收獲要遠大于問題本身的解決。但對于“半費之訟”,我們最關心的是問題的解決。
第二,這種觀點預設了法律與邏輯的對立或分離,好像法官判案可以不需要邏輯似的。但事實是,法官審理案件是以事實、法律為依據,以邏輯為工具,邏輯是法律必備的工具,邏輯可以沒有法律,但法律一定需要邏輯。在本案中,如果法官判決,他必須說理,說理的核心是對師徒二人的二難推理作出合理解釋,這需要邏輯。所以,將二者對立或分離的觀點并沒有正確理解法律與邏輯的關系。
綜上,我們否定了原告立場、被告立場和一般研究者立場,因此從邏輯上講,“半費之訟”的解決必須而且只能是法官立場。所謂法官立場,就是法官作出合法(合理)判決,這就是“‘半費之訟’之解”的確切含義。具體理由是:
第一,從法官的作用來看,法官是由國家授權,專職司法的人員,其作用是息訴止爭,因此,法官有權力并有責任對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裁決。既然普羅泰哥拉已經向法庭起訴,那就表明他期望法官對他與歐提勒士的糾紛作出誰是誰非的裁決,因此,法官擁有對本案的裁決權。
第二,無論原告與被告的訴求是什么,都只能經由法官的判決才可能實現。因此,法官在整個案件中處于裁決者的主導地位,“半費之訟”的真正解決自然系于法官。
但是,本案已過去2 400多年,審理法官早已不在,所以對我們后世的研究者而言,所謂解決“半費之訟”,就是將自己代入古希臘法官的角色對本案進行裁決。這是一種特殊的后世研究者立場。
明確了“‘半費之訟’之解”的確切含義也為我們澄清“半費之訟”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半費之訟”的性質——指明了方向。
三、“半費之訟”的法律本質
“半費之訟”的性質到底是什么?我們也沒看到有人進行過深入研究,大多數人認為是邏輯問題或主要是邏輯問題,少數人認為是法律問題或主要是法律問題,但人們幾乎都沒有進行充分論證,或許他們認為此屬顯然。所以實際上,這個問題長期處于研究盲區。但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直接決定了“半費之訟”的解決方向:認為“半費之訟”是邏輯問題或主要是邏輯問題的觀點,會把重心放在邏輯上;認為“半費之訟”是法律問題或主要是法律問題的觀點,會把重心放在法律上。因此,我們認為,對“半費之訟”準確定性并充分論證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半費之訟”的性質究竟是什么?我們認為,“半費之訟”本質上是法律問題。
從邏輯上來講,因為“半費之訟”只涉及邏輯和法律,所以“半費之訟”的性質只有四種可能:1.邏輯問題;2.法律問題;3.既是邏輯問題又是法律問題;4.既不是邏輯問題也不是法律問題顯然不可能,排除。
又可細分為以邏輯為主和以法律為主。
(一)“半費之訟”邏輯上沒有問題
認為“半費之訟”是邏輯問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三種:1.邏輯悖論說;2.混淆概念說;3.違背同一律說。我們認為,這三種觀點都不能成立。
1.邏輯悖論說不能成立
這種觀點認為,“半費之訟”具有悖論的基本特征:(1)老師和學生的論證都符合邏輯,但結論卻相互矛盾;(2)“半費之訟”存在自指,一是“幫人”包括學生本人,二是“半費之訟”的判決要以“半費之訟”本身的判決為依據,這就陷入了矛盾循環,所以導致了悖論的產生[5](P5)[6](P48)。對此,我們不能同意。
第一,這種觀點是單純從邏輯角度分析問題,他們可能不了解法律對邏輯的應用是有取舍的,某些法律原則會將邏輯規則和推理鏈條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如法律因果關系對邏輯和哲學因果關系的限制),“‘半費之訟’的判決要以‘半費之訟’本身的判決為依據”的錯誤即源于此。
第二,老師和學生的論證雖形式正確,但卻不合法律,所以都是錯誤的。詳見下文。
第三,“幫人”是否包括學生本人歷來是本案爭議的焦點,這種觀點直接認為包括學生本人卻無充分論證,其重要前提和基礎缺失。
第四,“半費之訟”可以解決是對此類觀點的最好反駁。
2.混淆概念說不能成立
這種觀點認為,普羅泰哥拉把合同中“歐提勒士畢業之后第一次出庭幫人打官司”中的“幫人”偷換成了包括歐提勒士本人在內的任何人,但合同的“本意”是不包括歐提勒士本人的。這種觀點也經不起推敲。
第一,這種觀點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幫人”不包括歐提勒士本人是合同“本意”,這可能是以后世的認知去揣度當時的認知。
第二,即使現在,許多合同在訂立之初也不能預料之后某些條款會有多種解釋,所以“本意”也有難以確定之時。
第三,“本意”說也可能源于對“幫人”的日常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說“幫孩子穿衣服”,但不能說“幫自己穿衣服”;可以說“幫老人過馬路”,但不能說“幫自己過馬路”……這些說法當然正確,但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外,一則英文中有“help yourself”(當然,英文不是希臘文)的說法,二則在日常語言中也有“幫人就是幫自己”“我是在幫我自己”的說法。所以,“本意”說雖然有理,但不必然。
具體到本案,我們認為,“幫人”可以包括學生本人,理由如下:
只需論證到“可以”,而不是也不能是“必然”,否則任何一個案件學生既是代理人又“必然”是當事人。如學生幫蘇格拉底打官司,學生“必然”和蘇格拉底一起成為被告,這是荒謬的。
第一,先例。
(1)公元前6世紀克里特島的厄匹門德說“所有克里特島人都是說謊者”,這就是說謊者悖論;
(2)智者派的先驅,早于普羅泰哥拉的高爾吉亞說過“一切知識都是虛假的”。
這些例子說明,在本案發生之前,古希臘語言中就已經存在自指現象,而當時(實際上直到現在)人們對這種現象感到迷惑,并未斷然將其從語言中清除出去,所以本案中將“幫人”理解為包括學生本人并非不可。
第二,從概念外延來看。
(3)歐提勒士是人,所以,人的概念的外延包括歐提勒士本人。
我們承認以上三條理由很弱,但其至少可以證明包括學生本人的可能性。
第三,核心理由,從“半費之訟”本身來看。
(4)老師這樣使用并且沒有反對學生這樣使用;
(5)學生這樣使用并且沒有反對老師這樣使用;
(6)法官沒有反對師徒二人這樣使用。
根據古希臘所采用的彈劾式訴訟的審理規則,法官不收集證據,只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進行比較、判斷;所以,既然原告與被告雙方都認為“幫人”包括學生本人且對對方如此使用并無異議,那么法官就有權加以確認。
即便學生是以歸謬法同理反駁,可能并非學生真實意思表示,但法官沒有義務猜測當事人心理,可直接以當事人意思表示為準。
這是我們認為“幫人”可以包括學生本人的核心理由,因為它直接來源于案件本身,沒有任何猜測成分,自然比其他各種猜測、分析、推論要直接和有力。
第四,加強論證。
或許有人會質疑:原告與被告雙方一致認可,法官不反對,可能是因為老師故意,學生裝傻,法官無能。且不論此種質疑沒有任何證據,若要此種質疑成立,則:
(7)必須將老師故意、學生裝傻、法官無能的概率分別論證為1,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只要任何一個的概率小于1,則包括學生本人的概率就永遠大于不包括學生本人的概率,即“包括”說在邏輯上永遠優于“不包括”說。
(8)還有人認為“幫人”不應包括學生本人是基于現今原、被告與其代理人有明確區分的法律規則,即原、被告不能同時是自己的代理人。顯然,這條規則極其簡單,如果在古希臘已有這條規則,那么老師、學生和法官都區分不出或故意混淆是不可思議的,根本不可信。因此,可以推定當時并沒有這條規則,原、被告與其代理人的關系還處于模糊狀態,所以,學生同時是被告和自己的代理人是可能的。
為驗證這種推定,我們查閱了相關文獻,發現律師制度起源于古希臘的雄辯術,形成于古羅馬時期。
在明確了“幫人”可以包括學生本人之后,我們可以確定地說,“半費之訟”自然可以是合同規定意義下學生第一次出庭幫人所打的官司,許多人的解決方案才有了堅實的前提和基礎。
但是,把本案的爭議焦點定于是否包括學生本人并沒有抓住“半費之訟”的本質,而一旦抓住,則“幫人”是否包括學生本人就變得無足輕重,對于本案的解決也無關緊要。
3.違背同一律說不能成立
違背同一律說認為,老師和學生都違背了同一律,他們在學生是否應該支付另一半學費這同一問題上采用了兩個不同的標準,哪個對自己有利就用哪個,這就犯了“前提不一致”的邏輯錯誤,其解決方案是在判決和合同中選擇一個,大多數人選擇判決。
這種觀點看似正確,但卻不能成立,因為:
第一,老師的推理形式和學生的推理形式是兩個形式完全相同且正確的連鎖二難推理。
老師的推理形式是:
(1)A→B(如果勝訴依判決)
┐A→C(如果敗訴依合同)
A∨┐A(或者勝訴或者敗訴)
B∨C(或者依勝訴判決或者依合同)
(2)B→D(依勝訴判決應付另一半學費)
C→D(依合同應付另一半學費)
B∨C(或者依勝訴判決或者依合同)
D(學生付另一半學費)
學生的推理形式是:
(3)A→B(如果勝訴依判決)
┐A→C(如果敗訴依合同)
A∨┐A(或者勝訴或者敗訴)
B∨C(或者依勝訴判決或者依合同)
(4)B→┐D(依勝訴判決不應付另一半學費)
C→┐D(依合同不應付另一半學費)
B∨C(或者依勝訴判決或者依合同)
┐D(學生不付另一半學費)
這是兩個形式完全相同的連鎖二難推理。二難推理的規則是兩個充分條件假言命題前件不同且窮盡所有可能。(1)(3)是復雜構成式,兩個充分條件假言命題的前件分別是勝訴和敗訴,且勝訴和敗訴窮盡了判決的所有可能;(2)(4)是簡單構成式,兩個充分條件假言命題有判決和合同兩個不同前提并且窮盡了所有可能,因此,這是兩個形式正確的連鎖二難推理。
有人認為還有一種可能是打和,所以前提并未窮盡所有可能,這是錯誤的。凡官司必有矛盾,無矛盾不可能打官司,所以判決只有勝訴敗訴兩種可能,打和的可能在源頭上就已被法律排除。
第二,判決與合同兩個標準為“半費之訟”本身所固有,并非師徒人為捏造,因此老師和學生以此為據在原則上是可能的。
第三,法庭有法庭的運行規則,在法庭上,當事人為自己利益辯護,怎么做對自己有利就怎么做是合法的。
第四,既然選擇判決,那就要證明判決高于合同,大多數人的理由是“既然已訴至法庭”,即當事人已將裁決權交給法官,所以應以判決為準。這種理由在原則上似乎成立,但在技術上卻面臨巨大難題:如果以判決為準,那判決又依據什么作出?自然是法律和事實。法律自然是有的,但事實何在?又由什么證明?自然只能是合同;合同不但證明事實的存在,還約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而這也正是判決的依據,如此,既否定合同又必須依據合同,豈不自相矛盾?如何克服這種矛盾,我們沒看到更進一步的分析。
至此,我們將“半費之訟”是邏輯問題的觀點一一否定,并且我們自己也沒有發現它存在其他邏輯問題;所以我們認為,“半費之訟”在邏輯上沒有問題。
(二)“半費之訟”本質上是法律問題
因為“半費之訟”在邏輯上沒有問題,所以從邏輯上來講,“半費之訟”只可能是法律問題。具體來說,“半費之訟”問題產生的根源是違背訴訟規則中的不告不理原則。不告不理是古羅馬時期出現的訴訟規則,在古希臘則稱為“沒有原告就沒有法官”,兩者的核心內容是一致的:“訴訟必須由當事人提起,啟動訴訟的權利專屬于當事人;當事人不起訴,法官不得主動開始訴訟;法官在審理過程中受原告人提出的訴訟請求范圍的約束,不審理訴訟請求范圍以外的問題。”[7](P28)也就是說,訴訟必須由當事人發起,即只有當事人起訴后,某某人才能以法官身份出場行使審判權;換言之,不告則不審,不審則不判;法官的職權只存在于審判期間,審判結束則審判權自然終止。
因為這種一致,所以我們不是用后世的規則來解決先前的問題,用“不告不理”只為行文方便。
現在,我們以老師的辯護為例說明“半費之訟”錯誤的根源所在。
當老師說,如果他勝訴,那么依照法庭判決,學生應當給付另一半學費,這個假言推理隱含了一個前提——法庭的判決應當被執行,根據法律、法官的地位、作用和功能,這個前提是正確的,因而老師這個觀點是正確的。
當老師說,如果他敗訴,根據合同,歐提勒士也應給付另一半學費,這卻是錯誤的。眾所周知,當事人的法庭辯論看似在反駁對方,但其根本目的實際在于說服法官,所以,老師的話根本上是對法官說的,而他的話預設了法官應對由本案判決可能引發的另一案件(本文稱為案件二)進行裁決,但這個預設違背了不告不理原則,是錯誤的。因為:
第一,起訴的權利專屬于當事人,案件二由誰起訴?原告何在?在當事人沒有起訴的情況下案件二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想象,法官當然不可能審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案件。
第二,法官既已作出敗訴判決,對他而言,其審判職權到此終止,“半費之訟”到此結束。因此,法官沒有權力對案件二進行裁決,原告的要求不合法,法官完全有權置之不理。
第三,“依照合同學生應付我另一半學費”是本案判決后可能產生的師徒之間“新的”民事糾紛,產生的原因是合同條款的“特殊”規定,這與法官無關。那師徒要如何解決這個“新的”民事糾紛?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誰在問?是師徒二人還是旁觀者?要誰回答?是法官、師徒自己還是其他人?我們對此以上帝視角說明:從根本上講,不管誰問,這是他們師徒自己的事,因為這屬私權;如果一定要回答,無非私下解決和再行起訴;如果私下解決,可協商,可放棄,可暴力;如果私下解決不成,或可再行起訴;即便再行起訴,那也是另外一個案件,應由另外的法官來審理;即便再由本案法官審理,那也是另外一個案件。那種要求“半費之訟”的法官對此進行裁決的觀點,實屬“求解過寬”,將“半費之訟”法官本不應該承擔的責任強加于他,這是人們求解“半費之訟”錯誤的根源。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再行起訴涉及一事不再理原則[7](P692),如何處理,要看古希臘時期的具體規定。但不論如何規定,都與“半費之訟”的法官無關,“半費之訟”法官的職責是而且僅僅是對“半費之訟”作出裁決。
至此,我們以不告不理將師徒二人的二難推理攔腰斬斷,“半費之訟”的法律本質也得以徹底澄清。
基于對“半費之訟”本質的澄清,下面一類解決方案的錯誤就很好解釋了。
羊滌生的解決方案是:“法庭可受理此案,并且根據他們的合同判愛瓦梯爾(即歐提勒士——作者注)不付學費,因在此之前,愛沒有勝訴過,因而可不付學費。于是愛瓦梯爾第一場出庭便勝訴。正當愛瓦梯爾勝訴之時,法庭又判決愛瓦梯爾該付學費,因愛瓦梯爾第一場出庭便勝訴。”[8](P337)李建新的方案是,先判學生勝訴,即“可以不還”,再判學生敗訴,即“必須償還”[2](P16-17)。
這類方案明顯是邏輯學家在不了解不告不理原則情況下的邏輯想象,真是為了幫老師拿到另一半學費而殫精竭慮!可是,第一,如前文已述,幫老師拿到另一半學費并非“半費之訟”的真正解決,而是研究;第二,這種方案直接違背了不告不理原則——法官無權指令(指示、暗示、勸導)當事人起訴,更不可能在當事人未起訴的情況下主動審理并判決;第三,它也違背了古希臘彈劾式訴訟中法官消極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原則。所以,這種方案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現實中是不可操作的。
四、判決
澄清了“半費之訟”的法律本質,那如何判決呢?如果我是古希臘的法官,我的判決如下:
本案爭議焦點為被告是否應給付原告另一半學費。此爭議焦點可分為以下兩點,本庭分別加以分析評判。
(一)本案是否為合同規定意義下之第一場官司
由于原告與被告在辯論中均認為“幫人”包括被告本人且不反對對方如此使用,加之此前有自指先例,此論亦未違法或有悖公序良俗,故本庭對此加以確認。由此可認定本案為合同規定意義下被告歐提勒士第一次出庭幫人所打之官司。
(二)判決后本庭是否還應對可能產生之新案進行裁決
不應該。第一,所謂新案并未由當事人起訴,實則并不存在,故裁決無從談起,故要求本庭裁決于法無據。第二,根據不告不理,法官審理受訴訟請求之約束,不審理訴訟請求范圍以外之事項。原告訴訟請求中并無要求本庭審理本案判決后可能產生之新案,故新案亦不在本案審理范圍之內,本庭無裁決之責任。第三,判決后,合同所規定之條件可能成就,亦可能不成就,但不論成就與否,由此可能引發之合同糾紛,實為原告與被告間私下之民事糾紛,應由雙方私下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可再行起訴,但此僅為本庭之建議。即便再行起訴,其受理、審判、裁決也與本庭無關,本庭之職權僅在于審理本案。
原告與被告在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實條件之下簽訂合同,且原告與被告并未對合同之有效性提出異議,故本庭對合同之真實性及有效性予以確認。因合同為附條件之民事合同,在原告起訴之時,合同所規定之條件——被告歐提勒士第一次出庭幫人打官司且勝訴——并未成就,故原告之起訴并無事實依據,因此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要求被告給付另一半學費之訴訟請求。
五、結語
“半費之訟”的解決是法官作出合法判決,如果法官作出合法判決,則法官必須對師徒二人的二難推理作出合理解釋,合理解釋就是師徒二人二難推理的后半部分要求法官對判決后可能產生的合同糾紛進行裁決的預設違背了不告不理原則,是錯誤的,師徒二人的二難推理也是錯誤的。
在對“半費之訟”的研究中,我們發現以下幾點:
第一,長期以來,“半費之訟”沒有得到公認解決的原因之一是人們普遍忽視了“半費之訟”元問題的重要性,如“‘半費之訟’之解”的含義,“半費之訟”的性質等。這些問題的回答直接決定了問題的解決方向和答案范圍。但幾乎沒有人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他們雖然不可避免要回答,但回答基本憑直覺、“顯然”或假定,由此造成了許多誤解和混亂。
第二,許多研究者不了解法律,也不了解法律與邏輯的關系,執著于邏輯的解決。他們提出了許多邏輯上的可能性,但卻不問這些可能性在法律上是否可能。或許他們認為,邏輯是一切學科的工具,自然也是法律的工具,所以,邏輯提供的方法和工具法律就得“照單全收”。殊不知,法律對邏輯的應用是有取舍的,許多法律規則對邏輯有限制,典型的如法律因果關系對邏輯(或哲學)因果關系的限制,某些事物邏輯上的可能性在源頭上就被法律排除,某些事物的因果關系被法律因果關系切斷。
第三,邏輯與法律的時間性并不一致。一般而言,邏輯沒有時間性,因而邏輯可以超越時空,所以可以出現“‘半費之訟’的判決要以‘半費之訟’本身的判決為依據”這種邏輯循環,但法律有時間性,因此,一些自我指涉的法律問題的邏輯循環可以用法律規則切斷。在“半費之訟”中,可以以起訴為時間節點將訴訟與非訴訟、法官與非法官、法官職權與法官職業合法而自然地切分,自我指涉的邏輯循環也就不復存在。
參考文獻:
[1]
潘建輝.訴訟悖論及其消解[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9).
[2]李建新.我對“半費之訟”的裁決[J].邏輯與語言學習,1993(12).
[3]田平安.民事訴訟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4]陳波.邏輯學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5]朱鈺華.“半費之訟”是一個悖論[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5).
[6]黃展驥.“半費之訟”悖論——略論“自涉”與“非自涉”[J].人文雜志,1998(5).
[7]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K].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8]蘇天輔.形式邏輯[M].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3.
The Legal Essence of Half-tuition Lawsuit
LIU Jian-ling
(Deportment of Philosophy,School of Humaniti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
The half-tuition lawsuit is essentially a legal issue rather than a logical issue.In the debate,the master and his apprentice presuppose that the judge should rule on the new case that may be triggered after his verdict,which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not trial without complaint.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ot trial without complaint,the judge’s trial power only exists in the trial process of the case,and the trial power naturally terminates after his judgment.Therefore,the judge of half-tuition lawsuit has no right to rule on the new case that may be triggered after this judgment.Therefore,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master and his apprentice is wrong,which is the source of the half-tuition lawsuit problem.To use the principle of not trial without complaint,with whether to sue or not,we can clearly distinguish litigation and civil dispute,judge and non-judge,judge’s trial power and judge’s profession,thereby? the dilemmas of the master and his apprentice can be cut off legally and naturally,and the half-tuition lawsuit can be completely resolved.
Key words:
half-tuition lawsuit;not trial without complaint;dilemma;presupposition;premise analysis
(責任編輯
徐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