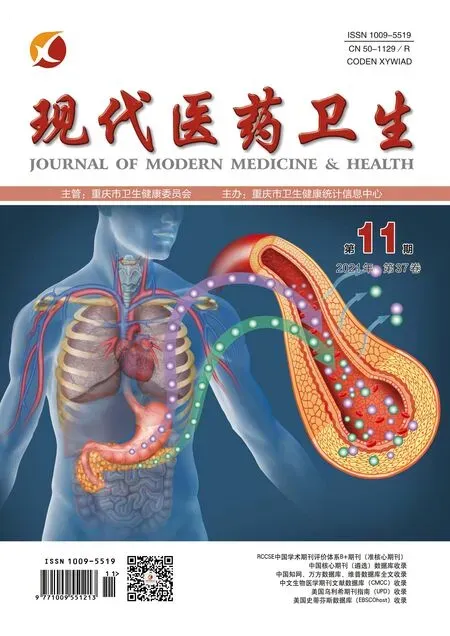中醫(yī)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yǎng)和引導社會輿論方面的改革思考
徐大釗,李琳軒,李春華,陳瀅如,辛思源,吳曉紅
(1.北京市中關村醫(yī)院,北京 100190;2.河北中醫(yī)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200;3.首都醫(yī)科大學電力教學醫(yī)院,北京 100073;4.中國中醫(y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北京 100700;5.承德醫(yī)學院,河北 承德 067000)
早在19世紀下半葉,隨著“西學東漸”的日盛,中醫(yī)學及師帶徒的中醫(yī)教育模式屢遭傾覆之議,從那時起中醫(yī)仁人志士便提出“非出刊物不足以喚醒醉夢,非辦醫(yī)校不足以剔除積弊”的呼聲,以期改變中醫(yī)的危局[1]。但直至新中國建立后,中醫(yī)的學校教育體系伴隨著一批中醫(yī)院校的建立才逐漸完善。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教育考試制度的確立,高等中醫(yī)教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為我國培養(yǎng)出大批中醫(yī)學專業(yè)的高材生[2]。
從直觀的角度來看,高等中醫(yī)教育是成功的[3]。但從目前臨床現實的需求來看,中醫(yī)學生面臨臨床能力相對不足、就業(yè)空間小、競爭壓力大等問題[4]。據統計,南方醫(yī)科大學2011年中醫(yī)類本科生畢業(yè)去向,從事醫(yī)療行業(yè)僅占30.3%,考研升學所占比例為24.7%[5]。與西醫(yī)從業(yè)人員比較,目前從事中醫(yī)執(zhí)業(yè)人員遠遠低于從事西醫(yī)執(zhí)業(yè)人員,且人數差距越來越大。據《2019中國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數據顯示[6],2015-2019年全國衛(wèi)生機構中醫(yī)執(zhí)業(yè)(含助理)醫(yī)師人數分別為45.2、48.2、52.7、57.5萬人,而全國衛(wèi)生機構西醫(yī)執(zhí)業(yè)(含助理)醫(yī)師人數由2017年的256.1萬人,到2018年就達270.0萬人,其1年期間增長的人數(13.9萬)就超過了4年中醫(yī)執(zhí)業(yè)(助理)醫(yī)師增長的總人數(12.3萬)。由此可見,中醫(yī)人才培養(yǎng)和隊伍建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
目前,社會輿論中質疑、詆毀中醫(yī)的言論屢見不鮮。而目前中醫(yī)主流宣傳常見于養(yǎng)生類訪談節(jié)目。此類宣傳方式并不足以回應社會輿論中的質疑,更不能引領社會輿論。教師需探索以中醫(yī)高等教育為主陣地的中醫(yī)宣傳,樹立科學、嚴謹的中醫(yī)宣傳模式,以便引導社會客觀、理性的認識中醫(yī)。
1 中醫(yī)高等教育的不足
1.1學生臨床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相對不足 目前,中醫(yī)高等教育培養(yǎng)的部分中醫(yī)學生臨床技能薄弱,就業(yè)時又會面臨西醫(yī)院校學生的競爭,部分中醫(yī)學生尤其中醫(yī)類本科生會有棄醫(yī)改行的選擇。
在全國中醫(yī)藥教育發(fā)展中心組織的《疫情期間全國中醫(yī)藥院校在線教學質量調查》中,教師反映在疫情前主要采取課程授課和臨床帶教方式,對線上教學經驗不足,而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不足,對線上資源的利用度不高,對臨床能力的提升遇到瓶頸。因此,如何在疫情下提高學生臨床能力也是需要探索和解決的難題[7]。
1.1.1理論與實踐相脫節(jié) 大部分中醫(yī)高等教育模式,與西醫(yī)院校教育相似,采用“基礎課-專業(yè)課-臨床實習”三段式教育模式。但不同于西醫(yī)基礎理論課程(如解剖學、生理學)具有直觀性、可重復性等特點,且這些課程往往伴隨著實驗課,容易加深理解。而中醫(yī)的理論比較深奧和圓融,理解、掌握中醫(yī)理論的精髓是學好中醫(yī)的基礎,但僅僅課堂上的理論講授,并不能真正掌握好中醫(yī)的精髓;而且中醫(yī)學生是在學完全部基礎理論后方進入臨床實習,理論教學與實踐被割裂為2個相互獨立的階段,導致學生理論和臨床嚴重脫節(jié),臨床處理實際問題明顯不足[8]。
1.1.2課程設置和西醫(yī)教輔材料的選擇上仍有爭議 中醫(yī)教育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是如何學習、借鑒西醫(yī)。比如在西醫(yī)課程與中醫(yī)課程設置比例上有的院校直接將中西醫(yī)課時各占50%,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不中不西”,也不利于學生培養(yǎng)出良好的中醫(yī)臨床思維。
目前,中醫(yī)類的西醫(yī)教輔材料與西醫(yī)院校學生不同,在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上距離西醫(yī)院校的教輔材料仍有差距,這樣的選擇會導致中醫(yī)學生對于西醫(yī)最新前沿知識了解不足,使很多中醫(yī)院校畢業(yè)生進入醫(yī)院、科研院所后,凸顯了西醫(yī)知識更新能力和臨床能力相對不足;同時由于缺乏對西醫(yī)全方面的了解,并不利于中醫(yī)學生從系統論的高度來評價中醫(yī)與西醫(yī)的優(yōu)劣和以此來堅定中醫(yī)的理論信仰。
1.2中醫(yī)文化的社會輿論引導力尚不足 中醫(yī)的社會影響力仍很薄弱,尤其是高等中醫(yī)院校比較注重臨床、科研方面人才的培養(yǎng)。但在中醫(yī)文化的宣教、引領社會社會輿論方面有待加強。
1.2.1社會存在質疑、詆毀中醫(yī)的不良輿論 目前,社會輿論存在著一股質疑中醫(yī)的言論。比如中醫(yī)“偽科學”的爭論,不斷被提及的“中藥不良反應”和擁有眾多粉絲的號稱“醫(yī)學界魯迅”的燒傷超人阿寶,在2014年“約戰(zhàn)”中醫(yī)脈診驗孕等。有些爭論固然可以看作是學術爭鳴,但分析相關言論大都是在不了解中醫(yī)理論的基礎上而簡單機械按照實驗論證的觀點來審視、批駁中醫(yī)的行為。但對于這些影響較大的社會輿論,擁有中醫(yī)優(yōu)勢資源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尚未充分因勢利導,引導中醫(yī)文化的宣教和普及。
1.2.2中醫(yī)高等教育缺乏中醫(yī)思想文化的人文建設 目前,中醫(yī)高等教育重視專業(yè)教材而忽視人文社會學科如歷史、哲學、文學的學習,缺乏中醫(yī)思想文化的人文建設,導致部分學生人文素質偏差,學術思維較局限,中醫(yī)學生專業(yè)思想不穩(wěn)固等問題。所以即使接受了中醫(yī)高等教育的人群,缺乏中醫(yī)文化情懷,在抵制不良社會思潮方面并未發(fā)揮出積極的作用。這也凸顯了中醫(yī)高等教育在中醫(yī)文化宣教引領社會輿論方面的薄弱。
2 中醫(yī)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考
面對上述問題,以中醫(yī)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為抓手能夠解決相關的問題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中醫(yī)高等教育領域擁有中醫(yī)藥優(yōu)勢的資源,俗話說“打鐵仍需自身硬”,中醫(yī)院校解決中醫(yī)的人才培養(yǎng)、宣傳中醫(yī)文化等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依靠中醫(yī)自己的陣地和團隊。尤其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發(fā)以來,中醫(yī)藥以其獨有的優(yōu)勢和特色,與西醫(yī)協同抗疫,取得了顯著成效,詮釋了中醫(yī)文化的博大精深,但面臨新冠“大考”,也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2.1重視臨床能力培養(yǎng),鼓勵名家醫(yī)脈案的整理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說:“中醫(yī)之成績,醫(yī)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經驗心得,醫(yī)案最有線索可尋,循此磚研,事半功倍。”中醫(yī)醫(yī)案是歷代醫(yī)家靈活運用中醫(yī)理、法、方、藥救治患者的真實案例,是中醫(yī)理論和臨床實踐相結合的生動范例,而蘊含其中的辯證思維、凝練的學術觀點更是中醫(yī)學術思想的源泉,更是學習中醫(yī)理論和提高中醫(yī)臨床思維能力最好的借鑒[9]。鼓勵醫(yī)學生對名家醫(yī)脈案的整理和總結,理解與滲悟歷代名家醫(yī)脈案是掌握中醫(yī)學術思想的一條捷徑,尤其親自翻閱與整理,可激發(fā)學術創(chuàng)新能力,使已有理論得以升華。
2.2優(yōu)化課程比例,重視中醫(yī)經典和公共衛(wèi)生課程 在本科的課程教學設計中應將中醫(yī)經典課程作為中基中診等基礎課程結束后的重點。一方面增加中醫(yī)經典的課時數量,減弱教學進度的苛求,擴充教學大綱對于中醫(yī)經典課程的掌握標準要求[10]。另一方面要強化中醫(yī)文化(尤其是儒家理學專著)、傳統哲學(重點是中國古代傳統哲學家的思想結晶)、中醫(yī)醫(yī)學史、大醫(yī)講壇(如國醫(yī)大師、知名中醫(yī)學者的學術思想)等一些中醫(yī)普及、入門的課程的設置。此類課程會對中醫(yī)學生加深中醫(yī)文化精髓的理解、增強中醫(yī)的興趣,甚至肩負起傳承中醫(yī)的責任感、使命感而起到重要的作用。
自新冠疫情以來,也凸顯了公共衛(wèi)生人才的短缺、應急處理能力的不足,因此在現行的中醫(yī)教育體系中,提高《預防醫(yī)學》《公共衛(wèi)生管理》等課程所占比例,提高中醫(yī)藥人才在傳染病防治和公共衛(wèi)生事業(yè)中的知識儲備能力和應急處理能力。
2.3重視哲學和醫(yī)學史的學習,加強中醫(yī)人文建設 中醫(yī)高等院校教育還要注重中醫(yī)文化、中醫(yī)思維等教育問題。中醫(yī)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經濟、文化基礎上伴隨著人們的生產、生活,甚至是戰(zhàn)爭、時疫、水旱饑荒而產生、發(fā)展的。所以要想真正地了解中醫(yī)的起源與文化范疇,必須注重對中國傳統儒家倫理著作、哲學、歷史甚至不同歷史時期政經、災異、民俗的研究。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掌握,因為中國傳統哲學是中醫(yī)理論的基礎。王永炎院士指出中醫(yī)學離不開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是民族的智慧[11]。加強中國傳統哲學的學習,還要兼顧傳統哲學對于當代普遍性矛盾的現實指導意義,要樹立起哲學是一種智慧,一種方法,無關對錯、高低的觀念。從本質上來說,中醫(yī)也是我們傳統優(yōu)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習好中醫(yī)需要傳統文化的積淀與澆灌[12]。
促進中醫(yī)思想文化的建設,醫(yī)學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醫(yī)學史的講授要注重2條線,一是重要醫(yī)家的學術觀點、學術著作產生時的政經、文化、社會等時代大背景;二是注重醫(yī)學專家個人成長的文獻研究。時代背景的闡釋會增強對中醫(yī)學術思想全方位的理解,而醫(yī)家成長背景的研究則會使中醫(yī)學術更加立體和飽滿。中醫(yī)的魅力固然在救死扶傷,但那些歷代名家不僅留下了學術專著、珍貴的醫(yī)方脈案,在求學、驅疾的歷程中所展現的孜孜不倦、苦讀上進的學風,妙手仁心的醫(yī)風,更是屹立千年而不衰,成為一代又一代中醫(yī)傳承者的道德坐標和精神楷模,所以對于中醫(yī)文化教育歷代醫(yī)家的文獻研究不可或缺[13]。
2.4重視中醫(yī)宣傳,增強中醫(yī)文化自信 隨著中醫(yī)學校教育的發(fā)展,中醫(yī)背景的人群增多,但并未在助推中醫(yī)的成果轉化、中醫(yī)思想的宣傳普及、大眾崇尚中醫(yī)等方面化為推動中醫(yī)發(fā)展的實際力量。甚至在社會輿論中一直存在一股抵制、譏諷中醫(yī)的言論。故中醫(yī)的發(fā)展除了在教學、科研、醫(yī)藥方向上培養(yǎng)出大批人才外,教師還需要中醫(yī)文化宣傳人才或者中醫(yī)文化的繼承者、發(fā)展者、弘揚者。中醫(yī)文化宣傳廣度與深度體現著中醫(yī)發(fā)展的軟實力。過去人們常常認為中醫(yī)不需要宣傳,中醫(yī)的作用要靠療效,或中醫(yī)的宣傳應是所謂中醫(yī)臨床專業(yè)的醫(yī)家的分內之事,并不需要額外宣傳中醫(yī)的人才。但結合目前的社會輿論和多元的社會認知來看,加強中醫(yī)文化的宣傳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在本次抗疫的早期,中醫(yī)藥的參與率并不高,隨著中醫(yī)藥參與抗疫的臨床療效確切,其優(yōu)勢才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全國確診病例中,中醫(yī)藥治療病例達92.58%。其中,武漢方艙醫(yī)院累計服用中藥例數達99.9%,中醫(yī)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臨床效果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認同。因此,也增加了中醫(yī)學子對中醫(yī)理論和文化自信。
3 小 結
中醫(yī)高等教育人才培養(yǎng)中還存在著精英化還是普及化路線的爭論。部分中醫(yī)人士認為中醫(yī)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應該走精英化之路[7],集中資源來重點支持優(yōu)秀的中醫(yī)人才和中醫(yī)院校,精英化的中醫(yī)教育提高了中醫(yī)的門檻,會淘汰掉一大批庸醫(yī)、偽醫(yī),改變目前的中醫(yī)人才供需結構,緩解中醫(yī)人才的就業(yè)需求,還會形成高智商人才反流學習中醫(yī)熱潮,從根本上解決中醫(yī)人才問題。
精英化的中醫(yī)高等教育固然可以解決目前困擾中醫(yī)的某些問題,但精英化的中醫(yī)教育是否一定可以帶來精英化的中醫(yī)人才,這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教師都知道中醫(yī)事業(yè)的發(fā)展是一個涵蓋傳統哲學、養(yǎng)生預防、臨床診療等多層次的發(fā)展體系。可持續(xù)的發(fā)展體系應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尤其是在社會輿論方面,還存在各種各樣的抵制中醫(yī)的誤解和謬論,如何正本清源,批判不良言論,引導大眾接受中醫(yī)的文化和思想,不僅僅是宣傳輿論戰(zhàn)線的勝敗交鋒,更是中醫(yī)能否贏得社會輿論、群眾基礎的發(fā)展關鍵。由此可見,教師不僅要注重名醫(yī)、名院、名校的建設,更要擴大中醫(yī)不同層次的人才,使之形成金字塔式的發(fā)展模式。教師相信在不斷推進的中醫(yī)高等教育改革中,如能提高自主學習能力,加強傳統文化和哲學的學習,磨礪中醫(yī)思維,推動中醫(yī)文化復興、提升中醫(yī)文化自信,推進國民對中醫(yī)文化的價值選擇和堅守意志,在中西醫(yī)交流選擇中不被外來文化“誘惑”及“同化”[14],并通過此次中醫(yī)藥在抗疫中取得的成就,積極推動中醫(yī)藥國際化進程[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