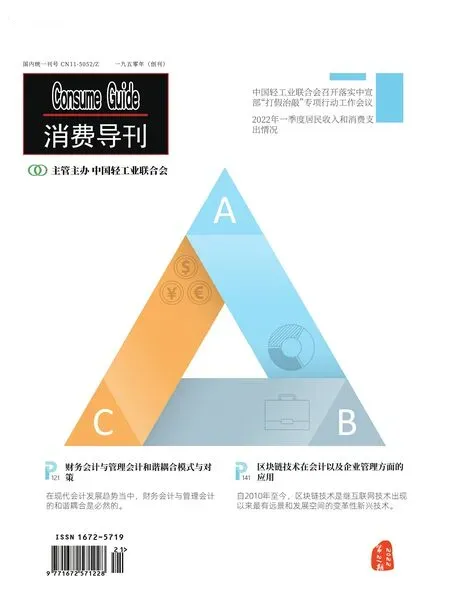推進糧食全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
鄭潔 江南大學商學院
一、引言
糧食安全是關系整個國家和人民的壓艙石,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永遠是重中之重。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了農業生產、貿易、商品價格和居民購買力,對糧食安全構成了威脅。我國采取的嚴格封鎖和隔離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但也對包括農業生產和貿易在內的經濟活動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產業鏈作為經濟的生命線,其重要性前所未有。“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問題,不僅是應對風險挑戰的關鍵之舉,更是著眼長遠,贏得發展主動權的重要手段。伴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數字化已經滲透到多個領域,推動多個領域的產業鏈創新發展。據統計,2019年服務業數字經濟增加值占行業增加值的比重為37.8%;工業數字產業增加值占行業增加值同比提升1.2個百分點。然而2019年農業數字經濟增加值占總體行業增加值比重僅為8.2%,數字化滲透融合程度遠低于工業與服務業。但“糧食數字化”的重要性已經引起社會各界注意,在第三屆中國糧食交易大會上,“數字化”成本屆大會的關鍵詞之一。交易大會首次設立“全產業鏈數字化”展區,并舉辦了“糧食產業數字化”論壇。
糧食全產業鏈的數字化可以通過融通整個產業鏈的物質、資金和信息流,帶動整個產業鏈向共生、互利、穩定、共贏邁進,從而為優質糧食工程和國家糧食安全提供助力。因此,討論如何將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推廣應用到糧食產業鏈各領域、推動糧食全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從而助力優質糧食工程和國家糧食安全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糧食安全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于1983年提出:“糧食安全是確保所有人在任何時候既能買得到又能買得起他們所需要的基本食物”。中國學者在基本概念上加入了中國國情的考慮,從不同側面對糧食安全的概念進行了擴展。比如,張元紅(2015)對中國糧食安全保障的現狀、趨勢、問題進行了分析,從而構建了包括供給、分配、消費、利用效率、保障結果、穩定性、可持續性和調控力等8個方面的指標體系[1];國家糧食局控制司也提出糧食安全應包括物質保障能力、消費能力以及保障渠道和機制等多個產業鏈組成方面指標。由此可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糧食安全的界定逐漸延伸為糧食全產業鏈的穩定運行。
(二)糧食產業鏈
糧食產量的逐漸增長,解決了階段性糧食供給總量的問題,但糧食問題已由總量矛盾向結構性矛盾轉移[2]。一直以來,保障糧食供給目標與種糧農民的增加收入目標往往成為矛盾的兩個方面[3],同時隨著生產成本的增加、金融排斥現象導致的糧食生產資金不足等問題導致糧食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在糧食產業的鏈條上,生產環節屬于產業鏈上游,而生產主體積極性的降低將給糧食持續增產造成負面影響。郭艷枝(2014)提出我國糧食損耗的環節較多,主要有糧食豐收后的收獲環節、收購環節、儲存環節、運輸環節、加工包裝環節等[4],這些環節均為糧食產業鏈中下游的重要組成部分,若不及時解決糧食在這一系列過程中的損耗問題,最終將導向糧食安全問題。在糧食產業鏈下游方面,寇光濤(2017)提出,糧食品牌管理以及對消費者個性化的需求滿足方面分析不足,渠道開拓能力差[5]。針對糧食全產業鏈方面,張士杰(2019)認為我國糧食生產、儲藏、加工等處于“小而散”的狀態,導致糧食產業間的聯結松散,遠沒有達到鏈條化、整體化的生產[2]。
(三)糧食產業數字化
近幾年,數字技術的應用推動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改變了傳統的商業模式,為各個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在農業領域,許世衛(2019)提出應用大數據思維、方法和技術解決農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服務的問題,將使農業發生重大變化[6]。綜合來看,目前的文獻大多關注整個農業領域,而以糧食全產業鏈為研究對象的文獻較少。
三、糧食全產業鏈數字化轉型助力糧食安全的機理分析
就目前而言,關于數字化嵌入糧食全產業鏈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只有少數專家就模式創新、概念界定、案例列舉等方面進行了相關描述與探究。筆者認為,數字化與糧食全產業鏈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拼湊,它是一項現代農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的系統工程,是一種傳統經營觀念的突破和商業模式的變革。它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通過政府支持,依靠互聯網技術,提升產業鏈條在信息、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專業化服務水平,通過鏈條上資源跨域跨界的合理配置和優化調度,使得糧食產業鏈糧資供應、糧食生產、糧食收儲、物流、加工、銷售、消費等產業鏈環節分別向著規模化、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品牌化、精準化、可溯化水平等全面提升,最終實現鏈條的效率提升和效益增加,從而為我國糧食安全助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糧食產業鏈劃分為四個部分,糧食產業鏈上游主要是糧食產前的準備工作,包括農資的供應、種糧資金的籌集;糧食產業鏈中游主要是糧食的種植生產過程;糧食產業鏈中下游為糧食產后的收儲、物流以及加工過程;糧食產業鏈下游主要為產后糧食的銷售和消費過程。
(一)從糧食產業鏈上游來看
農資產品屬于剛性需求,在糧食生產過程中需要進行不斷地補給,所需規模大且運輸要求較低,因此在當前國家政策利好電子商務的背景下,可以大力發展農資電子商務。目前,史丹利、金正大以及大北農等國內農資領域的龍頭企業,均已涉足電子商務業務。電子商務系統搭建起了廠商信息共享平臺,讓購肥更加快捷、方便。同時,基于地理信息系統、測土配方的化肥定制化生產等技術開始推廣應用,農資供應更加精準化。農資龍頭企業通過數字化服務使得企業訂單量增加以及競爭力得到提升從而防止被國際大糧商收購。
(二)從產業鏈中游來看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一些流行性重大病蟲在我國的暴發頻率增加,突發自然災害使得糧食產量受到的波動性較大。同時,我國的糧食生產模式機械化水平較低,生產效率不高。這一系列問題均對糧食生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數字化的興起與應用,恰恰可以為改變這種困境找到出路。如在優化糧食生產上,圍繞土壤監測、氣象預報、水肥管理、病蟲害預報、數字機械化種植等方面已經開展了大量的應用,國內外涌現出一批以大數據等新技術推動農業創新與轉型的IT服務商。在世界農業發達國家,農業大數據已為生產經營提供了有效的應用。美國硅谷土壤抽樣分析服務商Solum利用軟、硬件系統實現精準土壤抽樣分析,對土壤進行定性分析;我國的一些智慧農業社區也開始使用無人飛機進行噴藥施肥。通過將數字化融入糧食生產過程,可以實現糧食生產的精準化、規模化、實時化、可預測化等,從而提高了糧食產量和質量,為糧食安全助力護航。
(三)從產業鏈中下游來看
據以往研究,本文認為糧食產業鏈中下游主要包括糧食的收儲、運輸、加工過程。
利用現代信息技術自動采集數據的優勢,可以對糧食收購及儲存過程進行全程信息化監控。如將糧食質量檢驗、糧食稱重、糧價等環節的動態信息均輸入糧食管理服務系統,這將有力促進糧食收購規范管理;由于糧食所需儲備環境的特殊性,很難進行人工控制,而儲備可視化監管系統,可以全面、直觀、及時掌握儲備糧在庫情況,并可通過射頻、傳感器等技術來監控周圍環境變化,實時保證糧食儲備環境的最優性。以上可以看出數字化可以實現對儲備糧的全過程遠程監管,提高儲備糧管理現代化水平,減少糧食損耗。
在物流方面,我國目前具有較為發達的商業物流體系,但是在糧食物流方面依舊存在諸多問題。例如糧食運輸設備水平低下,包裝、裝卸等環節主要依靠人工,導致工作效率低;同時運輸過程的物流信息不能及時被監測。糧食物流的數字化可以在裝卸方面用機器人代替人工,在物流信息方面構建全面的管理服務系統,從而保障糧食物流的高效率。
(四)從產業鏈下游來看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者對于糧食質量的要求也隨之增加。因此對于消費者來說,溯源制度是否完善成為他們評估糧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互聯網可以形成來源可查、去向可追、責任可究的信息鏈條,方便消費者查詢。事實上,阿里巴巴、京東等大型電子商務平臺已經在利用大數據保障食品溯源,因此可以將其拓展到糧食上,通過二維碼來獲取糧食生產地、生產者、生長周期、化肥農藥施用量、收獲流通日期等溯源信息,從而實現糧食質量全產業鏈過程的把控。
(五)數字化金融支持在糧食全產業鏈過程的應用
近年來,普惠金融大力發展,但是目前我國的農村的“金融排斥”現象依舊大范圍存在——農戶貸款難、農業保險未能發揮其保障作用等。互聯網金融的大力發展為該現狀的改變提供了導向。互聯網金融可以將糧食產前資質評價、產中風險監控、產后收入等多環節信息進行整合從而形成較為完善的征信系統進而提供相應貸款與保險等金融服務。
四、結論與建議
(一)以大數據為基礎,優化糧食產業鏈
推動糧食產業數字化,深度融合云計算、大數據、5G等現代技術,通過連接糧食產業鏈上下游,實現數據共享。匯聚這些影響糧食種植的環境數據、生產過程各要素投入數據、物流信息數據、銷售數據等,構建糧食全產業鏈數據資源體系。
(二)建立成熟的糧食電商模式
無論是在產前的農資供應還是在產后的糧食銷售,電子商務在提高訂單量、提高配送效率以及擴大品牌效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同時,糧農入駐電子商務平臺,可以有效地收集其交易狀況等信息,從而完善糧農的征信信息,有利于糧農融資的可持續性。
(三)推進衛星導航等新技術在糧食種植過程的應用
在利用衛星導航對地觀測過程中,遙感器可以精確的對地表進行數字化記錄,使糧食種植情況得到可視化真實展現。據專家估計,我國自主運行的衛星數據在農業領域的應用排在中下游,這與糧食安全在我國的發展重要性極其不符,因此需要推進糧食生產過程中衛星導航系統的應用。
(四)加大互聯網金融對糧食產業的扶持
通過前文機理分析可知,可以通過構建覆蓋農資購銷、糧食生產、糧食銷售全過程的數字化平臺,將數字化金融嵌入糧食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推動金融服務體系在糧食全產業鏈構建過程中實現閉環和普惠,從而進一步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