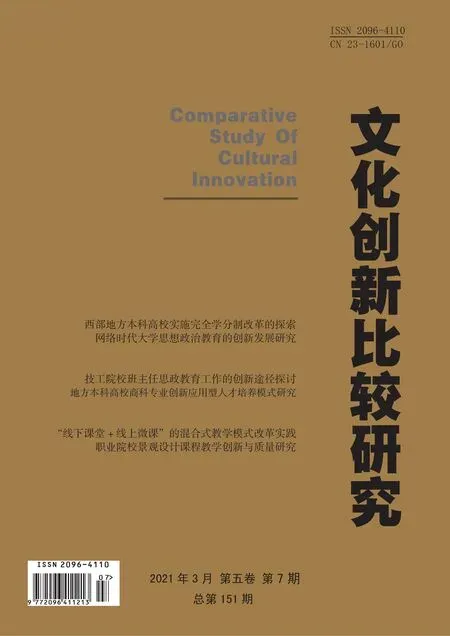高職院校大學生價值取向的特點及成因探究
朱潔
(江蘇城鄉建設職業學院,江蘇常州 213000)
《價值學大詞典》中將“價值取向”概述為主體的價值選擇傾向性。因而,價值取向反映的是主體的價值追求,體現的是其所奉行的某種價值標準[1]。由此角度來看,我們可將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理解為:學生在就業選擇或決策時的傾向性。
1 研究意義
該文以高職院校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致力于研究其就業價值取向的特點及成因。結合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等網絡平臺的文獻資源,分析并論述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的相關特性、演化情況及影響因素。
大學生奉行何種就業價值取向,直接決定其之后的就業選擇。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就業為民生之本,財富之源。作為主要的就業群體,高職畢業生占據了“半壁江山”,當然,面對非常殘酷的市場競爭,高職學生需承擔較大的就業壓力。由根本上而言,高職院校大學生(以下簡稱“大學生”)的就業價值取向一方面影響著其就業目標,另一方面直接關乎著其就業行為,也就是說與他們的職業選擇及發展密切相關。該文在分析當代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特點的基礎上,論述形成這些特征的成因,對推動高效教育教學改革、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價值觀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2]。
2 高職院校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特點
2.1 多元化
時代在不斷發展,社會價值的多元發展直接致使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演變。表現為大學生在樹立就業價值觀時,不再以國企、事業單位為最優選擇,更多的大學生會考慮自主創業或海外留學進修。此外,高職院校及教育部門也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人才到大西北等區域工作,這也使得大學生就業選擇朝向多元化發展。
2.2 信息化、網絡化
新媒體時代背景下,基于數字化、網絡通信技術的應用,使大學生不出門便可盡曉天下事。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大學生可快速獲取與崗位相關的工作,也可與意向企業進行交談。再加之如今的多數用人單位也開辟了網絡招聘渠道,大學生可利用網絡投遞簡歷,甚至是進行線上面試。由人人網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度,參與網上求職的大學生人數占據了大學生求職總人數的極大一部分,且遠遠超出傳統的校園招聘會。
2.3 功利化
雖然大學生就業選擇日趨多樣化,但在調查中,將“薪酬福利”擺在首位的大學生仍占據大多數。選擇到西部、基層崗位就業的大學生一般是看中了政府部門所給予的“優惠政策”,為追求高福利、穩定性,大部分大學生認為國企、事業單位才是最優選擇,所以說大學生中就業價值取向的功利化元素是客觀存在的,且特點十分突出[3]。此外,之所以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十分嚴峻,也與其自身定位的模糊存在較大聯系,表現為就業期望值過高,在與用人企業、單位交談時,將重點放在福利待遇、工資薪酬等方面,卻未做好個人職業生涯規劃,目標短淺,因此也使得大學生就業后的離職率較高。
2.4 社會責任感淡化
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視角來看,人本就是一類特殊的社會動物,既是一種合群的動物,也可在群體中各自獨立,在國家努力構建文明社會的背景下,社會責任感作為一種倡導型理念也備受關注。何為社會責任感?可簡單理解為在某一社會條件下,構成社會的各個主體在心理認知上對他人的倫理關懷及義務。分析來看,當代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由于主體的不同差異較大,再加之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許多大學生缺乏對人生的合理規劃,社會責任感淡薄,當提及是否會為社會、國家發展做出貢獻、承擔責任時,許多大學生表示不知如何去做,但表示樂于為社會、發展貢獻個人力量,由某一角度來看,行動力是當代大學生所缺失的,這也直接影響著其就業價值觀的樹立。
3 高職院校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的影響因素
3.1 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構性因素
基于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的研究由來已久,早在1992年,也就是中共十四大中,便初步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次改革主要指的是由計劃經濟體制至市場經濟體制的演變,隨之的不斷推行,長期以來的“統包分配”的就業制度被剔除,一種全新的“自主擇業”觀念被樹立,正是在這一改革進程中,大學生的就業價值觀也在不斷“進化”[4]。
3.1.1 “自主擇業”觀念下的大學生就業選擇的盲目心理
“自主擇業”被提出之后,院校所給予的“鐵飯碗”質量大大降低,大學生可自由的選擇崗位,可以與用人企業處于平等地位進行雙向選擇。這一就業模式更加符合當代朝氣蓬勃的大學生,為其擇業的自主性創設了良好的大環境,這是“自主擇業”為大學生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但同樣也伴隨著負面影響,表現如下。
其一,在“自主擇業”剛剛開始實行時,高職院校并未有意識地進行相對應的知識補充,大學生不具備適應社會需求、市場要求的條件,知識儲備不足,即缺乏完備的就業準備;其二,用人企業由最初人員招聘的“被動接受”直接轉化為“主動選擇”的位置,變化之快,使得原有的聘人標準、政策法規已不再適用,卻未形成新的標準體系。在此種現實條件下,大學生將“經濟報酬”作為就業選擇時的主要標準,除去離家遠近、家庭原因等外界客觀條件,對于自身的“專業匹配程度”“職位上升空間”“就業質量”等因素缺乏綜合考慮;由于大學生的認知偏差,其基于薪酬設置了較高的期望,且這種情況至今未得到有效改善,使得“跳槽”情況時有發生,大學生就業人格有待進一步提升[5]。
3.1.2 “產業結構”改革后的大學生職業規劃的缺失實況
經濟體制充分轉型之后,國內的經濟步入了高速發展時期,科技、投資行業成了支柱型產業,此種改變大大節約了人工勞動力,這主要影響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再加之經濟發展周期的轉變,那么,原有的以勞動力為主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勢必也會隨之改變。
據有關資料顯示,近年來,我國基于高新技術的人才需求逐年遞增,新增崗位也多要求人才的綜合能力,這對高職大學生的知識儲備、應用技能、人格修養提出來更高的要求。但是,部分大學生對于市場發展缺乏了解、在職業規劃方面缺乏意識,使得其能力難以達到崗位所需,這也直接致使了結構性失業現象的發生,即大學生發愁找工作、用人企業招聘難。
產業結構得以優化調整后,“技能型”人員成了“炙熱人物”,隨市場基于此類人才需求的持續性遞增,傳統行業中的“精英”不再搶手,這也正是時代不斷發展的最好證明[6]。而大學生在選擇就讀專業和院校時,未能夠結合各方面條件進行充分考慮,也未能夠科學的制定職業生涯發展規劃,所以,極大一部分大學生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現實性尷尬局面。
最近幾年,在教育教學改革的推動下,部分大學生有意識的調整了自身定位,且針對個人職業發展做出了合理規劃,在就業上不再“一條路走到底”,而是進行了多元化的嘗試,在工作場所及業務上進行了拓寬。因而,這部分大學生實現了成功就業,甚至是開始了自主創業之路。
3.2 經濟社會轉型的價值觀因素
經濟社會轉型,主要表現在社會層級、人口城鄉結構、主流意識形態等方面,這些方面的改變,助推著我國社會逐步步入一種開放化格局。
3.2.1 市場經濟價值觀念的直接影響
就業體制改革初始階段,長期以來的“官本位”的價值觀和經濟社會下的“利益至上”的價值觀產生了矛盾。在前者的影響下,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更多的是偏向“公務員”等職位,或者以進入國有企業為就業目標;而在后者的影響下,大學生在就業區域的選擇上比較傾向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無論在任何時期,這兩種持有相對極端的價值觀念的大學生均不在少數。但是,勢必會伴隨著十分慘烈的競爭,即一個崗位多人角逐等;人才聚集,表現為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人滿為患”,而西部偏遠地區的“無人問津”。
3.2.2 社會輿論價值傳播的間接影響
2003年,一則以“北大才子街頭賣肉”為主題的新聞事件引發了社會熱烈討論,當時的輿論近乎一邊倒,即名牌大學生賣肉,屬實是大材小用,當時的評論清一色的不可置信、難以理解。可見,在那個年代的就業價值取向是以“社會地位”為主要標準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大多數學生為之后更好的就業,會選擇一些“熱門專業”,往往忽略了自身的興趣。此外,帶有有色眼鏡看待高職院校的家長、學生不在少數,他們認為:只有學習不好的才會進高職、只有考不上大學的才會上高職,我們不可否認,高職學生的文化課成績確實與本科院校存在一定差距,但術業有專攻,作為以培養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為辦學理念的高職院校,可更好的兼顧學生的個人興趣,為其之后的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而分析這些思想的背后,無不體現著重名利的就業取向。
隨時代的進步,大眾媒體基于就業價值取向的引導也開始發生改變,社會各方針對職業教育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觀。大學生也不再以“社會地位”和“經濟報酬”作為就業選擇時的唯一依據,而是朝向多元化發展。
3.3 高職院校及家庭因素的影響
3.3.1 高職院校擴招的現實性困境
在國家政策及教育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我國的高等教育以由以往的“精英型”教育逐步轉向“大眾化”普及教育,各地區均開設了多個高職院校。大學生以往“人上人”“高經濟收入”的標簽逐漸被掀下,就業市場也在發生著改變[7]。至此,大學生遭遇了兩大前所未有的困境。
其一,“畢業即失業”的現實性困境。由21 世紀初期至今,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并未得到有效改善,這一前局面是否由高等教育擴招所導致的,社會上并未形成共識。但毋庸置疑,二者勢必存在某種聯系,但由各年度高校的畢業總人數上進行分析,這一數量是逐年攀升的,應屆畢業生人數不斷增多,就業數量也在上漲,由此所導致的職位競爭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就業困難的形勢。而為應對這一改變,諸多大學生選擇了一種折中的形式,即“先就業,再擇業”。具體表現為:先選擇一家企業或單位“應付當下”,再慢慢涉獵其他“優秀崗位”,一旦與意向企業達成共識,便跳槽。
其二,高職院校專業課程設置的不合理。高等教育的擴展,更多的是由政府主導,對于各大高校而言,缺乏前期的準備工作。也正是因為如此,擴招之后的高職院校仍保留著原來的專業課程設計,缺乏創新。且缺乏基于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指導,只是一味地灌輸理論類課程,實踐操作課時較少,這也不符合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使得高職教育的質量大大下降。
3.3.2 家庭資本方面的深層次影響
由社會學的視角來而言,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選擇均與成長環境、家庭教育相關,即可以由一個人的選擇決策中感知到其背后的原生家庭影響。就業是大學生的人事大事,其的決策也不可避免的摻加了家庭其他成員的意見,也就是說家庭的社會資本、經濟條件、文化情況均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大學生的就業價值觀取向。
“關系社會”是中國文化心性的一個重要表征,“關系”用學術語言來表述即為法國正如家布迪厄所說,大學生自身所具備,或者說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存量,直接影響著其就業選擇。先賦性社會資本,即上一代所給予的,是影響大學生選擇的關鍵性因素,一般而言,這一資本是大學生“與生俱來”的,也是區別于其他人的主要因素,這往往會在潛意識里驅使著他們產生與同齡人的不同就業價值觀取向。大學生在完成學業后,即需要面臨人才市場的激烈競爭,這種先賦性的社會資本會為其提供便利[8]。除此之外,大學生在擇業中,是必會伴隨著一系列的花費,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住宿費、通信費、個人形象包裝費等,在這里我們姑且將它們概括為“求職經濟”。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有大量的研究證實求職費用的多少并不會直接地影響到畢業生的求職,但站在就業價值觀取向的視角上進行分析,會存在一定的影響。具體而言,求職費一方面也反映著大學生的家庭經濟資本,有了這一原因,大學生必然會針對就業抱有某種期望,在中西部十省高校貧困生就業愿景的調查結果也顯示:貧困生、非貧困生在意向企業、單位的選擇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前者以“事業單位”作為最優選擇,而后者則是更加看重用人單位是否為“外企”或者“政府機關”,這也就證實了家庭資本會對大學生的就業價值觀取向產生深層次的影響[9]。
4 結語
就業難已上升為普遍的社會性問題,其關系著我國的民生發展,也直接影響到大學生個人及其家庭的良性化發展。當前,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已成為教育界的研究熱點,這應當引起各大高校、政府部門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