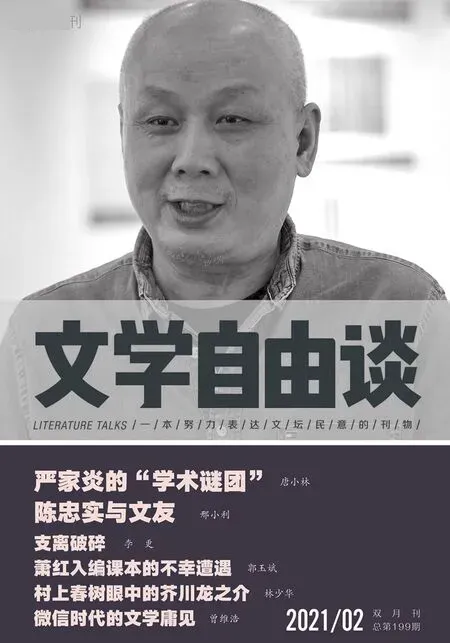“文人子弟”與“文人弟子”
□狄 青
索菲亞十八歲的時候嫁給了三十四歲的列夫·托爾斯泰,之后數十年間,先后為這個男人生了十三個孩子。起初托爾斯泰是想把索菲亞改造成為他精神上的“同路人”的,但遺憾的是,終其一生,索菲亞深深愛著卻又始終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丈夫,他遂把希望轉向了自己家族的子弟們。他用自己編撰的《識字課本》《閱讀園地》等教材來教授這些孩子,并讓他們與農民的孩子一起在他創辦的“草鞋學校”里上學,而老師就是他自己。托爾斯泰希望自己的“二代”們能夠身體力行去改良社會,而且不僅僅是改變農奴制。
對于中年以后的托爾斯泰而言,文學創作只是實現改良社會的訴求手段,金錢與所謂名望在他的創作中幾乎不占份量,就像他在《懺悔錄》中所說的那樣:“雖然我已經很清楚地認識到作家信仰就是欺騙,并且拋棄了它,但是人們由此賦予我的頭銜我卻沒有拋棄:詩人、藝術家、導師。我竟然天真地以為,我就是詩人,就是藝術家,就是導師了。”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翻臉,其中一個原因是屠格涅夫要把自己的女兒培養成上流社會的名媛千金。一次聚會,托爾斯泰當眾指出屠格涅夫培養女兒的方式是錯的,而這個女孩恰巧又是屠格涅夫的私生女。托爾斯泰說:“如果她是你的合法女兒,你就不會這樣教育她了。”為此,屠格涅夫險些跟托爾斯泰動起手來。
事實上,無論是托爾斯泰還是屠格涅夫,都沒有設想抑或希望把他們的“二代”培養、扶植成為詩人、作家,二人的后輩子弟中也的確沒有人靠文學創作揚名立萬。雖然幾十年后,阿·托爾斯泰自稱與列夫·托爾斯泰系本家,但他與列夫·托爾斯泰毫無交集,二人的世界觀也相距千里。我想,這可能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皆系貴族出身有關,他們包括其“二代”的生計都無需稿費和版稅來支撐,只是與他們的創作理念關聯很大,那便是,文學本質意義上并不是一種供人安身立命乃至風光無限的行當。即使放眼文學史,能拿出來的父子相傳的例子,基本上也只有大仲馬和他的私生子小仲馬,還有寫“兔子系列”的厄普代克——他的母親是一位專欄作家,盡管名氣不大。在世界文學史上尋找成功的“文二代”范例,遠比某些人想象的要難得多。但凡讀過安德烈·莫洛亞《三仲馬》一書的人都清楚,當年小仲馬寫作的初衷,恰恰是源于其經濟上的捉襟見肘。他從父親那里學到了靠寫作擺脫經濟窘境的方法,且對此也并不諱言。很多作家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并不希望子弟傳承自己的“文學基因”。塞林格寫作的房間,他的兒女是絕對不能踏入半步的;馮內古特因為崇拜馬克·吐溫,也給大兒子取名馬克·吐溫,但他從不與兒子交流任何文學話題;狄更斯的前妻給他生了十個孩子,竟然沒有一個借老爸的名望來經營個人事業的家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唯一的兒子少時倒是喜愛寫作,但即使在因身體原因被英國皇家海軍“刷”下來后,吉卜林仍然通過個人關系,將他送到英國陸軍赴歐洲戰場參加一戰,只因為吉卜林覺得,作為男人,沒有比上戰場更合適他去做的……
在我小時候,流行過一個詞語叫做“頂替”。實行“頂替”政策的單位,基本是國營和大集體性質的廠礦企業,以及部分機關、小集體企業。所謂“頂替”,就是父母退休或者提前內退,讓兒女去頂替他們的工作資格。此可算是彼時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良策。“頂替”頂的是工作機會,未必是工作崗位,所以就經常有干部的子女當了工人,而工人的子女也有可能會做干部。這里面,托關系走后門的事情肯定有,但較之后來,比例還是要少很多。我就知道一個電焊工的孩子,因為能寫能畫,“頂替”進廠后,直接進工會做宣傳干部。這些“頂替”的年輕人統稱為“子弟”。所謂“子弟”者,不只包括兒、女、弟、妹,也包括子侄輩。要說他們一點兒沒受照顧,肯定不客觀,畢竟都有父母和叔叔大爺的人脈在,但與我們當下所說的“子弟”抑或“二代”還是有明顯不同的。如今,但凡媒體十分關注、群眾紛紛“吃瓜”的“二代”,基本上都在有利可圖、有名可沾、有內幕可挖的行當,你看有誰會盯著產業工人的“子弟”和種田老農的“二代”不放來著?
我們今天所說的“文人子弟”也好“文人弟子”也罷,原本屬于衍生概念,系諸多“二代”中的一類。由富二代、官二代、學二代、演二代、畫二代,再到文二代,“二代”的范疇基本囊括了社會上所有熱門的“行當”。就說“文二代”吧,有人總把“三曹”“三蘇”拿出來說事兒,實際上古代但凡在官僚階層混的,廣義上都屬于文人,因為舞文弄墨是最起碼的要求,而平民百姓舞文弄墨的不多,所以說,古代的“文二代”更多的是指精神意義上的傳承。但現在則完全不是一回事兒,多半是利用“代際優勢”而具有了財富性的訴求。“文二代”可以更輕易地進入官方體系,同時也有更多機會被商業體系和金錢衡量體系所接納,因而占據了稀缺的社會資源。如今有很多老畫家,經常以辦父子畫展、母女畫展的方式,利用權力和影響力,為下一代盡快上位創造條件;一些老作家老詩人亦然,以開研討會、做活動的方式,來為自己的“子弟”和“弟子”助力。相形之下,沒有背景的平民百姓子弟,想要在這個圈子里站住腳,原本就十分困難,如今更加千難萬險。
2020年6月,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冊“文學家風”系列叢書,每冊都由女兒和父親共同創作完成。特別的是,這四冊書的爸爸們都是國內較有名氣的作家,四個“二代”也是赫赫有名。不能說出版社功利,在紙媒出版持續低迷的大背景下,如此運作,當然也是為了更好地吸引各方眼球。對于許多“文二代”來說,選擇一條和父輩相似的道路,或許不能夠使他們在文學史上占據一席之地,但足以令他們在現世活得衣食無憂甚至風生水起。有人說,目前的“文人子弟”實際上也不多。正所謂“河里沒魚市上找”,倘使你去各地作協訪訪,去里面閑散的科室或掌握發稿權的刊物編輯部調查一下,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屬于“文二代”了。
與其他“二代”們相比,“文二代”及文人子弟們即使拼爹,也多半不會拼得大張旗鼓,至少不會出現“我爸是李剛”那類新聞熱點,但也架不住周圍始終有各類幫閑文人起哄架秧子。原本有人的確是想低調做人的,結果被爭先恐后前來捧臭腳、蹭熱度的這個家那個家“出賣”了。記得某“文二代”的處女作出版時,新書的腰封上赫然列著長達三十人的推薦名單:鐵凝、余華、蘇童、阿來、方方、吳亮、陳思和、陳忠實、馬原……陣容之豪華,幾乎涵蓋了中國小說界、評論界所有具有話語權的人。倘若沒有“主席+主編”的“文一代”父輩,這三十個人能請出一位來,都非易事。倒是該“文一代”說得清楚:孩子從小就跟這些作家前輩們認識,他們也就都愿意出來幫個忙。
據說,評論家陳曉明先生多年來一直都殷切關愛著“文二代”茁壯成長的歷程。他說:“這些‘文二代’出手都很高,比起同齡人,他們的寫作也更有特點。有意思的是,這些‘文二代’的寫作風格與他們的父輩大都相去甚遠,從這一點也看到了他們的叛逆性。”關鍵是,陳先生是如何判斷出“二代”們比同齡人更有特點呢?如果“文一代”用傳統現實主義創作出的是“高玉寶”,其子弟和弟子還會用同樣手法接著創作“高玉寶”嗎?實際上,除了“文人子弟”外,如今的“文人弟子”也是某種身份的“標識”。隨著“創意寫作”專業本碩博學位在大江南北遍地開花,隨著“作家班”此起彼伏地開辦,誰教過某某某、某某某是誰的學生、某某某畢業或結業于某院系的某一屆,便成為一種師長與弟子之間的“互認標識”,也就有那么一些刊物,每期所發表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多一半都是作家導師推薦來的自己“弟子”的作品,對作品的評論有的甚至就是導師親自操刀的。
大家知道,如今,書籍不好賣,書號更是緊張。一位文壇新兵想要出書,已是千難萬阻,想要興師動眾大動干戈地宣傳,更如夢幻泡影。當下喜歡寫東西的人多了去了,寫的好的人也不在少數,而往往只有“文人子弟”與“文人弟子”得以直接進入關系圈。我認識的一個文人子弟,大學畢業后一直高不成低不就地混跡于四五個行業,哪都干不長,結果還是被作協收納,以“文二代”的身份,不長時間就風生水起了。
當所有人對此都假裝看不見,甚至謀劃如何能與之利益均沾的時候,有人站出來,對某些“文二代”的作品提出質疑,卻又有某些掌握話語權的這家那家急火火地跑出來站臺。說實在的,我以為他們多半是“站”給與他們利益相關的“文一代”們看的,因而行動必須迅速,立場必須鮮明。“文二代”能成這般蔚為大觀的氣象,實際上與書商和院所助力炒作也有關系。要拿到“文一代”的稿子,要被接納和認可并進入某些“文一代”把控的文學評價體系,要靠“文學子弟”和“文學弟子”的名分炒作賺錢,他們當然要出來為“文一代”的子弟和弟子們站臺。我就聽過一位作家講:“某某那是我學生,咱的人,他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和我說,還是要愛護。”他沒說錯。他嘴里的青年作家某某在某大學讀“創意寫作”,該作家被邀請去講過幾堂課,并與某某結了“一對一”的對子,當然就算是這位青年作家的老師了。
當“文人子弟”與“文人弟子”占據了大量的稀缺資源、控制了相當一部分展示平臺,你讓其他人一點兒沒有想法,的確是不人道的。當然,一定會有人告訴你說:你就不能有這種想法,人家某某的媽媽一年賺的錢夠你媽媽五十年賺的錢,這就是國情啊,你受得了受,受不了滾!而且,往往還會有滿嘴雞湯的道德義士站出來,說:有本事你寫得比誰都好啊,就不信誰能埋沒得了你!你看誰誰誰最早就是一個農民,人家如今都是作協主席了……這種話,你要說完全沒有道理,說明你這人不講道理;可你要說他們講的就是真理,它還的確不是真理。有許多事情只能屬于個例,沒有復制的可能性。就像每個說相聲的孩子都想像郭德綱一樣成功,可郭德綱就是一個個例,你無法復制他,這和你是否努力了、努力夠不夠關系不大,也和你是否說得不如郭德綱好關系不大。幾年前,郭德綱回天津探親,我與他有過一次接觸。他說,誰也別跟誰比,你命里沒有嘛,白搭。我理解他說的話。比方說天津是一個“相聲窩子”,可你讓天津再出來一位單槍匹馬去北京闖世界的主兒,即使他比老郭更努力更勤奮,但想要再造一個“德云社”出來,怕是也難上加難,搞不好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都說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不過我想說的是,既然有權威人士有相關媒體總是在給如今遍地的“文人子弟”和“文人弟子”們披上各種合理化的外衣,也就必須接受被指點被指摘的結果,況且明明就是有那么多可被指摘的東西擺在那里,哪有不讓人指摘的道理?我還以為,文學圈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父子兵、母女團來襲,有那么多放著其他營生不干,偏往文學圈里扎堆,且四處認師拜祖的“文學弟子”,第一,說明當下的文壇的確是有名有利可圖,第二,說明與其他行業比較,文學圈的門檻更低,也更加好混,且風景獨好——當然這是在你掌握了相當一部分資源的前提下。我不是說“文學子弟”“文學弟子”都寫不好。確有“二代”寫得很好,但相比于烏央烏央享受著“文一代”蔭庇的“文二代”來說,在文學創作上表現出色的,在作協系統編刊編得出彩的,同樣是鳳毛麟角。既如此,就不能想想辦法,讓“二代”們去干點別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