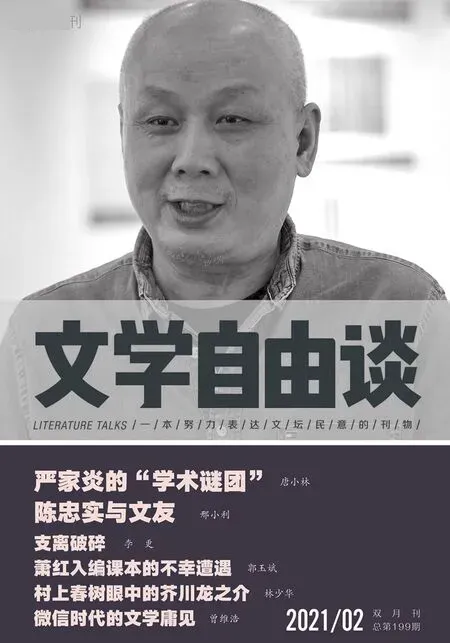潮聲書影總關(guān)情
□南北萍
打開倪斯霆先生新著《文壇書苑憶往錄》,仿佛打開了通往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春潮涌動(dòng)中的文藝百花園的大門。在那“有夢(mèng)有理想、有詩(shī)有文學(xué)、思想解放洪流和新啟蒙浪潮相互交織波濤洶涌”的年代,作者初出校門,即幸運(yùn)地成為傳遞文壇與出版春色的《天津書訊》報(bào)的記者、編輯。如同辛勤忙碌在百花園中的蜜蜂,他捕捉文壇訊息,采訪文藝名家,為《天津書訊》成為同類報(bào)刊中的佼佼者傾盡心血,也積累了大量采訪素材。隔著二十幾年的時(shí)光回望,文壇往事,出版珍聞,連同豐富難忘的激情記憶,如大潮余波沖擊心海,如交響樂后余韻不絕。回憶,懷念,遙想,催生了這本回憶與感悟的《文壇書苑憶往錄》。
全書圍繞懷舊憶往和留存史料兩大主旨展開。在懷舊憶往的文字里,作者以抒情散文的筆法,打開了記憶與情感的閘門。在《岳野憶謝添導(dǎo)演電影〈水上春秋〉后的遭遇》一文中,倪斯霆記錄了為電影主題采訪岳野時(shí),岳老講述與天津淵源時(shí)的回憶:1949年5月5日,岳野作為華南青年代表團(tuán)二十八個(gè)成員之一,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從香港乘船,秘密經(jīng)天津到北平參加全國(guó)第一屆青代會(huì)。當(dāng)輪船駛?cè)刖嗵旖蚴袇^(qū)東南六十公里的海河入海口時(shí),他們貪婪地望著兩岸解放了的土地,搜尋著入京咽喉上以“威、鎮(zhèn)、海、門、高”五個(gè)字命名的五座炮臺(tái)遺址。當(dāng)輪船終于靠上了碼頭,當(dāng)他們把密藏的“華南青年代表團(tuán)”的紅旗舉起,當(dāng)與早已等候的大會(huì)接待組的同志握手擁抱的時(shí)候,他們都熱淚滾滾地哭了起來。作者寫道:“岳老的講述一下子感染了我們,于是立即約他將這段情感和以后與天津的往來寫出寄給我們。華燈初上的夜晚,當(dāng)我們返津時(shí),都為能意外約到一篇好稿而興奮。”眾所周知,天津大沽炮臺(tái)是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來與侵略者多次血戰(zhàn)的陣地,直至1900年八國(guó)聯(lián)軍再次攻陷大沽炮臺(tái),并長(zhǎng)驅(qū)直入北京。近代以來亡國(guó)滅種的巨大危機(jī),讓中華無數(shù)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浴血奮爭(zhēng),才迎來民族解放和新中國(guó)的誕生。這段感情充沛的詩(shī)意描寫,讓讀者被深深地感染和打動(dòng)。
在史料留存方面,倪斯霆?jiǎng)t以理性冷靜的筆觸展開記述,力求史家之筆的客觀嚴(yán)謹(jǐn)。如,韋君宜《回憶“天津書局”》一文本來較短,倪斯霆對(duì)它的“補(bǔ)正”卻頗長(zhǎng)。作者鉤沉發(fā)微,發(fā)揮出版史研究的專業(yè)特長(zhǎng),對(duì)民國(guó)時(shí)期天津書局、出版以及有關(guān)書店的史實(shí)詳加考證,補(bǔ)正缺誤,可謂民國(guó)到解放后天津出版的出色論文。再如《柳萌“忘不掉”50年代初的津門“書香”》一文,從柳萌來稿和作者親身經(jīng)歷兩方面,介紹了天津和平路、濱江道等繁華街道上書店曾經(jīng)的密集興旺,引出解放初期為加強(qiáng)文化宣傳,軍管會(huì)給予新華書店對(duì)繁華街道店鋪優(yōu)先選擇權(quán)的珍貴史實(shí)。文章結(jié)尾處,寫到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后繁華街道上新華書店紛紛摘牌易主,變成商店賣場(chǎng),商業(yè)擠走文化的現(xiàn)實(shí),發(fā)人深思。
全書以人為線索,脈絡(luò)分明,繁簡(jiǎn)得當(dāng)。豐贍詳實(shí)的細(xì)節(jié),讓四十幾位名家立體、鮮活。這得益于倪斯霆采訪前做足功課、提問有的放矢、記錄認(rèn)真扎實(shí),由此留下的寶貴詳實(shí)的文史資料,多年后追憶,仍現(xiàn)場(chǎng)感爆棚。如,作者代父親接受王愿堅(jiān)軍禮、部隊(duì)干部提出的三個(gè)要求對(duì)王愿堅(jiān)創(chuàng)作的影響;“我”作為初出茅廬的小字輩首訪孫犁的背景原因,以及采訪中孫犁由起初的嚴(yán)肅寡言,到得知“百花”新推《孫犁文集》發(fā)行良好后的反應(yīng),交談中講述的“趣事”“故事”等等,讀來生動(dòng)真切,絲絲入扣。
隨作者領(lǐng)略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的同時(shí),對(duì)名家了解的深入也是讀者閱讀的重要收獲。《沈從文在天津的“乞醯”之舉》圍繞沈先生1947年在天津《益世報(bào)》任職時(shí),為求助的青年作者寫字義賣,幫其家庭度過難關(guān)的往事,寫出了沈先生的厚道、善良,是他處難以看到的珍貴史料;而《柯原憶天津“黎明”前的〈民生導(dǎo)報(bào)〉》一篇,又從“乞醯”事件所救助的詩(shī)人柯原的角度著墨,與記述沈從文“乞醯”的文章形成互文之妙。《柳溪談〈大盜“燕子”李三傳奇〉寫作緣起》寫到,柳溪看到當(dāng)時(shí)有些年輕人,因?yàn)闆]有經(jīng)歷過舊社會(huì),產(chǎn)生錯(cuò)誤認(rèn)識(shí)甚至信仰危機(jī),嚴(yán)重者走上犯罪道路,感到痛惜。因此,柳溪在長(zhǎng)篇小說《功與罪》的寫作中,穿插了“燕子”李三的相關(guān)素材,并藉此探索文學(xué)的民族化、通俗化,產(chǎn)生了良好的社會(huì)效果——作家之良苦用心,令人肅然起敬。
作為在《天津書訊》做記者編輯十五年的回顧總結(jié),本書涉及了眾多名家的重要作品,其中不乏有搜尋閱讀價(jià)值的書目,如梁斌自傳《一個(gè)小說家的自述》,張贛生的《中國(guó)戲劇藝術(shù)》《民國(guó)通俗小說論稿》,倪鐘之的《中國(guó)曲藝史》《曲藝民俗與民俗曲藝》,柳溪的《功與罪》,聞樹國(guó)的《徘徊在書外的感覺》,等等。從這點(diǎn)看,本書堪稱《天津書訊》的匯總拾遺和好書推介,為作者傾注多年心血的職業(yè)生涯,為如詩(shī)如歌的激情歲月,畫下了濃墨重彩的句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