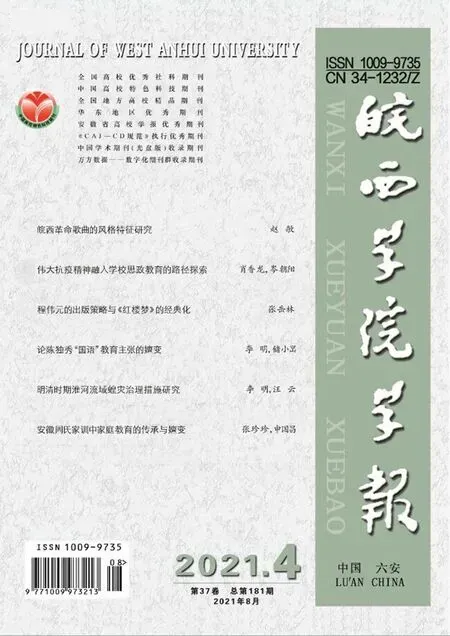程偉元的出版策略與《紅樓夢》的經(jīng)典化
張岳林
(皖西學院 文化與傳媒學院,安徽 六安 237012)
《紅樓夢》為社會所知,普及到大眾,強力占有市場,甚至衍生為一門研究學問——紅學,這都有賴于程偉元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出版發(fā)行的程甲本,以及次年修訂出版的程乙本。這結束了《紅樓夢》在少數(shù)人手中傳抄的秘密歷史,而開啟了《紅樓夢》的普及征程。
一、程偉元的出版策略
那么,程本何以能橫空出世并贏得市場?這固然與小說自身的價值有關,卻更有賴于程偉元的出版策略。
為論述方便,茲引程偉元序如下[1](P45):
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shù)過。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shù)金,不脛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傳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只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
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shù)年以來,僅積有廿余卷。一日偶與鼓擔上得十余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翻閱,見其前后起伏,尚屬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全書始至是告成矣。書成,因并志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為快者歟?
小泉程偉元識。
從序文看,《紅樓夢》的出版程偉元首先堅持了全璧策略。因為此前手抄本只在少數(shù)人手中傳抄,如怡親王府等,并不為社會大眾所知。程偉元直接推出前八十回,或宣稱就是原稿也是可以的。但他強調原本“一百廿卷,今所傳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增加了《紅樓夢》流傳的神秘性,引起了人們對后四十回,以至全書原本的閱讀期待。并且他把搜求“數(shù)年”(這說明他耐心等待了數(shù)年)“僅積有廿余卷”,直到“一日偶與鼓擔上得十余卷”的“原稿”約請人補成全書后,使《紅樓夢》最終以全璧的形式面市,這是《紅樓夢》出版史上的濃墨重彩的手筆。
其次是突出精品意識。因從鼓擔上購得的書稿“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全書始至是告成矣。”其實何止后四十回的殘稿,就是手抄本之間文本差異也很大,“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紅樓夢引言》)[1](P46),加之轉相抄閱,錯訛很多,這從今存的十一種手抄本來看,就很明顯。而程甲本的出版,“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訂,間有紕漏。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惟識者諒之。”(《紅樓夢引言》)程偉元的自述說明他有清醒的精品意識,顯然他不滿足于僅僅追求商業(yè)利益,而是立即再次修改,推出從文字到細節(jié)質量都更高的程乙本,這正是精益求精的結果。他強調“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為厘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紅樓夢引言》)表現(xiàn)出對原文的尊重。求“善本”,出“善本”,這都是追求精品意識的體現(xiàn)。因為,當時很多書商為了謀求商業(yè)利潤不惜作假,刻書業(yè)亂象叢生,如閩刻圖書。晚明謝肇制說:“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制劇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坊,刻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惡濫,蓋徒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騷騷蹈此病矣。”[2](P275)這種狀況到乾隆后期改觀不大。而程偉元的做法對當時圖書出版不僅具有正面引導的作用,對《紅樓夢》的傳播聲譽的影響也是積極的。
其實,不論他約請高鶚續(xù)寫《紅樓夢》后四十回的說法真實程度有沒有問題(現(xiàn)代學者認為高鶚可能只是參與了后四十回的整理),他都為我們奉獻了不乏精彩情節(jié)的后四十回,從而使《紅樓夢》以全本的形式面世,開啟了《紅樓夢》成為經(jīng)典的傳播過程。
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是,后四十回有兩個情節(jié)處理非常出彩。一個是“林黛玉焚稿斷癡情”;一個是“散余資賈母明大義”。前一個情節(jié)的處理增加了矛盾沖突的強度,增加了情節(jié)的戲劇性,凸顯了封建家長的冷酷無情,使得黛玉形象具有更強烈的悲劇性。后一個情節(jié)的設計對表現(xiàn)賈母的遠見卓識、深藏不露、沉著冷靜,計劃周密等,起到了形象再造的作用。這些成功的改動,對《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和成為文學經(jīng)典顯然有提升的作用。
再次是精準的市場定位。作為一個商人,程偉元有明確的市場普及預期。“書成,因并志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為快者歟?”“先睹為快”,產(chǎn)生市場反應,實現(xiàn)市場占有,直至實現(xiàn)經(jīng)濟目的,這是一般商人都有的心理。從程本引言看,在程偉元之前,《紅樓夢》“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紅樓夢引言》),是少數(shù)人的收藏品,一直不為大眾所知。其時,“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shù)金”,成為少數(shù)人的可居之奇貨。據(jù)考證明代舒載陽刊刻的《封神演義》,封面上有“每部定價紋銀貳兩”的木戳。這在萬歷時期能購米三石有余[3](P173)。而“乾隆五十年(1785)蘇南大旱,每升漲到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無論荒熟,‘總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為常價矣’”[4](P7)可見乾隆后期米價之高。清人毛慶臻說:“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紅樓夢》流行江浙,每部數(shù)十金。致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兩”(《一亭考古雜記》)[1](P30)。這證明了程偉元刻印本出版后,對書價的影響。其實,清朝乾隆末期,政治積弊已深,社會經(jīng)濟大不如前。如此,“數(shù)金”的書價遠不是一般讀者可以消費得起的,這會影響《紅樓夢》的普及。故程偉元發(fā)行《紅樓夢》時刪除了脂硯齋等的批語,并明確申明:“是書印刷,原為同好傳玩起見,后因坊間再四乞兌,爰公議定值,以備工料之費,非謂奇貨可居也。”(《紅樓夢引言》)這樣《紅樓夢》的書價降到二兩以下,以當時平均三兩一石的米價計算,價格已大大地降低了(以米價算,不及萬歷時米價的四分之一)。再從程本刻印發(fā)行以后在社會迅速普及的程度看,程偉元的普及預期是實現(xiàn)了的。到光緒年間,“今年六月初間,……萬選書局石印之《金玉緣》二千五百部”,且“距本月中(十八年秋),聞何(書販何秀甫)在他埠,已將書銷完,又托萬選覆印等情”。(《紅樓夢因禁改名金玉緣印行》)[5](P162)可見程本當時發(fā)行量之大,銷售之速,自是書價下降的直接結果。
至于《紅樓夢》發(fā)行后,很快流行,引起士人的注意,并興起一股評點《紅樓夢》的熱潮等傳播狀況看,這恐怕已超出程偉元的預期了。
最后是廣告手段。刻書請名人作序,本身就是廣告意識的體現(xiàn)。程偉元約請高鶚續(xù)書,恐怕主要是借重高鶚的名聲。高鶚的序說得已很清楚:“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幾廿余年,然無全璧,無定本。向曾從友人借觀,竊以染指嘗鼎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仆數(shù)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閑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謬于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奴見寶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識端末,以告閱者。時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鐵嶺高鶚敘并書。”[1](P45)以今天《紅樓夢》的聲譽來看,讀者或者無法理解程偉元約請高鶚的動機。但以程本刻印時代來說,屬于稗官野史的《紅樓夢》并不為一般人所重視,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作者曹雪芹語焉不詳?shù)氖鹈麊栴}了。
而故事化后四十回的發(fā)現(xiàn)過程,同樣可以起到廣告作用。原書殘缺,“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只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撼。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shù)年以來,僅積有廿余卷。一日偶與鼓擔上得十余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翻閱,見其前后起伏,尚屬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傳聞的牽動神經(jīng),搜羅的竭力,偶遇的機緣等都是富有故事性的。這對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增加購買的欲望是可以起作用的。
至于“繡像”本插入精美的圖畫,也具有提高小說視覺影響力的作用。
與此同時,程偉元還有“便于讀者”(《紅樓夢引言》)的讀者優(yōu)先意識。讀者決定市場,讀者決定圖書的價值,讀者決定圖書的命運。為此他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降低書價。經(jīng)過整理,批量發(fā)行通行本,這降低了普通讀者的閱讀門檻。
二是整理、梳通文本,使《紅樓夢》由“漶漫不可收拾”變?yōu)橥ㄋ滓鬃x。
三是預設讀者為“海內君子”,隱含了理想讀者的預期。隱含讀者是敘事學理論中的一個概念,指作品的敘述預設了一類讀者,這類讀者對作者的敘述目的,內含的意旨能夠通曉。因此,作者的敘述本身即包含與這類讀者的對話和對讀者的期待。程偉元的“海內君子”,顯然就是理想讀者。預設對理想讀者“海內君子”的期待,這對《紅樓夢》的傳播是有意義的。隨后《紅樓夢》引發(fā)評點家們的大量評點,開啟了《紅樓夢》研究的新時代,這正是理想讀者登場的結果。
四是突圍正統(tǒng)觀念,肯定《紅樓夢》的閱讀價值,為《紅樓夢》的普及提供輿論基礎。高鶚序稱“紅樓夢”“不謬于名教”,就是以正統(tǒng)名教的名義為《紅樓夢》辯護。殊不知,《紅樓夢》恰恰是批判封建名教的。否則《紅樓夢》一出,引起封建文人的百般詆毀就不可解釋了。如毛慶臻曰:“作俑者曹雪芹,漢軍舉人也。由是《后夢》《續(xù)夢》《復夢》《翻夢》,新書迭出,詩牌酒令,斗勝一時。然入陰界者,每傳地獄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yè)力甚大,與佛經(jīng)之升天堂,正作反對。”[1](P704)類似這樣對曹雪芹的詛咒在當時還有很多,正從反面見出《紅樓夢》出版造成的社會轟動效應。而作者先期打下預防針,顯然有助于讀者的接受。
二、《紅樓夢》經(jīng)典化的本土語境
至此,程本的發(fā)行開啟了《紅樓夢》經(jīng)典化的歷程。在小說被視為“稗官野史”的時代,宣稱《紅樓夢》“不謬于名教”,“詞意新雅”,具有“膾炙人口”的閱讀效果,這有利于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高鶚以舉人身份,參與《紅樓夢》后四十回的修訂(雖然他是后四十回作者的身份存疑),同樣是對《紅樓夢》社會價值的肯定。隨著他中進士,步步高升,自號“紅樓外史”對《紅樓夢》的知名度也會有提升作用。
即從思想觀念上說,程本保留了曹雪芹對“稗官野史”、風月筆墨、“才子佳人”等小說的批評,寶黛愛情悲劇,以及賈寶玉“國賊祿鬼”“文死諫、武死戰(zhàn)”等等的議論,就是對作者觀念的認同。這也成為大眾默認的《紅樓夢》流傳的價值觀念。
再說后四十回榮國府發(fā)還,蘭桂齊芳等的描寫,雖遭指責違背了曹雪芹原意,與前八十回暗示的小說結局不同,但以當時的社會意識看,這易于為當時的讀者所接受。
重要的是,《紅樓夢》得以全璧面世,引起讀者的廣泛關注,這是《紅樓夢》得以經(jīng)典化的文本基礎。
嘉、道間評點派的出現(xiàn)就是以程本為前提的。1811年問世的東觀閣重刊《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距離程乙本發(fā)行不過二十年。重要的是王希廉等的大量評點,涉及《紅樓夢》的作者、思想內涵、藝術特色、后四十回、版本等方面,成為《紅樓夢》研究史的第一個繁榮時期(脂硯齋應屬于創(chuàng)作期的評點,非獨立意義的批評)。他們的觀點對揭示《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是發(fā)揮了作用的。我們試舉幾例:
張新之:“一部《石頭記》,計百二十回,灑灑洋洋,可謂繁矣,而無一句閑文。……有謂此書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觀其通體結構,如常山蛇首尾呼應,安根伏線,有牽一發(fā)全身動之妙,且詞句筆氣,前后全無差別。則所增之四十回,從中后增入耶?抑參差夾雜增入耶?覺其難有甚于作書百倍者。雖重以父兄命,萬金賞,使閑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耳以目,隨身附和者之多?”[6](P703)
劉銓福說:“《紅樓夢》非但為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金圣嘆皆未曾見也。戊辰秋記。”(甲戌本《石頭記》題記)[6](P10)
洪秋蕃說:“《紅樓夢》是天下古今有一無二之書。立意新,布局巧,辭藻美,頭緒清,起結奇,穿插妙,……斯誠空前絕后,嘎嘎獨造之書也。”(《紅樓夢抉隱》)[6](P10)
這些觀點對《紅樓夢》或有譽美之嫌,但如果我們不以今天的學術標準來評判的話,置于嘉、道時期的誨淫誨盜論盛行的語境中,則作者的評論不啻驚人之語。而“別開生面”“古今有一無二”“空前絕后”等評語,無疑把《紅樓夢》置于一個新的高度上,使其成為一種小說標準。由此引發(fā)的關于人物、作者的種種議論、甚至爭執(zhí),使《紅樓夢》成為一個經(jīng)久不衰的話題。這些也是《紅樓夢》經(jīng)典化的內涵之一。
至于由此引發(fā)了統(tǒng)治階級的驚恐,視之為“誨淫誨盜”,對之加以查禁,恰恰說明了《紅樓夢》的不符合封建思想的內涵,從反面強化了《紅樓夢》的經(jīng)典價值(也會刺激讀者,增加閱讀《紅樓夢》的欲望)。
反觀現(xiàn)代學者對《紅樓夢》經(jīng)典品格的確認,是以西方小說標準為依據(jù)的。鄭振鐸、俞平伯、胡適等人對《紅樓夢》最初的低評,就是以西方現(xiàn)實主義小說理論為參照的。而這背離了《紅樓夢》文本自身生成、傳播的歷史語境,造成對中國小說經(jīng)典自身生成傳統(tǒng)的淡忘。這是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的。
三、結語
總之,程本的刻印發(fā)行,其前現(xiàn)代出版時期的發(fā)行策略和市場運作,改變了《紅樓夢》的傳播方式,決定了《紅樓夢》的市場定位,開啟了紅學的發(fā)展,推動了《紅樓夢》的經(jīng)典化的歷程。難怪俞平伯先生臨終遺言:“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7](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