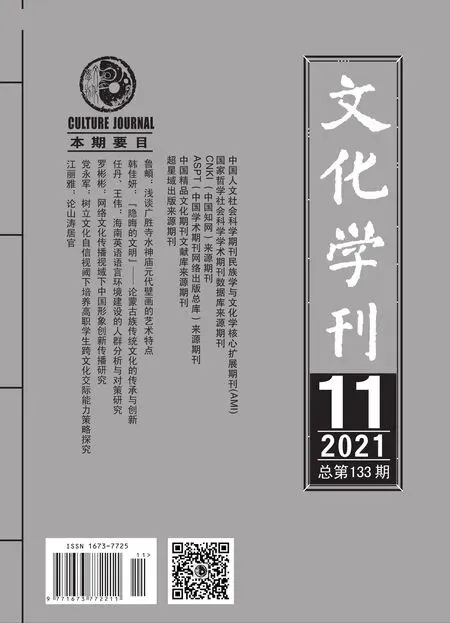基于互文理論的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研究
齊媛媛
一、引言
當前我國在國際舞臺中逐漸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國家層面充分意識到向其他國家推送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并將此提升到戰(zhàn)略層面。文學譯介在弘揚傳統文化過程中成為一種有效手段,不僅能讓更多國際友人了解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也能讓他們被中華文化所折服。為此,我國著手建設文學譯介工程。盡管文學譯介在我國備受關注,卻沒有取得良好效果。有些來自于海外知名作家的譯著吸引了大量中國讀者,中國作家的譯著卻沒有占領海外市場。結合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學者著手對文學譯介進行研究與分析,但現有理論成果的指導價值并不強。
二、文學譯介及其研究的重要性
在全球一體化發(fā)展的大背景之下,各個國家充分意識到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甚至將其視作能體現出綜合國力的關鍵指標。文化傳播不只是要把中華文化推廣到其他國家那么簡單,而是不同話語權之間的博弈。在中國文學與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文學外譯是重要路徑,完全有對我國的文學譯介進行深入分析與探究。
文學譯介雖然也是一種翻譯活動,但與其他形式的翻譯相比,譯者承受著較大的壓力,需要同時了解原語、譯語的文化背景,在翻譯的過程中要促進兩種文化的交流,采用最貼合譯文讀者需求的方式進行翻譯,就是要在譯語的文化體系之中與讀者一起分析原文的內涵[1]。在這一過程中,互文性是繞不開的話題,要把其他語言、文本等融匯到一起,使不同的語言與文化相融合。翻譯文本最能體現出互文性,在選擇互文翻譯策略時,一定要分析文學譯介怎樣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中找到合適的路徑,以最有效的方式進行表達。
三、基于互文性理論的翻譯研究
在對互文性與翻譯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時,國內外學界保持同步,都是從宏觀層面將二者相整合并進行分析,也運用了關聯理論、功能對等等理論,并從互文翻譯視角出發(fā)對如何選擇翻譯策略進行深入分析,尤其是異化、歸化等策略的提出,都是從新視角對翻譯進行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表明了翻譯策略如果能與互文性結合到一起,能體現出譯者在文化、翻譯兩個方面的傾向。在翻譯過程中,由于原文化對譯者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他們就會不由自主地將原文化融入譯本之中。只要把譯文、原文進行對比,就能直觀地看出在翻譯時譯者傾向于譯者還是作者。站在文化傳播立場上看,譯者會努力增強譯本的可讀性,要想在文化交流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一定要選擇一些更能滿足讀者需求的翻譯策略。翻譯活動不只是要用一種語言取代另一種語言,而要從文化與風俗習慣等方面進行交流,譯本之中會同時存在著譯者與原作者的聲音,從互文性視角出發(fā)對翻譯活動進行分析,能對翻譯的本質產生深刻認知,有利于翻譯活動的進行。
四、林語堂翻譯作品中涉及的互文性
筆者從廣義與狹義兩方面入手對互文性進行分析,逐一介紹互文性在林語堂翻譯作品之中的運用情況。
(一)廣義互文性的運用
從某種程度上講,林語堂的英文原作也是一種翻譯作品,只是把中國文化當成翻譯的內容。1939年,他在巴黎創(chuàng)作了《京華煙云》這部小說,介紹了自義和團運動以后北平三大家族之間的恩怨情仇,故事一直延續(xù)到抗戰(zhàn)時期。在寫這部小說時,林語堂運用的是英文,塑造的每個人物都獨具特色,是一部有著濃郁時代特色的小說。從廣義上看,互文性不只是要運用語言文字,而是兩種文化與風格之間的轉換。
《京華煙云》是一部能展現時代特色的小說,以歷史發(fā)展順序將一個個小故事串聯到一起,卻沒有讓人感到雜亂。林語堂用英文寫了這部小說,對特定歷史時期之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態(tài)進行了描述,介紹了中國人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可見,林語堂為西方讀者描述了中國的真實情況,這就是這部作品之中最能體現出互文性的內容。蘊含于這部小說之中的互文性,從廣義上看就是把多樣化的文化融為一體,把文化融入文本之中,使之與時代背景等渾然一體,在同一部文學作品之中介紹了不同的人生,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不管從哪一個視角入手進行分析,這部小說都向西方讀者展現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讓他們了解了真實的近代中國社會[2]。
(二) 狹義互文性的運用
從狹義上看,互文性即為明顯互文性,就是指一些能從文字層面上起到引用、參考作用的內容,這些內容均是有跡可循的。Hatim等(1990)把互文性劃分為自我引用、文學暗指等類型。在本研究中,對林語堂的英譯作品進行了梳理,認為主要包括如下幾種類型:
1. 用典
這種類型的互文性,就是指從一些眾所周知的傳說、成語、典故之中選擇可用的內容,以這種方式進行翻譯,讀者借助于自己熟知的典故等內容,了解原文的內涵。
例:原文:于縣官而言,打退堂鼓時最為快哉!
譯文:A magistrate order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 and calls it a day- Ah, is this not happiness?
這是一句出自于《不亦快哉》的內容,形象地道出了縣官在打鼓退堂時會感受到快樂。通常而言,退堂鼓就是指任務沒有完成時就產生了退縮感,封建官吏以這種形式表示退堂。這本是《竇娥冤》中的一個詞,在英文之中, "call it a day”為運用率較高的見習語,是指收工、停止的意思,運用這樣的習語,林語堂準確地闡述了原文的真正內涵,也運用另外的詞語對其進行補充,能讓讀者了解“打退堂鼓”的真正意思,即封建官吏以這種方式宣告下班,由此了解了中國的案堂文化。
借助于這個例句,我們能進一步感受到用典這種翻譯形式的真正內涵,即采用讀者熟悉的內容對原語文化進行描述,使讀者認知語境之中存在的空白得到補充,讓讀者能輕而易舉地了解原語文化。
2.注釋
從Genette的文本互文分類情況看,其中有一種把下文當成前文本,而圖表、注釋之類的內容則為派生文本。對林語堂的翻譯作品進行分析,了解到其在運用此類翻譯手法時,增加了一定注解,就是為了引起讀者的無限聯想,幫助他們消除閱讀障礙,使源語文化能得到廣泛傳播[3]。
例:原文:倩繪一像,挽紅絲,攜姻緣簿。
譯文:A picture, like a red silk [for the purpose of bind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couples], with the marriage book.
原文中用簡單的一句話描寫了月老形象,手牽紅線,也拿著姻緣簿。月老是中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專門負責指定人間姻緣,是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意象,有些情況下,中國人也會用紅線指代月老。西方讀者卻不了解這一點,他們從未聽說過“月老”這個人物,更不理解“紅線”為何物,如果只是簡單地對應翻譯,讀者在理解時就會產生疑惑。于是,林語堂在括號中對這些內容做出了補充解釋,讀者在閱讀中就能理解“紅線”的含義,將其與愛神丘比特建立起聯系。林語堂運用這種互文翻譯手法,讓讀者的文化空白得到了填補,對中西文化意象進行對比描述,能給讀者帶來感性理解,有利于促進文化傳播。
3.仿擬
這種互文翻譯方式較為典型,就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對人們熟知的語言表達形式加以仿照,尤其是習語、成語等,以此創(chuàng)造新的表達形式,激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在林語堂的翻譯作品之中,并沒有過多地運用這種翻譯手法,但僅有的幾個例子卻在文化傳播方面發(fā)揮出重要作用,具有借鑒意義。
例:原文:若作傳奇,將其稱為“吃粥記”矣。
譯文:If make legend, can name"eat congee to remember"carry on.
O. Henry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在英語國家產生了較高的影響力,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他寫了許多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林語堂在這個句子中就是對The Romance of a Busy Broker結構進行模仿,讀者只要看到“The Romance of the Congee”這樣的話,就會想到O. Henry小說中的內容。這兩種內容之間形成了較強的相似性,由此產生了關聯,讀者就會意識到在中國文學中存在著“……記”這樣的體裁。所以,這種類型互文翻譯手法的運用,能讓讀者簡單輕松地對原文傳遞的信息產生了解,進而達到文化繁榮、交流的目的[4]。
從廣義上看,文化交融是互文性的重要內容之一,也要通過互文性體現出時代因素與對受到其他文本的影響。從狹義上看,互文性只是局限于上述四種形式。如果能合理運用互文翻譯,能使讀者的認知范圍得到拓寬,從整體上對中國文化風貌產生理解,意識也會上升到新高度,而這樣的效果并非單純進行翻譯就能產生的。所以,譯者要想游刃有余地運用廣義互文翻譯形式,一定要具備融匯中西的能力。
五、結語
從文學譯介視角出發(fā),要想達到跨文化傳播與交流的目的,并非一般水平的翻譯人員所能達到的,譯者在跨文化交際能力方面都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要把握住不同文化的差異,掌握更為全面的互文性理論并在實踐中加以運用,以相似性為基點找到最佳關聯,避免出現歧義,也要防止文化元素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