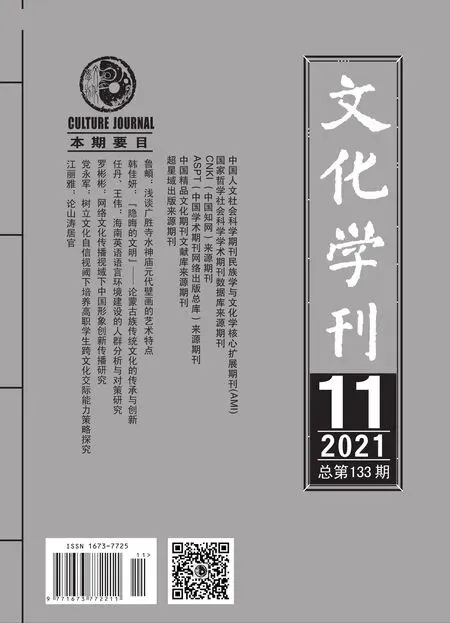王青偉小說《村莊秘史》中女書書寫者的女性主體性解讀
謝亞麗
女書又稱女字,是發源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縣、道縣一帶,僅在女性之間使用的文字,其出現標志著女性意識的提升和女性身份的建立。湖湘文化孕育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專用文字,在使用和傳承的對象上嚴格限制了性別,在中國近三千年的以男性為主導的男權社會中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其社會功能主要用于當地婦女的情感申訴與心靈交流。女書的書寫與傳唱是湖南江永地區真實存在的一種特殊風俗,2010年6月湖南本土作家王青偉寫作的《村莊秘史》在基于其民族身份與地域文化的把握下關注到女書這一特殊的文化遺產并將其以一種形象化的方式呈現出來。
《村莊秘史》以五個故事串聯的形式,通過故事的親歷者章一回講述了發生在紅灣和老灣這兩個相鄰鄉村里的人和事,表現了湖南鄉村隱秘的歷史,并借由對鄉村歷史的敘述表達了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思考。其中的一個故事講述了木匠章順與地主婆的畸戀以及與自己妻子即女書書寫與傳承者麻姑的愛恨糾葛。目前學界對于《村莊秘史》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有22篇相關論文,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歷史反思、鄉土發掘、人性探索、敘事手法以及小說建構方式的角度等方面來分析作品,僅有蔣艷麗的《身份認同焦慮與艱難認同之路》、田文兵的《身份的焦慮:〈村莊秘史〉中的認同危機與歷史敘述》和陳嬌華的《個體身份認同與鄉村歷史敘事》用了極短的篇幅將麻姑作為個案來探討小說人物普遍具有的身份認同的焦慮。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女書書寫對于女性的文化功能和女性主體性在女書書寫者麻姑身上是如何體現的,探討女性企圖依靠女書建構女性主體性這種嘗試的困難與切實意義,以期能給女書和女性主義的相關研究做一點工作。
一、女書書寫者的女性主體性表征
“所謂主體性,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那種特性,它既包括人的主觀需求,也包括人通過實踐活動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和把握[1]”,《村莊秘史》中麻姑的女性主體性表征主要是凡事依靠女性自己、要求女性具備獨立人格從而能夠活出女性自我的生活追求。
首先,對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麻姑有著自己的追求,她遵循自己的內心情感和觀念。所以她能夠聽從自己的情感需要,沖破男性主導的封建文化對于女性的道德規約和倫理教育的樊籠,大膽地和外地遠來且不知根底的章順在油菜地里野合并獨自孕育孩子,還能夠拋開男強女弱的傳統觀念和生活起居主體依靠男人的傳統家庭模式。為了保持自己作為女人的獨立性,她從來不會主動伸手向男人要錢來維持生活與養育孩子,也并不想依靠男人一直在老灣扎根生活,而是想生下女孩后立馬帶著女兒去尋找千家峒。即使在男人常年不在家的情況下,她依然拒絕接受鄉人們的任何幫助,靠著自己的辛勤勞動,獨立完成了自食其力和養育孩子的雙重任務。在她意外懷孕后,她決定不要孩子時既沒有半點女性遇事的慌張猶疑,也沒有求助阿貴,而是自行采取了多種辦法打胎。傳統女性依賴男性的歷史惰性在麻姑身上并沒有一絲遺留,讀者看見的是一個自立自強的麻姑。
其次,對于以丈夫章順和老灣為象征的男性世界她采取了將其物化并作為客體超越的態度。麻姑歷經千辛萬苦找到章順,迫使章順擔負起父親責任,并非其全部目的,除了民族文化中男孩只能跟著父親的規定,她更主要的目的是想借助章順繼續孕育一個女孩兒。從這可以看出,她并未把女性看成是男性的附庸,沒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和從一而終的陳腐觀念。男性在她那里不再是拯救者或給予女性物質供養與情感寄托的存在,而是成為了被她物化的客體,即用來幫助女性生育的種馬。面對丈夫章順哄騙她燒掉女書的甜言蜜語、暴力脅迫以及章順和紅灣地區的人身安全威脅,她倔強地不為所動,仍然無所畏懼地保留著女書文稿。這可以看作是在性別屬性上對于玷污女性世界的男性的拒斥和對自己女性私密空間的竭力保護。麻姑想要生育女兒并和女兒一同去找瑤族傳說中的千家峒,麻姑對千家峒的深厚感情不如是說是對溫情互愛的女性世界的渴望和對老灣象征著的男性世界的堅決逃離。她想帶著女兒逃去沒有男性的方舟中幸福地生活,潛藏著女性獨立意識的初步覺醒,企圖通過想象中的女性世界來抵抗男性世界對于女性的身心迫害。
麻姑不再是五四時期柔石《為奴隸的母親》中地位低下、被丈夫隨意典當而要忍受雙重母子分離痛苦的可憐妻子,也不是沈從文《丈夫》中那將自己的身體出售進而緩解家中經濟困境與幫助男性養家糊口的無奈娼妓。她有著與俗世格格不入但仍堅持自己書寫女書生活方式的主見和物化并超越男性世界的堅韌力量。
二、女書的書寫和女性主體性的建構
女書是由女性所創造的一種文字,而麻姑身為女性的主體性存在于自己每日書寫的女書對男性的放逐之中,存在于以女書為代表的族群文化和性別文化對于女性悲苦人生的理解與調和之中,她試圖通過書寫女書來建構自己作為女性的主體性。
(一)在女書的書寫傳承中述說對于男性的拒斥
女書文化的傳承中,“母女傳承是女書傳承的首要方式,這是女書之鄉的女性們為尋求自我生命之源與文化之根的一種內在表達,女書傳承方式隱藏的是女性世界中男性角色的缺席,準確地說應該是男性“在場的缺席[2]”。女書的傳承對象只能是女性,所以麻姑執著地要生下一個女兒,而且這種文字只有女性才能看懂,當老灣的人們試圖讓村里學問最為淵博的章大弄懂麻姑的女書時,章大予以拒絕并說:“那些文字祖祖輩輩一直秘傳給女人,男人們如果想去弄明白那上面的東西永遠不可能,還沒等到你弄清楚幾個字的時候,你的眼睛就會瞎掉,你的舌頭就會僵硬,你就會變成一個既看不見又說不出話的活死人”[3]93,說明了女書是一種具有性別傾向的文字,它本身就拒斥男性的參與和窺視的妄想。
除了傳承方式和傳承對象以及閱讀范圍具有單一性別的限定之外,即男性的存在在女書文化中不被允許這種顯性的規范之外,女書書寫者還可以通過女書在內在精神世界里完成對男性的放逐,所以《村莊秘史》中丈夫章順即使整天不回家并瘋狂地愛上與自己相差幾十歲的地主婆,在男人基本上對自己既無物質援助又無精神撫慰的情況下,麻姑依然能夠安然過日,甚至同意和支持丈夫章順把情婦接來家中當作母親供養的行為,沒有表現出一般女性對于情感侵占所會有的歇斯底里與憤恨等人之常情。這并非是她對丈夫的屈從,而是長期的女書文化賦予的女性結盟與女性同情,是文化基因和性別屬性所決定的一種“女同性戀存在”。
由此可見,女書的書寫意味著由女性創造出的神秘領域,在這個領域之中女性可以將男性徹底排除在外,營造出只有女性互愛沒有男性迫害的理想烏托邦。《村莊秘史》中瑤族女性麻姑就是通過書寫女書試圖尋找和建構起一個沒有男性干擾而女性們自在幸福生活的“千家峒”。
(二)在女書的書寫過程中實現女性的自我救贖
女書不僅僅是古代女性只為人際交流使用而創造的一種文字,研究者們對女書作品進行分類研究,發現作品內容十分豐富,涵蓋“友情、愛情、訴苦、別離、排斥男性、追求完美家庭生活、用合法手段反抗夫權、聯結歷史重大事件、控訴國家暴力以及謎語、祭祀等。”[4]大部分內容是訴苦情,表述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不幸經歷,并發泄內心的憤慨。由此可見,女書對于女性來說是一種精神的慰藉和情感的依托,女性在書寫女書的過程中將自己的困苦借用文字傾訴出來的同時,既能從中重新獲取繼續生活的能量,又能避開和主流社會及男性的情感不適調和自己的心態。
小說《村莊秘史》中的女書書寫者麻姑就是通過日復一日地書寫女書來傾訴自己的不幸生活并調節心態,完成自己內心的平衡修復。麻姑是一個從遙遠地方來的外鄉女人,并背負著生育女兒尋找千家峒的民族使命,地域遷移導致的起居飲食和文化觀念差異注定使她與老灣有所隔閡,如老灣的老人們經常給她講述紅灣人的罪惡歷史,企圖以此來同化她仇恨紅灣人,但她始終無法理解為什么鄰村會如此地痛恨彼此。對于老灣人對紅灣的政治批判與殘殺,來自互幫互愛的社會的她百思不得其解。無論她生活在老灣多久甚至孕育了老灣人章順的骨血,但她始終帶有融不進老灣的質地。再加上丈夫章順的拋家棄子與對老女人的畸戀,以及丈夫章順對自己的殘害,麻姑內心的苦痛屈辱和憤恨可想而知,所以麻姑才會夜以繼日地寫那些稀奇古怪誰也看不懂的女書發泄自己的情緒[5]。
在現實世界中人們面對困境時常常會寄托于精神世界來使原本痛苦的心情趨于平靜,完成一種心理上的安慰與平衡,麻姑也是如此。在丈夫離家又迷戀其他女人的情況下,她無論從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是愁苦哀怨的,尤其是當阿貴挑逗起她的情欲后,這種內心的煎熬更是成倍增加。于是麻姑在堅守為人妻的忠貞婦道和作為女性的正常情感需求之間、在貞節鎖的有形束縛和作為母親恥于要求孩子開鎖喪失自尊的無形禁忌之間、在情人阿貴欲火焚身的痛苦和自己孩子的生命之間以及在焚燒女書和保護自己之間,無數個艱難的選擇橫梗在她面前。而她只要心理一開始失衡,便“從那口木箱里取出一摞字稿,發了瘋似的寫著”[3]116。“麻姑的婚姻生活極其凄苦,女書便成了她抒發自身苦情的集中代表和象征,她不停地書寫女書,尋找那個世外桃源般的千家峒,借對家鄉的美好回憶,她現實處境的艱辛和感情的凄苦似乎也得到了一種釋放和轉移。”[6]
我們可以看出,在這里女書的意義與價值不僅是一種女性的書寫工具和表達手段,它由純粹的物質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對于無數個像麻姑這樣婚姻不幸生活困苦的女人而言,女書的書寫過程給予了他們一種性別文化的理解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得女性能夠在男性帶來的痛苦之中脫離出來達到自己的涅槃重生。
小說中的麻姑就是通過書寫女書得到來自女書構建的觀念性女性世界的支持,從女書的書寫過程中獲取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在女性性別文化的支持、疏導和調解之下實現了女性的自我救贖。
三、女書的被焚與女性主體性建構的失敗
“女性作為個體在社會文化層面的身份認同有兩種情形:一是作為主體自我,通過尋找性別群體的傳統來確認自我身份;二是通過認同已有男性中心社會給予女性的角色規范來確認自我身份。”[7]麻姑顯然是屬于前者,她始終日復一日地書寫女書,就是擔心失去自我身份認同而喪失尊嚴,她努力通過尋找女性群體的傳統來確認自我身份。
對于麻姑而言女書的書寫就是一種自我身份確認的過程,也是她建構女性主體性的一種方式,她可以通過書寫女書活在女書文化構建起來的虛擬女性群體世界和強大的內心世界里,從而抵御以丈夫章順為代表的男性世界對女性的輕視與損害,忽略以老灣為代表的男性主導的傳統社會對于女性的或有形或無形的壓迫。
老灣人始終認為麻姑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女人,“他們一直弄不明白這個女人是從什么地方來的,麻姑說的那個地名他們都不曉得”[3]91所以,當麻姑兒子為了母親免遭殺生之禍,而私自焚燒她的女書時,麻姑“瘋了似的上去扒拉那堆灰燼,她以為能夠從那里找出一片沒有燒干凈的字稿”[3]122燒掉女書文稿意味著徹底地清空了她的歷史,于是“事情在麻姑那里形成了一片巨大空白,她眼中晃動的那些人影幾乎全變成了永遠也回不到現實的夢境,她什么人也認不出了”[3]123,意味著失去了民族和家園記憶以及女性集體記憶,同時也是對于自身女性主體性的毀滅。如果說以前所謂的“空白歷史”是老灣人對于他人歷史的惡意抹殺和其歷史的不正確認知,但她心里一直很清楚自己的歷史并且憑借自己每日書寫的女書為證并加以強化,而至此她的歷史真的被男性燒成了一堆紙灰,陷入了沒有歷史身份和自我性別認同的迷茫與空白中。女書的被焚毀從側面宣告了女書書寫者試圖建構女性主體性的失敗,但細究女書畢竟是一種不為男性所知道的文字,實際上并未與男性世界正面地進行過較量。這種在無聲狀態下冠名的女性意識的增強和女性主體的強調近似于20世紀90年代陳染等人建構的女性私人空間,待在一個人的黑暗房間里獨自囈語或做著幻夢。
四、結語
自20世紀80年代各種女性主義理論傳入中國之后,女書的性別對峙價值再次被挖掘和衍生,成為了當代的女性宣言。不少的學者和社會人士要求對女書文化進行保護和傳承,認為對于女性主體性的建構具有文化和心理層面的支撐作用。從女書的性別意蘊或者說女性主義賦予的各種延伸意義來看,女書這種獨特文化的確有一種挑戰男性權威的現代性,可以說是女性獨立意識覺醒的標志。可是從女書的存在空間、傳承方式和受眾等來看,女書更多的是女性一個人的戰爭或最多是女性們背著男性合謀然而又缺乏實踐性的臆想交流。而且從廣泛的社會處境來看,在現實中女書文化經常會遭到詆毀,正如《村莊秘史》中的女書書寫者麻姑不被外界所接納,甚至在不干擾他人的情況下其書寫的女書也遭致焚毀,這寄寓著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是一種文化必然,但是在實踐中能不能真正地通過女書文化建構女性主體性卻是個值得思辨的問題。王青偉的《村莊秘史》無疑給我們提供了關于女書更多面更形象的思考,為女性意識和女性主體性開放意義上的建構提供了更為切實的參考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