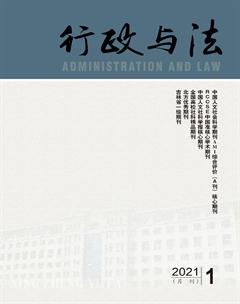項目進村中技術理性的折耗

摘? ? ? 要:以技術理性為精神內(nèi)核的項目制能夠助推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和公共權力理性化,但仍存在邏輯困境和運行瑕疵,這在項目進村入戶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2017至2019年村干部貪污侵占犯罪案件的分析表明,項目專項資金已成為村干部貪占的重災區(qū)。從表層的技術邏輯看,村干部憑借相應的手段破解了項目制技術程式;從深層的制度邏輯看,項目進村在為村干部提供了項目管理這一結構性機會的同時,所依存的制度成本保障不足,而制度成本問題可能會給項目制及其技術理性帶來內(nèi)卷化和形式化的風險。因此,在項目進村入戶時,應加強基層政府和普通村民對村級組織的監(jiān)督制衡。
關? 鍵? 詞:項目制;項目進村;技術理性;制度成本
中圖分類號:D630?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207(2021)01-0050-12
收稿日期:2020-11-09
作者簡介:溫丙存,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社會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法律社會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信訪在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中的角色定位與銜接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BSH091;重慶市技術預見與制度創(chuàng)新項目“健全我市‘三治(自治、法治、德治)結合的鄉(xiāng)村治理體系”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cstc2018jsyj-zdcxX0086;重慶市社科規(guī)劃委托項目“貧困地區(qū)基層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9WT07。
一、研究緣起
分稅制易誘發(fā)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xiāng)政府財權難以滿足事權要求的財政困難,[1]為應對基層政府的財政窘境,財政轉(zhuǎn)移支付這一配套制度及其項目化運作模式開始不斷被強化,項目專項治理模式發(fā)展成為國家治理中的一種制度思維,[2]從一定程度上說,“除了工資和日常支出外,幾乎所有的建設和公共服務資金都‘專項化和‘項目化了”。[3]在項目制形成的諸多結構要件中,績效合法性的思維模式最為根本,其集中表現(xiàn)為在以引導規(guī)制市場、構建以公共服務為本的新型治理體系的同時,引入法治化、規(guī)范化、技術化和標準化等理念,以保證最終能夠持續(xù)產(chǎn)生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治理績效,于是就引發(fā)出對技術理性和技術治理的內(nèi)在要求,而項目制正好與這種對績效合法性及其技術理性的內(nèi)在要求相契合,“專項資金的‘抽取和‘下放,只有通過一整套嚴密設計的技術系統(tǒng),通過立項、申報、審核、監(jiān)管、考核、驗收、評估和獎罰等一系列理性程序,才能最終使項目生效,獲得全社會的認可和信任。”[4]這就是項目制的生成邏輯。
學界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在制度安排和運作愿景上,技術理性和技術治理是項目制制度精神的精華所在。如周雪光基于“控制權”的理論視角分析項目制的博弈過程后認為:“如果僅僅從委托方的意愿和項目設計來看,項目制實施應該是一個按照上級意志推行落實的理性化過程。”[5]桂華在考察農(nóng)地整治項目實施過程后發(fā)現(xiàn),項目制能夠?qū)⒐芾磉^程指標化、技術化、量化,以此來解決委托代理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也因此項目制的技術理性能夠較好地解決項目質(zhì)量等監(jiān)督問題,比如農(nóng)地整治項目能夠基本保障農(nóng)地整治資金投入的專款專用。[6]應小麗、錢凌燕在考察項目進村中技術理性的實際運作時認為:“事本性目標導向、權威主導、程式化的線性技術以及效率至上的經(jīng)營性技術共同構成了‘項目進村的技術治理邏輯。”[7]在郭琳琳、段鋼看來,項目制帶有濃厚的技術治理的制度精神,“項目制在運轉(zhuǎn)中要求精細化管理項目資金、規(guī)范化項目運作流程、嚴格項目運轉(zhuǎn)程序,并對項目過程進行無縫隙監(jiān)管”。[8]所以說,技術理性是項目制治理的精神內(nèi)核,即項目制是伴隨技術理性而產(chǎn)生的,技術理性是項目制得以生成、存續(xù)和伸延的最堅實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歷史性、開創(chuàng)性成就,產(chǎn)生了全方位、深層次影響,但同時也必須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特別是要持續(xù)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持續(xù)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嚴懲扶貧民生領域腐敗”。[9]對于村干部貪腐問題,學界主要基于權力運行視域進行討論,有研究認為權力資源是農(nóng)村小微腐敗發(fā)生的重要載體,[10]具體表現(xiàn)如村民自治權運行不暢、[11]有效監(jiān)督機制欠缺、[12]基層民主相對滯后[13]等。由此可見,項目進村雖已成為村干部貪腐所嵌入的新的結構背景,但學界尚未從項目制的制度視角探究村干部貪腐問題。項目制及其技術理性無疑可以助推國家政權的理性化建設,[14]但其并非完美無缺,在實踐運作中也會“打折扣”,出現(xiàn)權力尋租與合謀、[15]供給斷層與治理失效、[16]邏輯悖論與運行張力[17]等具體困境和問題。項目制及其技術理性在制度設計與運作實踐之間所出現(xiàn)的某種背離和錯位,正是本文所要例證的核心問題:在以技術理性為導向的項目進村中,項目專項資金何以被村干部貪占。換言之,在現(xiàn)階段項目進村的結構背景下,村干部能否繞開項目技術理性而貪占公共財物仍是一個需待打開的“黑箱”。本文從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上的犯罪案件入手,分析項目進村中的村干部職務侵占現(xiàn)象,進而討論項目制及其技術理性問題。
二、項目專項資金已成村干部貪占重災區(qū)
(一)數(shù)據(jù)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841起村干部貪占犯罪案件
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刑法的相關規(guī)定,村干部的刑法身份具有二重性,只有當村干部在協(xié)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時才構成“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也才具備貪污罪等職務犯罪上的刑法身份。貪污罪是侵占財產(chǎn)犯罪的一種具體形式,[18]為此,在考察項目進村中的村干部職務侵占現(xiàn)象時,本文選擇從村干部貪污犯罪案件入手。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lián)網(wǎng)公布裁判文書的規(guī)定》(法釋[2016]19號)之規(guī)定,法院應依法、全面、及時、規(guī)范地將裁判文書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公布,但涉及國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調(diào)解結案、離婚訴訟等情形的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犯罪案件即來源于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研究數(shù)據(jù)的具體檢索與整理流程如下:
第一步是搜索:確定四個檢索詞及其組合,包括“貪污(案由)+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搜索詞)+2019、2018、2017(裁判年份)+一審、二審(審判程序)”①。本研究最后(補充)檢索時間是2020年6月30日,檢索后網(wǎng)站系統(tǒng)自動生成1121份裁判文書。第二步是剔除:逐篇審讀以剔除無效刑事裁判文書。根據(jù)研究目的,對系統(tǒng)自動生成的1121份裁判文書逐篇審讀后發(fā)現(xiàn)一二審同案關聯(lián)、罪名不適、主體不適、二審發(fā)回重審、裁判無罪等不符合研究條件的文書144份。第三步是“提純”:提取嚴格意義上的單獨犯罪案件和共同犯罪案件。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某些客觀事實上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數(shù)名被告人存在被分開審判的可能,而同時審判的幾名被告人也存在非共同犯罪的可能(即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共同犯罪,僅是并案審理而已)。據(jù)此剔除121份同案被告人被另案處理的文書和15份非真正共同犯罪的同案審理文書。至此,本研究最終有效數(shù)據(jù)為全國各地法院2017年、2018年、2019年所裁判生效的841起村干部貪污侵占犯罪案件,其中,單獨犯罪案件544起(占64.69%),共同犯罪案件297起(占35.31%)。
(二)項目專項資金成為村干部貪占的主要選項
本研究分析發(fā)現(xiàn),項目專項資金已成為現(xiàn)階段村干部貪污侵占的重災區(qū)。“資源和規(guī)則下鄉(xiāng)之后改變了村莊權力的運作邏輯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規(guī)則,構建起了村莊內(nèi)部的‘權力——利益網(wǎng)絡。村干部穩(wěn)定的周期性選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項目運作的封閉化是村莊內(nèi)部‘權力——利益網(wǎng)絡的外在特征。”[19]項目進村為當下村干部貪占項目資金創(chuàng)造了“新契機”,提供了“新選項”,本研究中項目專項資金案件(832起),占村干部貪污侵占犯罪案件總量(841起)的98.93%②。
對841起村干部貪占犯罪案件中的具體對象和發(fā)案領域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③,被村干部侵占最多的是民生基本保障項目資金,共424起,占50.41%。根據(jù)項目保障目標及其技術要求不同,其又可細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危房改造項目專項資金案件(共179起,占42.22%)。第二類是扶貧項目,僅指產(chǎn)業(yè)發(fā)展項目、易地搬遷項目、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等專項資金案件(共88起,占20.75%)。第三類是民生救濟類專項款物案件(共75起,占17.69%),其中被侵占最多的是低保資金(共50起),另外還包括五保補助款(9起)、養(yǎng)老保險金等社保費用(6起)、孤兒基本生活補貼款(5起)、涉軍優(yōu)撫金(3起)、計生特別獎資金(2起)等。第四類是水災、地災、震災、農(nóng)災等搶險救災專項資金案件(共49起,占11.56%),其中,騙取國家政策性農(nóng)業(yè)保險理賠款案件19起。第五類是水利移民領域?qū)m椯Y金案件(共33起,占7.78%)。
排第二位的是征地補償費等土地管理項目資金,共208起,占總量的24.73%。排第三位的是農(nóng)林業(yè)支持保護補貼專項資金,共134起,占總量的15.93%。其中,侵占農(nóng)業(yè)支持保護補貼(含種糧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nóng)資綜合補貼、耕地地力保護補貼、養(yǎng)殖補貼等)專項資金案件有84起;侵占林業(yè)支持保護補貼(含退耕還林項目補貼、生態(tài)公益林項目補貼等)專項資金案件有50起。排第四位的是改善民生類(不含扶貧濟困類)基建項目資金案件,共54起,占6.42%,包括美好鄉(xiāng)村建設項目專項資金、農(nóng)水工程項目專項資金、沼氣池建設專項補助資金等。另外,被村干部貪占的其他類項目資金案件共有12起,其中,農(nóng)村義務教育化債資金等公益性鄉(xiāng)村化債專項資金案件有7起。
三、村干部貪占專項資金的“技術”邏輯
(一)村干部貪占的核心“技術”:虛報瞞上
在本研究832起村干部貪占項目專項資金案件中,村干部貪占手段可分為“虛報瞞上”“克扣欺下”和“其他手段”三種類型。其中,虛報瞞上是指村干部在項目管理中通過無中生有、以少充多、以舊充新、重復申報等虛增虛報方式直接欺騙各級政府以套占國家項目資金。克扣欺下是指村干部在項目管理中通過全部克扣或部分截留等方式直接侵占本應屬于村集體或村民家戶應該獲得和享有的項目資金。也可以說,虛報瞞上主要是通過虛增和瞞上手段侵占項目資金,就其直接后果而言,除了國家外并無其他直接具體的受害人;而克扣欺下則主要通過既有欺騙又有欺負的手段侵占村集體或村民家戶明確可得的項目資金,可將其看作是村干部和村民間的零和博弈,村集體或村民是直接受害人,國家是間接受害人。其他手段則指除了虛報瞞上和克扣欺下之外的手段(共有62起,占總量的7.45%),需要說明的是,該類案件統(tǒng)計時還包括通過案件裁判文書難以查知具體作案手段的村干部貪占專項資金案件。
本研究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村干部通過虛報瞞上手段貪占專項資金的案件有665起,占總量的79.93%。具體來看,有的村干部以自己、親朋或者其他村民的名義向基層政府虛報套取;有的村干部采取虛增項目工程量的方式套取,這在改善民生類基建項目領域尤為突出;有的村干部采取虛增農(nóng)地面積的方式套取;還有少數(shù)村干部采取以舊充新方式套取項目資金。村干部虛報瞞上的“最大利好”在于“上面的”基層政府不確知上報項目的真實性,如符合條件的村戶名冊、項目實際工程量、農(nóng)林地實施面積、項目修建時間等,也就是說,基層政府對村莊內(nèi)情(即項目進村入戶所需的各類資料信息)難以精準把控,只能借助或者單憑村干部的“一家之言”。因為村干部掌握村莊熟人社會中的所有信息資料,即村干部在協(xié)助基層政府開展項目管理時擁有壟斷村莊信息資料的權力,這樣,就存在村干部虛報相關信息資料的可能。如在(2017)魯1721刑初457號案件中①,邵莊鎮(zhèn)民政辦主任趙某明的如下證人證言足可以說明項目進村入戶時,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如何與村干部互動以及遭蒙騙:
2014年3月省政府規(guī)定,每戶低保戶都要補辦村民低保審批表,統(tǒng)一由鎮(zhèn)、縣民政部門管理。按照規(guī)定民政辦應對全部上報人員逐戶進行核查,由于鎮(zhèn)民政辦只有其一個人,其只是對各村上報的申報情況進行抽查,沒有逐戶進行核查。張屋村約有40戶低保戶,其沒有全部入戶審核,只抽查了幾戶。當年,上級民政部門要求統(tǒng)一對低保戶重新建檔,張屋村黨支部書記王某剛把張屋村所有低保戶申報材料一塊報到鎮(zhèn)里。其在審查時,看上面評議人員都簽了名,就在鄉(xiāng)鎮(zhèn)經(jīng)辦人處簽上了自己名字。其記不清鄭某、趙某榮、曹某是從什么時間開始享受低保待遇的。張屋村村干部沒有向其說過他們弄虛作假、冒領低保款的事情,直到檢察機關查處張屋村干部冒領低保款問題后其才知道。
(二)村干部貪占的輔助“技術”:克扣欺下
本研究中村干部通過克扣欺下手段侵占專項資金案件有105起,占總量的12.62%。具體來看,有的是克扣截留村民個人應得的項目資金,如在(2018)陜0924刑初1號案件中,犯罪人鄧某禮作為村委會委員、村文書,利用職務之便,截留國家發(fā)放給農(nóng)村特困人員蘇某的五保供養(yǎng)金18140元據(jù)為己有。有的是克扣截留村集體應得的項目資金,如在(2017)陜0724刑初60號案件中,犯罪人邱某春(時任西鄉(xiāng)縣兩河口鎮(zhèn)紅花村黨支部書記)在協(xié)助兩河口鎮(zhèn)政府管理退耕還林補助資金上報、兌付過程中,利用職務便利,將村集體的退耕還林補助資金35175元據(jù)為己有。
公開透明決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敗,然而村干部克扣欺下的“最大利好”在于“下面的”村民難以及時、完全、準確地掌握項目進村入戶的相關信息,即普通村民不清楚是否有項目、不知道自己是否該得或該得多少專項資金,這就給村干部克扣截留村民應得的項目資金提供了機會。如在(2018)冀0623刑初35號案件中,犯罪人王某興(時任淶水縣婁村鄉(xiāng)虎過莊村村委會主任)在協(xié)助政府進行危房改造補助金發(fā)放時,截留三戶村民的16000元危房改造補助款據(jù)為己有。本案中據(jù)張某一的如下證人證言可知,在專項資金發(fā)放中,村干部憑借掌握項目資金享受者銀行賬戶信息等便利,通過虛假簽名、多取少予等方式,克扣截留普通村民應享的專項資金。
其家曾進行危房改造,是一般貧困戶,屬D級危房,改造過程中其向村干部提交了戶口本、身份證復印件。其沒有領取過戶名為張某一、賬號為62×××18、金額為20000元的危房改造補貼款銀行卡,卡上的錢不是其自己支取的,其也沒得過20000元的危房補貼款。是穆某給的其現(xiàn)金,穆某說王某興給的。虎過莊危房改造銀行卡發(fā)放表上的“張某一”三個字不是其本人簽的,手印也不是其按的。
綜上,虛報瞞上和克扣欺下已成為當下村干部侵占項目專項資金的兩種慣用手段,特別是虛報瞞上已成為村干部侵占的核心“技術”,該類案件占近80%。究其原因在于,相比于克扣欺下,為減少貪污犯罪風險,村干部理性選擇通過弄虛作假來化公為私,并非“簡單粗暴”地與民爭利,而是繞過與村民的“零和博弈”,瞄準“公家的”那部分,作案手段愈加隱蔽。
(三)典型案例剖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虛報瞞上和克扣欺下的貪污侵占犯罪案件中,村干部有時并非“獨惡其身”,換言之,也存在村干部與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包括普通村民之間的合謀貪污問題。在本研究832起村干部貪污侵占項目資金犯罪案件中,共同犯罪案件有311起(占37.37%),涉及犯罪人973名。除了1名村干部作為村干部貪污侵占案件的“底數(shù)”外,在剩余的其他同案犯中,身為村干部的(即另外有其他村干部也參與到貪污侵占犯罪活動中)共有494名;身為普通村民的共有87名;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共有43名。這說明,在少數(shù)案件中,基層政府或普通村民對村干部貪污侵占行為也絕非完全被動或不知情,而是“裝糊涂”或者與村干部“合謀”。相較于通常的村干部“單方”貪污侵占問題而言,這種縱向身份間的合謀貪污破壞力更大,以(2018)皖1226刑初147號案件為例展開剖析。
該案中,犯罪人陳某雪在擔任潁上縣西三十鋪鎮(zhèn)四十鋪村黨支部書記期間,利用協(xié)助鎮(zhèn)政府從事本村危房改造工作的職務便利,明知其同母異父哥哥孫某家已于2011年享受國家危房改造補助資金后,不應再次享受該補助且未蓋新房不符合危房改造上報條件的情況下,連續(xù)在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別以其哥哥孫某、嫂子張某名義重復上報為危房改造戶,共騙取危改資金60000元。根據(jù)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潁上縣住建局關于農(nóng)村危房改造申報的說明①、證人萬某(擔任西三十鋪鎮(zhèn)民政所長,負責審核危房改造資料和初步驗收工作)證言②等足以說明項目初始設計上的技術理性。既然危房改造項目的技術理性設計中已對申報、評議、驗收、放款等線性流程加以技術規(guī)制,那么,該案犯罪人又是如何做到重復申報以套占國家危房改造資金的呢?從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中可以梳理出項目技術程式層層“失守”的答案。
首先,村莊民主評議推薦環(huán)節(jié)“失守”。從本案證人孫某二證言(哪戶最困難最終還是由村書記決定。在2012年至2014年危房改造戶上報中,其村沒有開會評議,上報哪些戶進行危房改造,最終是由村書記陳某雪拍板決定)、朱某證言(上報哪些戶進行危房改造,最終還是由村書記拍板決定,所以陳某雪提出將孫某當作危房改造戶上報,其作為村干部沒有反對)及犯罪人陳某雪供述(因為其是村里的一把手,其提出來了這個事,其他村干部雖然知道孫某、張某不符合危房改造的條件,但也都勉強同意了)可知,村莊一把手的“專權”“一言堂”導致村莊民主評議難以落地,有名無實。
其次,基層政府審核審批環(huán)節(jié)“失守”。該案中,鑒于與村干部已建立工作和私人層面的“較好關系”,負責審核驗收的基層政府工作人員萬某選擇了“放過一馬”③。當然,徇私合謀的基層政府工作人員也得到了村干部的回報和“好處”。證人萬某證言證明:“2013年過年時,陳某雪為了感謝,給其送了4只雞、兩條魚、10斤牛肉、一箱柔和種子酒”;“2014年過年時,陳某雪又給其送了幾只雞、幾條魚和一箱酒”。
再次,基層政府評估驗收環(huán)節(jié)“失守”。從證人萬某證言(驗收時一般住建局都不參加,都是鎮(zhèn)里去驗收,鎮(zhèn)里由其具體負責組織驗收,后來鎮(zhèn)里分管領導帶著其去村里驗收時,在生產(chǎn)隊干部孫某四的帶領下,孫某四隨便指一處新房說是孫某的新建房,其就在新建房前拍照,走走過場算驗收合格了,實際上孫某、張某家沒有建房)可知,因被委托從事實際驗收人員與當初審核審批人員為同一主體,所以評估驗收就是走過場,鄉(xiāng)鎮(zhèn)政府和村委會形成一種“共謀現(xiàn)象”。[20]
最后,基層政府打款發(fā)放資金環(huán)節(jié)“失守”。證人李某的證言證明:項目資金并未直接打到農(nóng)戶賬戶上,而是打到了村干部個人賬戶上。“2012年四十鋪村的張某、孫某的補助款,其是按照萬某安排的,打給陳某雪卡上了”;“2013年其是按照萬某的安排制作花名冊,進行打卡發(fā)放。表中張某的補助資金打給陳某雪的”;“2014年的危房改造資金是2015年2月打卡發(fā)放的,將孫某的補助資金打給陳某雪是萬某安排的”。
綜上,在農(nóng)村危改項目“進村入戶”過程中,村干部憑借其在村莊內(nèi)部獲得的不受制約監(jiān)督的話語權和分配權,以及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相關工作人員建立的“私人情義倫理”[21]和利益交換關系,在利益驅(qū)使下,突破了村莊民主評議推薦、基層政府審核審批、評估驗收和打款發(fā)放資金等環(huán)節(jié),最終使項目技術理性在落地實踐中折耗。
四、村干部貪占專項資金的制度邏輯
(一)村干部的“政府委托人”身份為其貪占提供了結構性機會
在“鄉(xiāng)政村治”格局中,鄉(xiāng)鎮(zhèn)政權與村莊之間的關系存在著結構和運行邏輯的錯位,即宏觀的行政體制遵循自上而下的科層思維和行政邏輯,而微觀的村民自治則尊崇民主和自治精神,當二者遇到“不接軌”問題時,鄉(xiāng)村關系就會形成以居于強勢地位的行政運行模式和居于弱勢地位的村民自治的民主化村級治理同時存在的常態(tài)特征。[22]村級組織是聯(lián)系基層政府與村莊的紐帶,村干部同時承擔著雙重身份:一個是基于村莊內(nèi)部自治事務管理而生成的“村莊代理人”身份,另一個是基于行政委托事務管理而生成的“政府委托人”身份。項目進村無疑會加劇鄉(xiāng)村關系中既有力量對比的不平衡,造成“政府委托人”的話語權更加強勢,村莊民主自治力量則相對弱化的后果。項目進村對鄉(xiāng)村關系的形塑將直接影響村級組織和村干部身份作用的發(fā)揮,在項目資金自上而下、由外而內(nèi)進村入戶過程中,村級組織和村干部須“在場”,而其出于“自主性和自利性沖動”,[23]會理性選擇向更加強勢的力量靠攏,導致“村級治理行政化的趨勢愈加顯著”。[24]
在基層政權運作中,有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對村級組織尤其是“村兩委”進行控制,以分解和完成各項指標任務。研究發(fā)現(xiàn),在項目進村過程中,村干部的“村莊代理人”身份是圍繞“政府委托人”身份而運轉(zhuǎn)的,村干部所組織實施的村內(nèi)民主評議等自治行為只是實現(xiàn)項目行政管理的一個技術環(huán)節(jié)、手段或者“走過場”,所以,村干部的“政府委托人”身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原生的、主導的、顯性的,而其“村莊代理人”身份則是居于被支配地位的,是派生的、輔助的、隱性的。村干部既然或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了承擔更多的“政府委托人”身份,協(xié)助縣鄉(xiāng)政府從事項目管理類的行政管理工作,那么,其也由此成為了刑法規(guī)制上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具備了貪污罪等職務犯罪上的刑法身份。
在項目進村的結構性背景下,項目管理已成為村級組織人員協(xié)助基層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主流,與此同步,項目資金成為了村干部最經(jīng)常接觸或者是唯一能接觸到的國家公共財物,因此項目專項資金成為村干部貪污侵占的重災區(qū)也就不難理解了。如隨著國家逐步調(diào)整農(nóng)村政策特別是農(nóng)村稅費改革對農(nóng)民減負增收,[25]以及項目制背景下基層政府維持運轉(zhuǎn)已從過去依靠收取稅費轉(zhuǎn)向依靠上級轉(zhuǎn)移支付,[26]使得原來村干部協(xié)助政府所從事的“代征、代繳稅款”工作已被“發(fā)放農(nóng)林業(yè)支持保護補貼”工作所替代,因此農(nóng)林業(yè)支持保護補貼逐漸成為當下村干部貪污侵占的對象,而原來常見的農(nóng)業(yè)稅費則在當前村干部貪占對象中難尋蹤跡。
(二)項目進村所需的高昂制度成本消解了項目技術理性
“制度成本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是指投入在制度各個環(huán)節(jié)中的相關資源。在一個完整的制度周期中,每一個階段都需要支付相應的成本,由此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形成成本、制度執(zhí)行成本、制度監(jiān)督成本、制度變遷成本。”[27]制度成本問題在項目制中更為凸顯,從表面上看,財政資金專項轉(zhuǎn)移支付是上級政府對基層政府和目標受益群體所量身打造的單方行為,但在項目實際運作中,基層政府和目標受益群體并非是零成本和純獲益,其還需支付高昂的制度成本——項目制的制度成本在運作實踐中幾乎都轉(zhuǎn)嫁到基層。在前面研究項目制及其技術理性之精神時已發(fā)現(xiàn),項目資金不會自動配對和精準輸送至目標群體,項目制及其技術理性價值的實現(xiàn)是有條件的,這種條件和對價就是由招投標、配套資金、信息溝通、監(jiān)督評估、協(xié)商評議、審計驗收、利益博弈等所帶來的制度成本。項目制在基層運作特別是進村入戶階段,其對制度成本的需求和依賴則更加強烈,而這種配套的制度成本一旦缺失,項目制及其技術理性在進村入戶時則會相應地減損和消耗。
回到本研究中來,村干部之所以能夠利用虛報瞞上和克扣欺下這兩種方式侵占專項資金,與項目進村入戶階段所需的大量制度成本投入保障不足直接相關。因為,一方面,“上面的”基層政府特別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限于人員、經(jīng)費、精力等,怠于完整履行資金配套、項目監(jiān)督、入戶調(diào)查、實地驗收、規(guī)范評估等各項義務;另一方面,“下面的”村民或受制于能力或受制于機制平臺,難以充分行使知情同意、協(xié)商評議、民主監(jiān)督等權利。信息“擁堵”會誘發(fā)交易成本和基層“微腐敗”問題,[28]在項目進村入戶階段,本應不可缺位的制度執(zhí)行成本、制度監(jiān)督成本等的投入保障不力,使得基層政府與項目資金享受者之間難以達致“溝通理性”,這就為村干部貪占專項資金提供了機會。處于中間環(huán)節(jié)和紐帶作用的村干部可以把項目運作的本原信息屏蔽或替換,導致項目出現(xiàn)“進村易,入戶難”的局面,最后使項目原有的規(guī)范性、精準性等技術理性產(chǎn)生折耗。
當然,村干部貪占專項資金問題僅是項目制技術理性失去應有的制度成本保障而折耗并誘發(fā)的諸多意外后果之一,學界在分析項目制運作實踐時還發(fā)現(xiàn)了項目制技術理性折耗后的其他意外后果。如折曉葉、陳嬰嬰認為,項目并不必然給村莊和農(nóng)民帶來利益,項目制對標準化、技術化和統(tǒng)一化的過度崇拜將招致對地方和基層特殊條件、實踐能力的忽略甚至無視,以及對項目承受者實際需求、條件差異和自主參與的忽視。[29]黃宗智、龔為鋼、高原分析發(fā)現(xiàn),項目制在實踐中遵循的是逐利價值觀下的權——錢結合的運作邏輯。[30]李祖佩在對涉農(nóng)項目實踐過程進行考察后發(fā)現(xiàn),“基層精英群體凝結成日益固化的利益分配結構主導整個項目實施過程”。[31]在焦長權看來,項目制實踐中仍然存在“資金沉淀”問題,尚未有效解決財政資金大規(guī)模閑置浪費問題。[32]吳映雪在考察縣域扶貧項目時發(fā)現(xiàn),項目制下扶貧資源存在制度性耗散與非制度性耗散兩種現(xiàn)象:“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扶貧項目流程繁雜造成的時間耗費、扶貧項目跑動與論證過程的資金消耗、扶貧項目實施的機構增設與監(jiān)督成本耗費;非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項目虛報與重數(shù)量輕質(zhì)量、項目施工中的工程外包與阻工鬧工、項目驗收中的資金挪用和監(jiān)管缺失等。”[33]
[16]余成龍,冷向明.“項目制”悖論抑或治理問題——農(nóng)村公共服務項目制供給與可持續(xù)發(fā)展[J].公共管理學報,2019,(2):147-158.
[17]張振洋.當代中國項目制的核心機制和邏輯困境——兼論整體性公共政策困境的消解[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32-41.
[18]王彥強.業(yè)務侵占:貪污罪的解釋方向[J].法學研究,2018,(5):136-152.
[19]鄧泉洋,費梅蘋.項目下鄉(xiāng)后村莊秩序的再審視[J].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5):100-108.
[20]周雪光.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xiàn)象”——一個政府行為的制度邏輯[J].社會學研究,2008,(6):1-21.
[21]狄金華.“權力——利益”與行動倫理:基層政府政策動員的多重邏輯——基于農(nóng)地確權政策執(zhí)行的案例分析[J].社會學研究,2019,(4):122-145.
[22]吳毅.雙重邊緣化:村干部角色與行為的類型學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78-85.
[23]金江峰.項目制背景下的鄉(xiāng)村關系——制度主義的視角[J].天府新論,2016,(4):104-112.
[24]朱政,徐銅柱.村級治理的“行政化”與村級治理體系的重建[J].社會主義研究,2018,(1):121-130.
[25]周黎安,陳燁.中國農(nóng)村稅費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雙重差分模型的估計[J].經(jīng)濟研究,2005,(8):44-53.
[26]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nóng)民關系之影響[J].社會學研究,2006,(3):1-38.
[27]張廣利,陳豐.制度成本的研究緣起、內(nèi)涵及其影響因素[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2):110-116.
[28]廖金萍,廖曉明.基層扶貧“微腐敗”:生成邏輯與治理路徑——基于交易成本政治學分析框架[J].求實,2020,(2):37-45.
[29]折曉葉,陳嬰嬰.項目制的分級運作機制和治理邏輯——對“項目進村”案例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1,(4):126-148.
[30]黃宗智,龔為綱,高原.“項目制”的運作機制和效果是“合理化”的嗎?[J].開放時代,2014,(5):143-159.
[31]李祖佩.項目制基層實踐困境及其解釋——國家自主性的視角[J].政治學研究,2015,(5):111-122.
[32]焦長權.公共支出效率與現(xiàn)代預算國家——“項目制”實踐過程中的“資金沉淀”問題研究[J].學海,2018,(6):83-90.
[33]吳映雪.縣域扶貧項目制的“耗散”過程及其邏輯[J].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31-42.
[34]溫丙存.特派式、專門性、全程化的項目監(jiān)督——項目制基層監(jiān)督的地方創(chuàng)新及其實踐邏輯[J].中國行政管理,2017,(6):18-23.
[35]孔衛(wèi)拿.鄉(xiāng)村建設過程中的項目內(nèi)卷化負債——基于安徽G縣的調(diào)研與思考[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4,(4):49-64.
[36]焦長權.從分稅制到項目制:制度演進和組織機制[J].社會,2019,(6):121-148.
[37]豆書龍,葉敬忠.項目制研究何以成為“顯學”:概念辨析、性質(zhì)定位與實踐探索[J].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4):24-35.
[38]周飛舟.政府行為與中國社會發(fā)展——社會學的研究發(fā)現(xiàn)及范式演變[J].中國社會科學,2019,(3):21-38.
[39]許漢澤,李小云.精準扶貧視角下扶貧項目的運作困境及其解釋——以華北W縣的競爭性項目為例[J].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49-56.
[40]杜春林,張新文.農(nóng)村公共服務項目為何呈現(xiàn)出“碎片化”現(xiàn)象——基于棉縣農(nóng)田水利項目的考察[J].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31-40.
[41]《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編寫組編著.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0:45.
(責任編輯:高?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