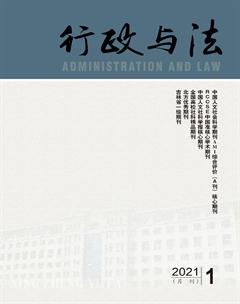我國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之構建
王素芬 任妍暉
摘? ? ? 要:以犯罪人為中心的刑事政策使被害人權利遭到嚴重忽視,尤其在經濟上難以獲得充分賠償,易于導致被害人的“二次傷害”。建立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將刑事被害人的權利保護納入社會保障法體系范疇已被世界多國選擇。我國應引入社會補償制度,重新審視國家與社會、救助與補償之間內涵與區別,明晰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性質,構建補償對象清晰、補償條件明確、資金來源充裕、管理機構權威的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以實現我國刑事被害人權利的充分保障。
關? 鍵? 詞: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社會補償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5.2?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207(2021)01-0113-09
收稿日期:2020-12-07
作者簡介:王素芬,遼寧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任妍暉,遼寧大學經濟法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遼寧省教育廳項目“醫療保險可持續運行的法制保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LJC201921。
一、問題的提出
2020年6月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數據顯示,依據起訴案件數量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8年常住人口數相比較,全國平均每萬人的刑事犯罪發案量為13人。[1]我國共有14億人口,數量多、基數大,因此,每年新增的刑事被害人人數不容小覷,如何保障這一群體的權利已成為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實際上,這一問題早已引起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高度重視并紛紛建立了專門的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新西蘭于1963年頒布《刑事損害補償法》,開現代意義補償制度之先河,其后十余個國家在20世紀70-80年代陸續頒布刑事被害人補償法。1985年11月29日,經聯合國大會第40/34號決議通過,《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以下簡稱《原則宣言》)正式頒布。直至今日,《原則宣言》仍然被視為世界范圍內刑事被害人補償的大憲章。相比之下,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刑事被害人的保護力度明顯不足,全國人大常委會僅在2007年將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法列為立法建議項目。2009年,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聯合印發《關于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2014年,中央政法委等六部委出臺《關于建立完善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司法救助意見》),標志著國家司法救助制度正式建立,但時至今日,該制度依然停留在政策層面,距離專門立法仍相去甚遠。
由犯罪人對被害人進行賠償在實現上具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一賠償依賴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完備程度,而理論與實踐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已成共識。“如何透過社會團結之措施,將社會對于弱者之慈善化為制度性之保護制度”早已成為各國共同的課題。[2]因此,立法層面需要回應如何基于既有政策及相關實踐,為刑事被害人構建適宜的社會補償法律制度。
二、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學理評析
社會補償是基于社會連帶理論,對于戰爭、意外事件、犯罪行為等特定因素給個人造成的損害,在傳統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及其他制度無法有效救濟的情形下,以社會整體力量補償受害人的損失,使當事人不致因上述特定因素造成的傷害影響其基本生活的一種特殊的社會保障制度。[3]社會補償制度的創設是構筑新型社會保障體系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亦是對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補充。
事實上,我國當下并無一部名為社會補償法的法律,社會保障法學理體系中亦較少提及社會補償。因此,《司法救助意見》中將保護刑事被害人的有關制度稱為“國家司法救助”。在我國社會保障法律體系中,國家司法救助屬社會救助項下的專項救助之一,旨在助力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將一項本屬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冠以“國家”之名并不合適。誠然,社會保障并不排斥國家責任,且需要國家充當“給予者”對其予以支持,[4]但社會保障中的國家責任并非是完全的“國家責任”,而更應當理解為以政府責任為基礎的社會責任。因此,將作為社會保障項目之一的司法救助冠以“國家”之名難免引發誤讀。筆者認為,將國家司法救助定性為社會救助也不妥當。從體系上說,社會救助與社會補償均為社會保障法之重要組成,但二者存在本質區別。社會救助法制建構的最終目的在于形塑社會保障之最后安全網,該制度多適用于低收入或無收入的群體,系典型的無因性社會保障,即凡法定低收入或無收入者皆可申請,申請人和政府均無任何過錯;社會補償是“依據法律規定在特定情形下對于特定受害人給予的經濟補償,因社會秩序紊亂而產生,政府乃至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講,有一定失職行為”,[5]乃是有因之給付。由此可見,國家司法救助并不具有社會救助的性質,而應是社會補償制度的組成部分。因此,引入社會補償制度十分必要,對于明確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性質及其法治化的實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會補償一詞并非本土創造,而是從德國社會法中借鑒而來的。在德國,幾乎所有社會法學教科書均采用1983年漢斯·察赫爾建構的社會法理論體系,即“社會預護——社會補償——社會促進與社會扶助”。[6]這三大支柱構成了德國社會法的體系,“且它們在功能上具有相互連接、層層遞進、相互銜接、全面覆蓋的特征,使得德國的社會法成為一個體系嚴密的邏輯體系。”[7]需要說明的是,引入社會補償的概念并非意圖推翻國內原有的相關法學理論,而是嘗試以德國社會法學的觀點來梳理刑事被害人補償等核心規范。德國社會法理論體系中的社會預護制度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對人們將來必然發生的“生老病死”等社會風險提供預防性的社會保障措施,與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內涵相一致;社會促進與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相似而又存在差異(此問題并非本文關注重點,故不在此贅述)。社會扶助制度屬于社會安全保障的最后屏障,與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異曲同工,但社會補償制度,是我國目前所欠缺的。社會補償的理論基礎源于德國基本法中的社會國原則①,其目的在于保障符合社會國原則追求的目標和價值的利益,注重社會實質正義的實現。借鑒德國社會補償制度能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在我國社會保障法律體系中找到合適的歸屬,明晰制度性質,夯實制度根基。同時,與其他大多數法律制度相比,社會補償制度產生的時間不長,我國學界近幾年才將此概念引入,故其學理體系并不完善,很多方面的理論共識尚未形成。以構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并完善該制度體系為切入點,恰恰能夠起到反向促進作用,有助于社會補償基礎理論的提煉,并由此形成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更有利于加快健全相關法律規定。
三、我國構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正當性
(一)構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必要性
其一,確保刑事被害人能夠獲得有效的經濟補償。在我國,刑事被害人之權利救濟屬于刑事法范疇,其損失主要依靠犯罪人賠償得以彌補,而犯罪人賠償主要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來實現。我國實施此項制度至今已逾三十年,旨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同時附帶解決因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損失的賠償問題。這一制度的本意在于節約訴訟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也正是基于這一本意,導致該制度存在與生俱來的缺陷——附帶性:一則無力與國家打擊、懲罰犯罪行為爭奪有限的司法資源;二則訴訟結果受刑事審判牽制,勝敗并無定數。從客觀條件來看,犯罪人的賠償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制度功能的實現,亦使被害人手中來之不易的勝訴判決成為一紙空文。不僅如此,許多尚未破案或犯罪人尚未歸案的刑事案件甚至無法走到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這一步,被害人想要獲得賠償更是奢望,但社會補償制度能夠有效彌補上述不足,可確保刑事被害人獲得有效的經濟補償。
其二,司法救助的諸多弊端呼喚社會補償制度之規范設立。隨著《若干意見》與《司法救助意見》的出臺與實施,新的出路似乎初見端倪。然而,在過去的救助實踐中,開展被害人救助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緩解被害人的經濟狀況,似乎更偏重于防止被害人因生活陷入困境而反復申訴上訪甚至釀成極端事件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如此一來,文件的刑事政策導向性明顯,所有可能造成上述不良影響的群體都被納入到救助范圍。依據刑事政策說的相關理論,補償被害人一方面修復了損害、恢復了法秩序,另一方面也強化了國民對法律制度的信賴,從而為防止被害向加害轉化、贏得公眾和被害人配合與參與、刑罰寬緩化創造良好條件。[8]在這種理論的指引下,“救助的核心不再是亟需獲助的被害人,而是秩序維護和公民信賴等政治利益訴求,是將保護被害人當成了手段,背離了被害人保護的理念。”[9]但從該制度的實踐情況來看,各地標準參差不齊、政策秘而不宣;有的地方將救助刑事被害人視為“維穩”工具,[10]旨在防止其鬧事、上訪,而沒有對需要幫助的被害人給予平等保護,造成部分被害人的權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因此,在明確既有不足的基礎上,有的放矢地勾勒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構建的具體路徑,構思制度的規范體系便尤為必要。唯有如此,才能使刑事被害人得到應有的、公平的、全面的補償,使其經濟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亦可彰顯社會保障法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
(二)構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可行性
構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必要性側重于凸顯制度的重要性,但如何將這項重要的制度加以推行,還需探討構建該制度的可行性。具體來說,構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可行性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實踐中已有類似探索。我國最早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是山東省淄博市。2004年2月,山東省淄博市委、政法委與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出臺了《關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經濟困難救助制度的實施意見》,其中即規定了“對遭受犯罪嚴重侵害、無法獲得賠償的被害人予以物質救助”。此后,《若干意見》及《司法救助意見》相繼出臺,確立了國家司法救助制度。按照《司法救助意見》的要求,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紛紛結合本地區實際,出臺了國家司法救助的具體實施辦法并開展救助工作。雖然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存在諸多缺陷,但其與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在保護對象上具有相似性,均包含刑事被害人,因此,該制度在實踐中總結的有益經驗及相關數據是實施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重要基礎。
其二,社會補償制度的內在優勢及其填補價值。從整個法律體系來看,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能夠彌補其他部門法的不足;從社會保障法體系內觀之,社會補償制度亦可填補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缺漏。在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框架下,“只要犯罪事實與被害損失間具有‘相當因果關系,則被害人或其遺屬即可提出補償之申請”,[11]無需等待刑事審判結果,亦不受刑事審判結果牽制,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相比,更有利于撫平被害人內心的傷痛。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相比,當社會補償的對象不符合社會保險給付、社會救助給付之情形時,就無法通過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等獲得保障,“而當事人又遇到不幸甚至影響其正常生活,此時社會補償制度作為新型社會保障形式應運而生,其是社會安全網的一角,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12]
其三,我國已經具備實施社會補償制度相應的經濟條件。構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必須以一定的經濟基礎作支撐,因為制約制度建設的最大瓶頸往往是經濟因素。我國雖屬于發展中國家,不及發達國家財力雄厚,但以目前的經濟狀況來看,完全有實力支持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實施。國家統計局2020年2月28日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經初步核算,201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990865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比上年增長6.1%,明顯高于全球經濟增速。[13]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有關數據顯示,2015年至2018年全國各級法院每年發放的司法救助金總額均在10億元左右。[14]綜合以上各方面條件可見,我國現有資金狀況已經不是構建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障礙。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世界范圍內人權保護意識的不斷提升,以及我國法治社會的深入推進,加之過去十余年相關制度的實踐經驗現實的迫切需要,建立我國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并出臺具體立法已頗為可行。
四、構建我國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的具體路徑
(一)厘清補償對象
我國被害人群體數量巨大,單就資金方面考慮也不可能對所有被害人都進行補償。聯合國《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第12條把遭受嚴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體傷害或身心健康損害的受害者作為補償對象,沒有規定對所有刑事被害人都須進行補償。許多國家在構建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時大多也對補償對象的范圍加以限制,僅將因故意的暴力犯罪遭受人身傷害或者死亡后果的被害人作為補償對象,而侵犯財產的犯罪一般不屬于可補償的對象。[15]因此,我國在進行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立法時也應結合我國刑法具體規定以及我國的實際情況對補償對象進行限縮,以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及公平性。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3條規定,在被害人為公民的情況下大致可將犯罪行為分為兩類,一是侵犯公民私人所有財產的犯罪,二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犯罪。如前文所述,許多國家在確定補償對象時多排除財產犯罪的受害人,德國學者艾伯哈特.艾亨霍夫認為,社會補償的主要目的在于填補“個人的損害”,而非“財產的損害”。[16]人身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因承擔醫藥費、喪失勞動能力而遭受多重痛苦甚至陷入經濟窘迫的困境,而財產犯罪的被害人只有財產損失并未喪失勞動能力,受補償的必要性、緊迫性相比前者較弱。因此,結合我國刑法規定,將我國被害人社會補償對象表述為“排除純粹的財產犯罪的被害人”似乎更加嚴謹。同時,并非人身法益遭受侵害皆可被納入補償之列,亦要求造成嚴重的后果,即被害人重傷或死亡,其判斷標準可徑行采用刑法上之認定標準,并無再造之必要,以防止多重標準引發學理及適用上的混亂,亦可避免多次鑒定,從而減輕當事人的負擔。
除前文所述,還存在這樣一類被害人,犯罪行為并未造成其身體上的器質性損害,也未造成其直接財產損失,但犯罪行為使其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多為性犯罪被害人)。[17]是否應將此類被害人納入補償范圍目前尚存爭議。筆者認為,即便聯合國《原則宣言》第12條將“身心健康損害”的受害者納入補償范圍,很多國家的立法中也有類似規定,但就我國當前實際情況來看,暫時還不宜將其納入社會補償對象范圍。正如人身法益受到侵害時將損害程度限定為被害人重傷或死亡,精神受損時亦不能不問其受損程度,故應限于精神“嚴重”損害的被害人。“嚴重”一詞并不如“重傷” “死亡”等表述具體,對于精神損害是否達到“嚴重”的程度不能僅憑主觀判斷。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38條規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見,原則上我國刑事領域并不存在精神損害賠償,亦不存在相應標準。①民事侵權領域中雖有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定,但民法與刑法保護的法益不同,引發精神損害賠償的原因自然不一致,對刑事被害人進行補償時無法參照。在無法確定判斷標準的情況下貿然將此類被害人納入補償范圍,不應是制度實施初期的明智選擇,應待相關法律出臺后,且制度運行日趨平穩時,再考慮將此類被害人納入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范疇。
依據《司法救助意見》的規定,如果被害人死亡,補償對象則為被害人近親屬,但在該文件中并未就近親屬的范圍及其受領補償金的順位做出具體安排。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1045條,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并在第1127條中就繼承順序做出了具體安排,其中第一順序繼承人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順序繼承人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但是,補償被害人近親屬側重于保障被害人近親屬的生存權,故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應在《民法典》的基礎上對近親屬的范圍做一定限縮并加以區分。我國臺灣地區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給付金支給法》(以下簡稱《給付金法》)中均將被害人死亡時的補償對象稱為“遺屬”,以便與近親屬的概念相區分。從我國社會保障法的語境分析,《社會保險法》第17條、第38條、第49條中出現了“遺屬”與“供養親屬”兩種不同的稱謂,其中第38條第8項規定了從工傷保險基金中支付的費用包括“因工死亡的,其遺屬領取的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因工死亡補助金”,此處即出現了的“遺屬”與“供養親屬”不同的稱謂。《社會保險法》中關于遺屬的規定基本與《民法典》中有關近親屬的規定相同,而供養親屬則是指由該職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的近親屬。因此,為維護社會保障法中各項制度的一致性,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不妨繼續沿用遺屬之稱謂,但是關于被害人遺屬受領補償金的問題還應結合具體的補償項目予以綜合考慮,申請的補償金中若包含扶養費一項則要求該遺屬依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因為該給付之性質與被害人之財產有異”。[18]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補償資金的浪費,以使得真正有需要的遺屬得到補償。
(二)明確補償條件
在以往的實踐中,刑事被害人或者其遺屬獲得救助的條件是因遭受犯罪侵害致使其“生活困難”,作出此種限制似乎是出于國家財政承受力有限的考慮。然而,刑事被害人補償若以被害人或其遺屬經濟困難為限,則須對補償申請人進行資產和收入調查,如此便會大大降低補償效率,難以為被害人或其遺屬提供及時的有效幫助。雖然目前我國的刑事被害人群體較龐大,但在已經限定補償對象為重傷被害人或被害人遺屬的前提下,這一數目會大為減少,再附加“生活困難”這一限制條件似乎并無必要,反而會消減該制度的救急功能。同時,去除這一限制條件可有利于克服實踐中“大鬧多給、小鬧少給、不鬧不給”的弊病,擺脫功利主義之嫌,亦可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補償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不設置生活困難的限制條件并不等于在補償金的發放上完全不設限制。基于“自我引起被害”和“救助有違公平”的原因,各國被害人補償的排除條款通常包括但不限于:被害人過錯、被害人與犯罪人屬于同一家庭成員、被害人不配合司法機關等。[19]因此,即使被害人符合前述所有要求,但存在排除條款中規定的情形,也不能獲得補償或不能獲得全額補償。我國在立法時亦可結合實際情況對上述條件進行取舍,使立法更具合理性,更能符合一般社會公眾的公平正義觀念。另外,從提出申請到補償金的發放尚有一段時間間隔,因此對部分有急迫需要的被害人可進行先行補償。這一做法實際源于日本《給付金法》中的“假給付金制度”。此項制度規定,如果公安機關因被害人的傷害程度等有關事實不清,不能立即作出決定的,則采取“救濟前置主義”,按政令確定的數額先支付1/3的暫時補償金。[20]我國亦可采取這種方式,對確有緊急需要的被害人或其遺屬先行發放部分補償金,從而解決部分被害人的燃眉之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但總體來說應以一般補償為原則、以先行補償為例外,先行支付的金額須在最終確定的補償金數額中予以扣減。
(三)拓寬補償資金來源渠道
充足的資金是制度得以建立并良性運行的基礎,倘若資金不足,再完備的制度也終究是一紙空文。墨西哥在1929年、古巴在1936年曾嘗試建立被害人補償制度,但均因資金不足而以失敗告終。[21]目前,我國司法救助資金的籌集主要依靠政府主導、社會廣泛參與,而建立專門的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則應實現補償資金的專款專用,政府在制定每一年的年度預算時應對發放的刑事被害人補償款專項列支。需要注意的是,國家財政撥款固然穩定可靠,但絕不能視其為唯一,把所有的責任都強加給政府,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來保障制度的實現是不現實的。若完全依靠財政支持,大可直接稱其為國家補償,但該制度的社會性便無從彰顯。因此筆者認為,一方面,資金籌集需要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應呼吁社會公眾和公益組織對刑事被害人給予充分的關注與關懷,調動社會公眾和公益組織積極參與刑事被害人援助工作,踴躍捐款捐物,從而達到擴充資金來源的目的。此種做法不僅有利于刑事被害人得到更多幫助,而且還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有利于和諧社會之構建。另一方面,亦可將監獄服刑者的部分勞動收入納入補償資金以補充資金的不足。我國《監獄法》第72條明確規定參加勞動的服刑人員有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但并未規定服刑人員勞動報酬的具體分配方案。國外一些國家針對服刑人員勞動報酬的處分方式可供我國借鑒:“罪犯的勞動報酬并非悉數交與罪犯本人,大多分作數項:上繳國家;犯人在被拘禁期間的正常支出(包括本人和其家屬);賠償受害人;釋放后使用的儲蓄金。”[22]保障監獄服刑者的勞動報酬權并將其勞動所得分公私兩項使用的做法為拓寬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資金的來源提供了新思路。勞動報酬一部分為服刑人私有,可以調動其積極性,提升勞動效率,進而使補償資金不斷增加,為財政支出減輕負擔。如此一來,不僅使服刑人員的勞動報酬權得到切實保障,也有助于被害人社會補償的權利得以落實。
(四)框定補償事務管理機構
與社會公益活動不同,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具有較為顯著的公權屬性,故而其主管部門應為國家機關。在以往的實踐中,補償事務由公安機關、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處理。就法院而言,雖對案件事實有著深入的了解,但不宜管理此項事務,原因有二:其一,刑事案件由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后法院開始介入,若此時便開始處理補償事項,未免有未審先判之嫌;其二,若在刑事案件審理結束之后處理,又會使社會補償制度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殊途同歸,增加了法官原本就繁重的工作量,被害人也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補償,公安機關、檢察院亦是如此。因此,筆者建議由民政部門和公安機關共同管理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事務,以民政部門為主,公安機關為輔。因為維護弱勢群體的權益是民政部門的一項重要職能,刑事被害人作為逐漸走進人們視線的“弱勢群體”,將其補償事務交給民政部門管理亦是“民政”工作內容中的應有之意。同時,民政部門屬于行政機關,在資金調撥方面存在優勢,也便于接受社會捐款。[23]但是,民政部門并不了解案件事實,也不能僅憑被害人的一面之詞予以判斷,為了節約時間及人力物力成本,公安機關應予以協助。之所以選擇公安機關而非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是因為公安機關介入案件最早,加之刑事案件的偵查多由公安機關負責,方便調取證據資料,可為民政部門提供及時、可靠的案件信息。公安機關只是協助民政部門了解案件事實,真正與被害人接觸的只有民政部門,這就避免了部門之間相互推諉。此外,民政部門和公安機關同屬行政機關,若被害人不服補償決定,可直接依照《行政復議法》及《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方式對自身權利進行救濟,避免在救濟程序上另設規定,造成制度冗余。
【參考文獻】
[1]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EB/OL].最高人民檢察院網,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006/t20200602_463796.shtml#1.
[2]郭明政.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后民法與社會法法律時期的成熟標桿[J].政大法學評論,1998,(04):308.
[3][5][12]鄭尚元主編.社會保障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314,317,323.
[4]《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編寫組.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02.
[6]郭明政.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M].翰蘆圖書出版公司,1997:130.
[7]楊士林.論德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社會法的基本范疇[J].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4):15.
[8]PeggyM.Tobolowsky,Crime Victim Rights and Remedies[M].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1:159.
[9]趙國玲,徐然.刑事被害人救助立法根基的比較與重構——從救助和補償的概念之爭談起[J].東南學術,2015,(01):154.
[10]黃華生,徐世民.我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回顧與展望[J].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學報,2019,(01):47.
[11][17][18]社會法[M].元照出版公司,2015:319-323.
[13]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逼近百萬億元大關[EB/OL].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shuju/2020-02/29/content_5484777.htm.
[14]最高法:2018年發放司法救助金10.75億元[EB/OL].中國法院網,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2/id/3738277.shtml.
[15]陳彬,李昌林.論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J].政法論壇,2008,(4):55.
[16]EberhardEichenhofer,Sozialrecht der Europ?ischen Union[M].Erich Schmidt Verlag,2003:416.
[19](日)大谷実,斎藤正治.犯罪被害給付制度[M].日本:有斐閣,1982:67.
[20]盧希起.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77.
[21](日)大谷実.刑事政策學[M].黎宏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11.
[22]王素芬.罪犯勞動報酬權之省思——一個歷史與比較的視點[J].法學,2004,(04):40.
[23]申小紅.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比較[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5):55.
(責任編輯:趙婧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