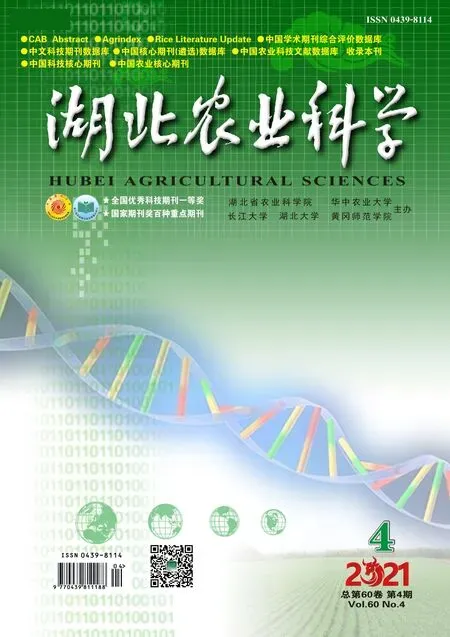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研究
謝 慧,曾 偉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公共管理學院,武漢 43007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6%上升到2017年的58.52%,增長了2.325 倍。但是,快速城鎮化也導致了一系列環境問題的出現或加劇,因此,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當前中國處于城鎮化加速發展時期,城鎮化發展引起的生態環境問題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黨的十八大提出實現“五位一體”;201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黨的十九大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政府引導下,實現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成為城鎮化的發展方向。武漢市作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是國家級重要的工業基地、科教基地和交通樞紐,是中國快速城鎮化的典型代表。2015年武漢市GDP 超過10000 億元,2016年城鎮化率超過80%,但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很多生態環境問題也隨之出現。為此,有必要加強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問題研究。
1 研究述評
關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互動關系,國外研究開始較早,起源于19 世紀末埃比尼澤·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田園城市理論強調利用規劃實現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和諧有序發展。20 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Grossman 和Krueger 使用面板數據對42個國家的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統計分析,發現了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即生態環境隨著城鎮化發展的變化軌跡呈現倒“U”型曲線。后來,許多學者對這一曲線進行了驗證,這種研究方法被國內外學者廣泛應用。
國內關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互動關系的研究可以分為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兩個方面。馬世駿等[1]提出了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認為社會、經濟、自然雖然是3 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是各自的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的制約,王如松等[2]對此進行了擴展。此后,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作用機理的分析。周正柱[3]把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關系用圖示的方式表示,旨在說明城鎮化對生態環境存在脅迫與改善兩個方面的作用,生態環境對城鎮化存在支撐與約束兩個方面的作用,同時可以利用外部環境中的體制機制、政策法規等對兩系統進行調控。以理論研究為基礎,國內實證研究相對較多,大多都是通過構建兩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來綜合評價兩系統的發展是否和諧。學者們利用了多種實證研究方法,包括耦合協調測度模型[3-5]、生態環境響應模型[6]、模糊物元模型[7]、灰色關聯度模型[8]、主成分分析法[9]等方法。研究范圍廣泛,覆蓋了黃河三角洲地區[10]、中原經濟區[11]、西北地區[12]、中東部地區[13]、四川省[14]、湖南省[15]、呼和浩特市[8]、金華市[16]等區域、省域、市域等。研究結果多是分析研究區域城鎮化與生態環境所處的耦合協調階段,并根據綜合發展水平滯后狀況判斷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脅迫與約束效應,從而提出對策建議來指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國內外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互動關系的大量研究為兩系統協調有序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參考,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豐富的基礎。但是,由于不同區域、不同城市存在較大差異,不能以統一的模式指導城鎮化和生態環境的發展。同時,鑒于武漢市作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城市,其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狀況對周邊城市也會產生影響,而當前關于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研究較少。本研究基于武漢市2008—2017年的數據,運用熵值法、變異系數法、耦合協調度等計量分析方法,對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綜合發展水平和耦合協調度進行分析,為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
2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關系機理
城鎮化,一般認為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過程,但不同學科對城鎮化的定義不盡相同。從人口學角度而言,城鎮化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城鎮化是農業活動向非農業活動轉換;從地理學角度而言,城鎮化包括地理空間的轉換;從社會學角度而言,城鎮化包括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的改變。綜合各學科領域對城鎮化的理解,城鎮化系統包括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社會城鎮化4 個方面[17,18]。關于生態環境系統,學者們一般通過壓力-狀態-響應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對其進行研究[19]。生態環境狀態即通過資源狀況、環境質量來測算生態環境的水平;生態環境壓力即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由于不當的生產、生活方式等給生態環境帶來污染、破壞等;生態環境響應即采取一定的措施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城鎮化與生態環境都是極其復雜的系統,這就決定了兩系統之間的交互耦合也極其復雜。綜合學者們的觀點[3,20],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具有雙重效應,城鎮化的發展帶來經濟的增長,可以為保護和治理生態環境提供資金保障和技術支持,但是城鎮化在發展過程中如果過度消耗能源資源、排放污染物,則會造成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等問題;而生態環境為城鎮化發展提供各類物質基礎與資源,生態環境的惡化也會反過來制約城鎮化的發展。本研究基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系統各自的內涵,結合學者們的研究成果[3,21,22],兩者相互作用關系如圖1 所示。

圖1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關系機理
3 研究設計
3.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內涵是科學測度兩系統耦合協調的關鍵,基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內涵,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3,10,16,19,23,24],本研究從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社會城鎮化4 個要素層面選取了22 項指標來表征城鎮化系統,從生態環境狀態、生態環境壓力、生態環境響應3 個要素層面選取了22 項指標來表征生態環境系統,構建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具體見表1。

表1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
3.2 數據來源及處理
3.2.1 數據來源 關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8—2017年)、《湖北統計年鑒》(2008—2017年)、《武漢統計年鑒》(2008—2017年),并以武漢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8—2017年)、武漢市綠化狀況公報、武漢市環境統計公報、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庫、中國區域經濟數據庫、中國城市數據庫、中國城鄉建設數據庫、湖北省縣市統計數據庫作為補充。
3.2.2 數據標準化處理 由于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指標體系中各指標項量綱差距較大,需要進行標準化處理。本研究采用極值法進行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式中,xij表示第j項指標第i個樣本的原始數值,j=1,2,3,…m,i=1,2,3,…n,xmax表示第j項指標原始數據中最大的值,xmin表示第j項指標原始數據中最小的值,x′ij為標準化值,取值在[0,1]。
3.3 指標賦權
指標賦權的方法有很多,為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影響,本研究采用熵值法和變異系數法這2 種客觀賦權法對指標進行賦權。
熵值法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1)求第j項指標下第i項值的比重Pij:

2)求第j項指標的熵值Ej:
3)求第j項指標的效用值Dj:


4)第j項指標的權重

變異系數法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1)第j項指標的變異系數Vj:

式中,σj和分別是第j項指標的標準差和平均值。
2)第j項指標的權重:

3)求熵值法和變異系數法兩者權重的算術平均值,即指標的最終權重:

3.4 研究模型
3.4.1 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 借鑒相關研究[16,25],評價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程度,首先需要度量兩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
綜合發展水平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Ui是指武漢市第i年的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Ei是指武漢市第i年的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Wj是第j項指標的權重;Pij是標準化后的數值。
3.4.2 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模型 借鑒相關研究[3,26],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兩系統的耦合度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式中,Ci為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兩大系統的耦合度,取值范圍在[0,1],取值越大,表明兩系統相互影響程度越深。
但是,僅用耦合度模型無法完全反映系統的相關性[18,23]。因此,需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進一步分析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
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Ti是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指數;α和β是待定系數,分別表示城鎮化和生態環境在這個大系統中的重要程度;Ci是耦合度;Di是耦合協調度。考慮到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同等重要,本研究取α= 0.5,β= 0.5[16]。耦合協調度的取值仍然在[0,1],數值越大,表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況越好;反之,數值越小,表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越不協調。
借鑒相關文獻[6,17,23]使用的耦合協調度發展類型的劃分來確定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類型及劃分標準,具體見表2。
4 結果與分析
4.1 綜合發展水平評價分析
根據前文建立的公式,計算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和耦合協調度,確定其發展類型,具體見圖2 和表3。
由圖2 可知,2008—2017年武漢市城鎮化發展水平呈波動上升態勢,綜合發展水平較高。具體而言,可以劃分為4 個發展速度不同的階段:2008—2012年,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由0.0303 上升為0.5270,城鎮化發展速度很快;2012—2014年,城鎮化發展增速放緩,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由0.5270 上升為0.6700;2014—2015年,城鎮化發展增速大幅提高,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由0.6700上升到0.8165;2015—2017年,城鎮化發展速度再度放緩,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由0.8165 上升到0.9249,武漢市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較高。武漢市城鎮化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得益于武漢市擁有良好的政策規劃,包括1996年制定的《武漢市城市總體規劃(1996—2020年)》以及2010年在主要發展目標已基本實現的背景下制定了新的城市總體規劃,對武漢市城市發展的各方面做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
同樣,2008—2017年武漢市生態環境發展水平也呈波動上升態勢。具體而言,也可以依據發展速度劃分成4 個不同的階段:2008—2010年生態環境發展較快,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由0.1612 上升為0.3343;2010—2011年生態環境發展增速放緩,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由0.3343 上升為0.3433;2011—2015年生態環境發展增速加快,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由0.3433 上升為0.7483;2015—2017年生態環境發展速度再度放緩,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由0.7483 上升到0.8037,武漢市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較高。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勢必會對生態環境帶來一定的壓力,但在2008—2017年,武漢市生態環境的綜合發展水平也是一個穩步上升的狀態,這主要得益于城鎮化的發展會促進經濟發展從而提供更加優質的環境,以及政府重視環境問題從而出臺了相關政策,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城鎮化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壓力控制在生態環境可以承受的范圍內。例如,2005年武漢市頒發了《武漢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2007年武漢市經過國務院批準成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圖2 武漢市城鎮化和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變化曲線

表3 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耦合協調度及發展類型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數整體處于上升發展趨勢,綜合評價指數曲線始終處于城鎮化和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曲線之間,這說明兩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由城鎮化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共同決定,任何一個系統的發展跟不上,都會影響綜合發展水平。由圖2 可以看出,雖然兩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都處于上升發展趨勢,但2008—2010年武漢市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領先于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2010年后,武漢市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開始滯后于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2009—2010年武漢市進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軌道交通、長江隧道以及武漢市鸚鵡洲大橋等建設項目,基礎設施的發展在提高武漢市城鎮化水平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對生態環境綜合水平的提高產生了約束效應。武漢市在發展城鎮化的過程中有必要進一步加大保護生態環境的力度。
4.2 耦合協調度評價分析

圖3 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變化曲線
由表3 和圖3 可知,2008—2017年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兩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呈現不斷上升趨勢,兩系統的協調性不斷增強。同時,兩系統的耦合度水平也較高,兩者交互關系密切。但是,整體而言,耦合協調度低于耦合度,體現出了高耦合未必高協調的特點,說明了兩系統的協調性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從耦合協調等級來看,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可以劃分為4 個等級(表3)。其中,2008年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系統處于中低度協調,這是由于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發展水平均較低;2009—2011年武漢市城鎮化水平得到提高,生態環境質量也得以改善,耦合協調等級上升為中度協調;2012—2013年耦合協調等級發展為中高度協調;2014—2017年耦合協調等級發展為高度協調。2008—2010年,城鎮化發展滯后,2011—2017年生態環境發展滯后,部分原因在于城鎮化的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生態環境發展水平提高速率落后于城鎮化發展水平提高速率。總體來說,2008—2017年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由中低度協調、城鎮化滯后型發展為高度協調、生態環境滯后型,發展趨勢向好,同時說明了當前武漢市有必要進一步加大保護生態環境的力度。
5 小結與討論
通過對2008—2017年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研究,結果表明,2008—2017年武漢市城鎮化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均呈波動上升態勢,綜合發展水平均得到了較大提高,耦合協調度也由中低度協調發展為高度協調,但是,2010年后,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滯后于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武漢市有必要進一步加大保護生態環境的力度。
武漢市生態環境發展水平滯后于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兩方面:一方面,當前經濟增長仍然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高速的經濟增長會消耗大量的能源資源,產生較多的污染,這一局面無法避免;另一方面,武漢市當前的經濟結構雖然有所升級,但是第二產業所占比重仍然較大,大量的工業企業會產生較多的污染,導致生態環境壓力仍然較大。因此,武漢市接下來的發展方向應是進一步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具體措施包括:①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進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努力提高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利用武漢市的區域優勢,發展物流業,加強旅游文化產業;加大對環保產業的投入力度,大力發展環保產業等。②深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發展資源節約型經濟,發展節水、節電、節地型產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形成循環經濟產業鏈;合理規劃地區招商引資,控制污染企業的進入,優先引進環保企業。③大力發展教育,培養創新人才。創新人才有利于新技術的研發,有利于環保技術的創新,武漢市應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培養大量高層次創新人才。④推動制度創新,完善法律體系,推進在“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方面的制度創新,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確保各種有利于兩型社會建設的行為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