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時代的刑民責任界分與承擔
曉今

2020年12月6日,第十一屆博和法律論壇在上海舉辦
《民法典》的頒布使我國正式構建起了系統性的民事法律體系。在《民法典》實施之際,刑法如何與時俱進與之銜接協調,是理論界與實務界熱議的焦點話題。如何解決刑民法律關系的交叉與競和,如何明確刑民法律關系責任的界分與承擔,如何協調刑民法律價值選擇與規范體系等問題,都具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研究價值。
本屆論壇主辦方為上海市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上海市普陀區法學會、上海博和漢商律師事務所。在主辦方的歡迎辭中,上海市律師協會副會長、上海博和漢商律師事務所主任林東品認為:“刑民交叉、界分、協調問題的探索已不再是一個法律應用的技術性問題,而是對法律關系、法律責任、法律制度,甚至法律文化等一系列涉及法治本源的深刻追問;也不再僅僅是實現個案公正的現實需要,而是實現核心行業法治大衡的必由之路。”也正是基于這點,論壇邀請了民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等多領域、多學科的全國知名專家學者,邀請了資深檢察官、法官、律師大咖,共同探討民法典時代罪與罰的相關議題。
“我們是不是要出刑法典呢”
施偉東/上海市法學會專職副會長:
在民法典時代,我們刑法人,特別是刑法學的專家學者怎么面對刑民交叉問題?我們要針對界分刑民交叉問題做出有效的協調,首先是慈悲心腸,再是雷霆手段,應該以謙抑審慎的態度來把握法律的實踐、認知。
受《民法典》出臺的激勵,現在有學者提出我們是不是要出刑法典呢?我想這也是一個可考慮的選項,但前提是研究,對于未來中國法治建設,如果需要一部刑法典,我想在大家的努力下是可以推動實現的。
“重刑主義在刑民關系中留下了很多負面影響”
楊興培/華東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刑民關系發展到今天,跟它的歷史走向是有緊密關系的。
中華民族在法的觀念、法的源頭、法的制度上一開始就是以“嚴刑竣法”登上歷史舞臺的。據史書記載,中國最早的刑事案例是以“刑殺立威”開始的。《國語》和《韓非子》都有記載:傳說禹會諸侯于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怒而殺戮之”。我想不過就是違反行政法規或者說最多對禹有點不尊重,何必殺頭呢?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以刑殺可以立威,以刑殺可以維護權貴。
重刑主義讓我們在刑民關系當中留下了很多負面影響和沉重的包袱。我想用六個方面來加以概括:
一,“先刑觀念”模糊了刑民界限,造成了刑法一法獨大的局面;二,“先刑觀念”違背了刑法屬于第二次違法規范形式的原理,損害了前置的權威性;三,“先刑觀念”助長了社會的獵奇心理,大量浪費司法資源而效果適得其反。四,“先刑觀念”必然會增加犯罪總量,加重了監獄的關押壓力;五,“先刑觀念”會助長一些人的哀情表演,通過社會輿論“綁架”司法機關;六,“先刑觀念”往往會導致片面解釋刑法,造成刑法技術運用的走樣。
“刑法和民法的觀察角度和解決方案有很大差異”
車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刑法和民法雖然不是包含性的全面接壤的關系,但也是接壤程度最高的兩部法。過去我們一直講刑法是民法的保障法,但實際上這種說法過于簡單。實際上這兩個法之間的關系很復雜,刑法相對于民法而言有一定的獨立性,也表現出某種重復性。獨立性體現在雙方有的時候會共用一個法學概念,但僅僅是形式和名稱相同,這個概念的實質內容和界定方法差別很大。另一方面,在有些不同的概念當中刑法內容的確立也會受到民法的影響,這就是刑法相對于民法的從屬性。獨立性首先體現在思維方法上,我個人覺得刑法更側重于實質性的思考,民法更強調規范性思考。比如我們都知道民法可以根據一個人失蹤的時間來決定他在法律上、規范上成為一個“死人”,進而展開財產分割,但是對于刑法來說必須“活要見人死要見尸”。對于死亡,民法可以規范性地決定,刑法則必須事實性地認定,如果一旦出現規范性認定,就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很多“亡者歸來”的冤案往往就是由于沒有踐行刑法“死要見尸”這樣一個事實性認定所造成的。當然,有的時候刑法也有強調規范性的部分,比如刑法規定14歲年齡以下不負刑事責任,但是一個13歲的殺人犯事實上完全理解殺人的含義,一個15歲或16歲的智力異常兒童可能腦子不太靈光,只能給那個13歲的少年當一個跟班,但是13歲殺人不負刑事責任,15歲殺人要負責任,這是刑法規范上的界定,這個時候不去考慮某個犯罪人事實上的認知和控制能力。除此之外,刑法和民法的規范目的不同,社會任務不同,因此有的時候面對同一個社會現象,觀察的角度和解決方案就會有很大的差異。
“個人信息保護更多是民刑互動的問題”
韓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政法大學企業合規與監察研究中心主任:
在個人信息保護問題上,民刑法之間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差異:
第一個差異是保護的客體。民法規范對個人信息的界定劃分為私密信息和非私密信息,分類的意義在于從個人行動自由、生活安寧和人格尊嚴角度對個人信息作出區分。
而刑法規范是將個人信息區分為所謂的個人敏感信息和個人一般信息。其背后所代表的立法邏輯可能還是考慮到個人信息中所承載的行動自由、人格尊嚴,同時反射出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因此,兩個不同的法律規范體系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出發點、落腳點有差異,但的確是互相關涉的。
民法盡管強調人的識別性、人的尊嚴、個人身份的還原性,但是對個人身份的還原性的考慮也事關公共秩序、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同時,盡管刑法從公共秩序入手來規范個人信息和分類個人信息,但是它一定指向每個人的人格尊嚴和行動自由。因此兩個立法在立法目的上是高度交融和高度結合的。
第二是關于個人信息保護法益范圍的差異。關于這個問題,民法的視域,個人信息本身不具有法律保護地位,保護個人信息更多是從對個人信息的數據、素材所反射、承載的特定的人身權益、人身利益的保護來加以考慮的。
而刑法的個人信息保護除了個人的人格利益以外,更多的還是考慮一種超人格利益、超個人利益的法律范疇,也就是經由個人的人格法益上升到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乃至于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的保護。
第三個就是關于民法和刑法對于侵害個人信息不法行為不法性界定的差異,這是一個理論難題,也是民刑交叉、交融的一個關鍵點。我們一般認為在民事侵權責任的范疇里面,界定行為的不法性主要從三個方面來加以考慮,如果一個行為直接侵害了絕對權,這樣的行為天然具有不法性。比如說侵害生命權、健康權等。第二個層面,違反保護性的法律是構成民事不法行為的第二個認定標準。當然,保護性的法律本身也有其局限性,成文法國家的規范總有一些漏洞和不足,因此我們還發展出來第三個規范,就是以故意背離公序良俗的方法加害他人利益的,是作為民事不法行為一個兜底性的規定。
“怎樣在刑民交織的案件里追究刑事責任呢”
張紹謙/上海交通大學刑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關于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區別主要有七點:第一,體現了法律關系的主體不同,刑事關系是國家和犯罪分子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公法關系,體現了懲罰和被懲罰,而民事關系體現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自治關系;第二,法律責任的本質不同,刑事責任體現的要么是道義和譴責,要么是社會責任上的預防和矯治,而民事責任本質是利益的恢復和社會關系的修復,它體現的是對被侵害者個人利益訴求的滿足;第三,兩種法律責任的正當性基礎不同;第四,法律責任的嚴重程度不同;第五,法律責任的規范依據不同,刑事責任依據的是刑法,不允許法外制裁,而民事法律關系依據的是《民法典》,追究民事責任,除了依據法律規定以外,一定條件下還允許根據傳統習慣、公序良俗等非民事法的規定來進行裁判;第六,強制性和專屬性程度不同;最后一個是法律責任的追究程序不同,刑事責任必須嚴格依照刑事訴訟來追究,一旦起訴,除非是自訴案件,否則就不以當事人意志為轉移,而且對于證明的標準要求比較高,而追究民事責任程序相對比較寬松,而且證據的證明沒有要求達到必須排除合理懷疑,高度蓋然性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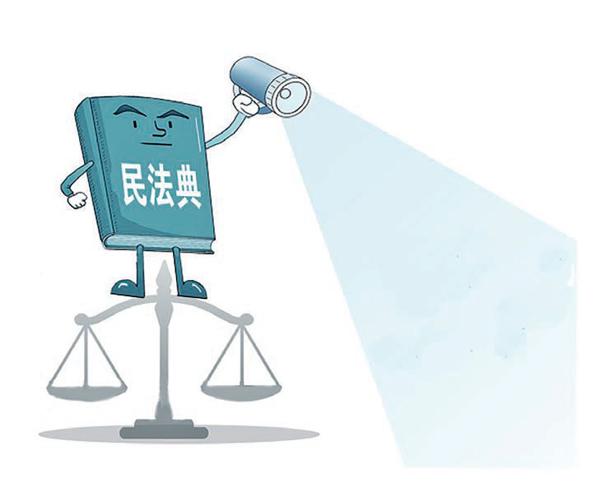
有的時候一個行為同時產生刑事、民事兩種責任,但因為追究的程序和證明標準不同,導致無法滿足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序要求或者達不到追究刑事責任的證明標準時,案件性質就可能轉為民事案件,追究民事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樣在刑事、民事交織的案件里面追究刑事責任呢?我個人感覺基本思路有以下幾點:
第一,應當嚴守罪刑法定原則,避免刑法介入民事糾紛;第二,要堅守刑法謙抑精神,避免濫用刑事責任;第三,要重視刑法二次規范的性質,正確協調刑事和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范圍;第四,懲罰犯罪應當與維護被害人的利益并重,要重視社會關系的修復;最后,需要根據刑民責任的不同情況區分處理。
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是兩種不同的法律責任,司法認定時首先必須嚴格區分,不能混淆,讓刑法的歸刑法、民法的歸民法,讓可刑可民的盡量歸民法;其次,要充分重視發揮兩者的作用,該并存的并存,該轉化的轉化,該影響的相互影響,使兩種責任在我國整體法律體系中和諧相處、協同作用。
“我非常贊同刑法的歸刑法,民法的歸民法”
朱曉喆/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比較民法與判例研究所所長
本質上來說,刑民交叉其實是一種法律的競和現象,我們在刑法內部有各種法條的競和,在民法內部也有各種請求權的競和。現在刑法和民法同時去關照同一個案件事實的時候也發生了競和。剛才張老師講刑法的歸刑法,民法的歸民法,要依據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截然不同的構成要件認定相應的法律責任后果,我非常贊同這一說法。
民法對于損害賠償、財產返還有相關的認定標準,而且是比較開放的。民法已經到了對于受害人的權益保障比較成熟的程度,刑法為什么要固步自封呢?我們是不是要把刑法中保護受害人財產權益或者精神損害賠償權益的部分功能交給民法?我觀察了很多實踐當中的案件,涉及刑民交叉的案件,大部分可能是操作銜接上的問題,所謂民刑交叉或者民刑沖突究竟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我是比較存疑的。當然,最后司法機關在處理交叉案件的時候最好進行協調,以實現法秩序的統一。
“數據能不能作為刑法當中的財物”
勞東燕/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眼下,當我們說刑民方面法秩序統一性的時候,只是以行為性質作判斷,應該遵守一種原則,或者非法,或者合法。但是相同概念有可能要做不同的解釋,這里面就涉及民法對于物權、債權、知識產權是有三分的,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都有可能作為刑法上的保護客體。而財產犯罪是以傳統的財產犯罪理論,即以侵犯物權和侵犯債權的框架建立起來的,其行為對象和認知客體不包括知識產權。
當然,有一點也必須要承認,我們刑法當中對于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的保護的確不只是為了保護民法中抽象的權利,我們是要使得民法對于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的行使,在現實上成為可能,所以我們保護的是事實性的支配、占有。如果有不法行為人要直接拿走你的財物的話,你在民法上的所有權不受影響,但是你作為所有權人對于所有權的行使就會受到阻礙。
眼下刑法保護模式當中對于一般財物的保護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區分的,我強調的是,數據能不能作為刑法當中的財物?在討論虛擬財產的時候,刑法學界比較主流的觀點往往認為它具有經濟性的意義,可交換,直接把它放到財物當中。可是我們發現數據本身跟知識產權一樣,它是具有共享性的,但是跟知識產權不同的地方就是知識產權的權利具有專屬性,而數據不具有專屬性。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如果不放到一般財物當中,為什么權屬更加薄弱的數據能夠放到財物當中保護呢?這一點顯然是值得反思的。
民法上的占有和刑法上的占有,因為保護目的、構成要件的不同,一個偏重于事實,一個偏重于規范。
“我不太贊成說‘刑民交叉是偽命題”
姚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不太贊成說“刑民交叉是偽命題”,哪個刑事犯罪不涉及民事啊?今天很多學者都提到了不同的構成要件、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價值判斷,諸如此類,這才有銜接的問題,而且是全方位的。
另外,兩個法的角色功能是不同的,在社會規范體系當中的定位不一樣,是不是有一個先后或者手段上適用不同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在評判民事法律行為時,適用的法律當然首先是民事法律或者司法規范。
民刑兩法在銜接的時候要考慮到一個原則,就是刑法的謙抑性,刑法是作為最后手段,要先從民法的角度去看待問題。
“法律有能力解決過去的問題,也有能力回應新發生的情況”
黃祥青/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
就刑民交叉問題,我談三個具體的觀點。
第一,刑民交叉問題討論的范圍。一些具體的行為究竟是屬于犯罪行為還是屬于一般的民事違法行為,犯罪的界限界定在何種程度?這樣的問題是經濟活動當中一個罪與非罪的問題,可以去普遍討論的。嚴格來講,刑民交叉應該是兩個主體同時并存。對罪與非罪的問題,一旦法律的界限和政策明確以后,要么就是一個刑事犯罪的問題,要么就是一個民事違法、追究民事責任的問題,并不存在兩者同時并存和交叉。所以把這樣的問題區分開來,是有利于我們行業對刑民交叉問題進行更深一步討論的。
第二,討論的標準問題。我認為無論是按照同一法律關系還是同一事實,似乎都不及用行為更能夠解決相關的法律問題。用行為的觀點來看,它是法律關注的重點,法律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都共同關注行為及其相應的法律責任。我們可以把單一復合的主體和復合的行為看作是復合行為,復合行為就應該在一個法律體系下,或者說有秩序地在多個法律體系下分別進行評價,而不能對復合行為刑事作刑事評價,民事作民事評價,甚至得出明顯背離的評價結論,我覺得這是不合適的。所以我認為,刑民交叉問題研究的基礎對象首先要聚焦行為問題,行為包含單一行為,也包含復合行為。
第三,我們聚焦這些行為,聚焦相關的重點問題以后,如何來解決它的法律責任問題。對于同一個問題,刑事和民事法律都有規定的情況下,應該堅持刑法的謙抑性,這是一個基本的立場。
我們在堅持這些手段的前提下也應該關注現實和未來的問題,因為我們很多法律、規范更多地是在過去的基礎上形成的經驗、規則,但是我們實際生活當中許多新問題尚未形成立法和司法解釋等有效法律手段,這些新型問題能不能用既存的法律手段去解決呢?我覺得法律有能力解決過去的問題,也有能力回應新發生的情況,不能說我們的法律對于未來沒有規制效力。當然在有規制效力的情況下,我不主張刑法一定要堅持二元規制,應該允許有例外。
“刑事法領域看待民刑關系,很大程度是立場的問題”
孫萬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院長
民法典時代的罪與罰也好,民刑交叉也好,民刑界定也好,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命題,既包括對刑事法益、民法法益該怎么理解的問題,也包括對規范性本身該怎么理解的問題,當然還包括解釋觀念的問題、程序方面的問題。
刑事法領域,我們怎么來看待民刑關系?很大程度上就是立場的問題。各方專家學者各取所需,表現出了從自身角度出發看待問題的合理性。
《大禹謨》的一段話:“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某種意義上,我們如果堆集大量的案例以后,你會發現它就是“罪疑惟輕”。中國古代,法官適用“罪疑惟輕”的案例是非常多的。
很多學者講到刑法是最后的保障法,最后一個關口,最后一個手段,最后一個結果,但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形式性的概念,并不能因為刑法是保障法,就說只有建立在前置性違法的基礎上,刑法才能介入。刑法的獨立性表現在哪里?輕犯的法益到底是什么?當一個行為不僅僅是對被害人個人的侵犯,還具有非常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刑法要評判的不再是被害人和被告人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對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侵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說故意殺人罪到底是因為民事侵權侵犯他人的生命而構成的犯罪,還是它天生就是犯罪?我們刑法學者非常困難,也非常痛苦,因為我們時時刻刻涉及前置法的問題。
今天我們的標題是“民法典時代的罪與罰”,這個名字起得不僅好,而且很有文藝范兒。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說,叫《霍亂時期的愛情》,是講一對戀人50年的時間里,經過了戰爭、瘟疫,然后共同維護愛情的尊嚴。同樣,今天我們在這個主題下進行探討,我覺得非常貼切。希望在座的專家學者們也能用自己人生的50年時間守望、保護我們的司法公正。
編輯:鄭賓? 39375816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