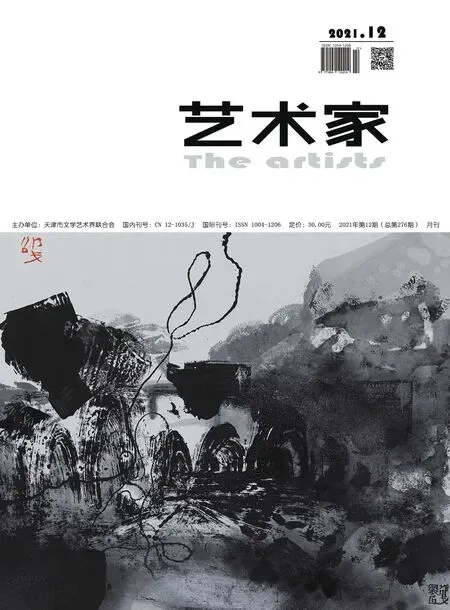理想與現實
——古希臘雕塑與中國古典雕塑的發式博弈
□曾 光 肇慶學院美術學院
古典雕塑作為中西方藝術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以其獨特的技法語言和立體的呈現方式,讓人通過視覺和觸覺的雙重體驗來實現對美的鑒賞。西方古典美標準的建立,離不開古希臘藝術對美的探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應為雕塑;而中國古典美的發展,雖歷經秦漢、魏晉、唐宋、明清等時代變革,卻呈現出少有的一致性,其鮮明的古典特征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時期。
古典雕塑因其跨越時空的藝術美和文化影響,歷久彌新,常常作為美的典范出現在現代生活中,或為家中裝飾,或為課堂擺件,或為商業點綴。在學術界,對其研究也較為充分,有比較研究、審美研究、主題研究等。但是,關于古典雕塑發式的討論卻寥寥無幾,涉獵的作品也無非是最著名的幾件,如古希臘的《斷臂維納斯》《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拉奧孔》《擲鐵餅者》《荷矛者》,中國的唐代發式、少數民族發式等。
一、中西古典雕塑男像發式比較
發式作為一個人形象的重要裝飾,包含著政治、經濟、歷史、民族、宗教等多元因素,正如法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和史學家伊波利特·阿道爾夫·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藝術哲學》中所說,文學藝術與種族、環境、時代這三個要素緊密相關。從這一意義上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之形象的發式,超越了日常裝束的功能,有時是滿足實用主義的需要,有時是時尚的風向標,有時是某種權力、身份的象征。
古希臘是一個海洋國家,和煦的海風吹拂著這塊土地上的萬事萬物。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人們,一邊承受著土地的貧瘠和物質的匱乏,一邊享受著高度發達的奴隸制帶來的成果,如手工藝、航海、對外貿易等。因其平等、自由的社會氛圍,人們很早就關注到個體自身,并在藝術上有著非常直接的表現。他們生活簡樸,性情奔放,特別重視精神生活,因此也非常樂意打造各種各樣的發式造型。早期雕塑男像由于受古埃及的程式化裝飾影響,多為長發,配以頭巾,顯得莊重;后期由于戰爭和運動的催化,為方便打理又顯優雅,則變成光頭、小平頭或卷曲的短發。

表1 古希臘雕塑男像經典發式舉例
此外,為使崇尚體育競技和健康體魄的古希臘男人看起來精神抖擻,神采奕奕,男性短短的卷發上,常常束一根帶子,這根帶子后來成為現代頭箍的雛形。當然,上戰場的男人還需戴上帽子或頭盔保護頭部,這時頭發被遮蓋和擠壓,只露出耳朵邊的兩綹和后腦勺,發式之美基本就可以忽略了。
古希臘孩子的發式,除了簡約的小平頭外,還常常將前額一綹扎起,擋住“腦門”,祈愿健康,體現出父母希望孩子茁壯成長的美好愿望。
古希臘雕塑男像發式,從古風時期到古典時期再到希臘化時期,每一階段都變化鮮明,時而嚴謹,時而活潑,時而平實,于淳樸中帶著小清新,展現了古希臘人在發式設計方面的不同追求。而中國古典雕塑男像發式的最佳代表,莫過于與古希臘年代接近的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發式。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秦始皇陵兵馬俑軍陣,有著鮮明的“個體寫實,整體寫意”特征,充分體現了秦代高超的雕塑技藝。兵馬俑依照人馬的真實比例塑造,根據兵種的不同分為步兵俑、騎兵俑、車兵俑、弓弩手、將軍俑等,面部神態、服式、發型各不相同,塑模并用,通體彩繪,栩栩如生,是中國古代雕塑逼真寫實的范例。

圖1 中國秦俑男像發式舉例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秦俑發式是區別步、騎、車三大兵種和身份、地位高低的顯要標志。由于騎兵、車兵人數較少,隊伍穩定,因此發式相對一致。而步兵的發式變化則非常復雜,這與其來源地域廣闊、民俗不同、人數眾多、地位不一有關。軍陣中,“將軍俑的發式”為從中間分開,前額兩綹翹起,頭戴鴿冠,彰顯其高級指揮官的威嚴;“跪射俑”的發式為“發直上”式樣,且受尚右卑左的思想影響,發髻偏左的武士俑身份要低于發髻偏右的武士俑身份,而他們的地位又都高于發髻偏后的跟坐俑。同時,其所佩戴的發飾也是身份高低的象征。頭部不加飾物,發髻裸露的俑,地位最為低下。頭戴軟帽的士卒,地位當高于裸髻者,少數頭戴長冠者,似為中下級軍吏。
總而言之,秦俑的發式以高髻為主,綰結方法多樣,整理仔細,脈絡清晰,發式穩固,干凈利落,便于長時間保持,是秦代軍事制度和審美風尚相互作用的結果。表現技法上趨于寫實,與軍隊的著裝、佩飾共同展現著嚴肅、有序的軍隊陣容,是秦王朝統一六國大氣魄的反映。
兩相對比,不難發現,古希臘雕塑發式以“審美”為出發點,向理想美的方向行進;中國秦俑發式則以“標榜身份地位”為目的,雖人物面部表情各異,但仍舊淹沒了軍士的個性,使之服從于“軍陣”大局。此二者功能不同,造型自然也有所不同。
二、中西古典雕塑女像發式比較
在古希臘的大部分城邦,女性基本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既不能參與城邦政治活動,也不能進行政治決策,更無須奔赴戰場,她們很少出入公共場所,社會地位比男人低,在家的自由時間比男人長。因此,古希臘雕塑女像發式相比古希臘雕塑男像發式更加豐富變化。其美麗、多變、有序的頭發管理,在某種程度上,展現出整個古希臘藝術自然、唯美、簡潔的風格。
古希臘女性沒有戴帽子的習慣,因此,她們格外關心發型的變化,每天在發型上花費大量時間,甚至培訓專門的奴隸來負責發型創新,通過扭、扎、卷、捆等辦法,創造出各式各樣的花哨發型,不僅增添了古希臘女性的綽約風姿,還反映出她們創造美的智慧與能力。
古希臘女性喜歡把長發盤成發髻,用骨質發針、螺旋金線或紫羅蘭花冠作為裝飾。少數貴婦的發式則更加高雅奢侈,尤其是扎成蝴蝶結樣式的發型,正面看優雅嫵媚,背后看兩條分開梳的小辮子活潑可愛,讓人聯想到發型隨風而動的飄逸效果,浪漫唯美。古希臘著名雕塑《斷臂維納斯》以及《美惠三女神》中的光輝女神、激勵女神和歡樂女神都是這款發型。不難發現,女神發式映射的是人的生活,藝術家則根據古希臘女性的發型創造了女神的發型,而古希臘女性也像女神一樣愛美,在現實生活中向女神致敬。這種人神合一的現象,蘊含著古希臘人原始的敬神情懷,使發型成為信仰的象征。
古希臘女性常常會把短發梳得紋絲不亂,或是齊劉海,或是中間分叉,兩邊頭發掠向耳后,有時梳起密密小小的波浪卷,綴以發帶或珍珠裝飾,也是典雅清爽,美不勝收。
古希臘女性還崇尚金發,因此,也會染發或戴假發,這一習俗直接影響了后世幾百年。例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一畫中,維納斯就擁有一頭長長的大波浪卷發,彎曲自然,金黃柔和,把從海水中誕生的維納斯烘托得美麗優雅,魅力無窮。而巴洛克、洛可可時代,法國的王公貴族也鐘情于金色假發卷,將其作為發式之美的最高追求。甚至,現代女性也喜歡將頭發染成金色,以提升其高貴氣質。由此可見,古希臘金發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表2 古希臘雕塑女像經典發式舉例
古希臘女性發式的美麗彌補了其服裝造型的樸素,無論長發、短發、金發、黑發,古希臘女性都認真對待,將頭發這一平淡無奇的人體構成部分,演繹成了一曲美的頌歌,并借此搭配古希臘理想化的臉型,成為古典美的最高詮釋。
中國古典雕塑的女像發式,最為典型的當屬唐三彩仕女像發式。從初唐的螺髻(形似螺殼,有單雙之分)、半翻髻(單片或雙片刀型,豎于頭頂),到盛唐的雙環望仙髻(雙環發式)、倭墮髻(發髻朝一邊傾斜墜落)、回鶻髻(回鶻椎狀發髻),再到晚唐的拋家髻(高聳似拋)、墜馬髻(集發于頂再綰髻下搭),萬變不離其宗,始終以髻為中心,配以鬢發修飾,雖然展示出一定的民族特點和婚嫁之趣,但同時,并無古希臘女性發式的豐富變化。
三、中西古典雕塑發式差異的成因及深遠影響
古希臘雕塑的發式之美,彰顯的是古希臘人的發式之美,那么,是哪些原因催生了這么美的男女發型呢?德國著名歷史哲學家克羅齊在其名作《歷史學的理論與歷史》中曾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古希臘雕塑的發式之美必然是那片地域、那個時代、那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產物,其風格由最初的自然質樸逐漸轉向華麗奢靡,見證了不同時期的風尚和情境變化。

圖2 中國唐代雕塑女像發式舉例
(一)民族特點原因(種族)
古希臘是海洋民族,人們充滿想象力和熱情,一代一代積淀著對美的欣賞、實踐與開拓的興趣,建立起美的標準,不但倡導人體美,而且積極開創發式美,并最終形成了古希臘古典美學體系。而古代中國是農耕文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規律,使人們養成了務實的性格,表現在發式上即為實用和區分等級。
(二)自然環境原因(環境)
海洋環境的開放廣博,氣候的溫暖干燥,服飾鞋帽的簡約樸素,使古希臘人熱衷于在可變性最強的頭發上大做文章,創造了豐富的男女發式,彌補了物質貧乏帶來的裝飾缺憾。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藝術生活化和生活藝術化,把“人”往“神”的方向提升,并美化它、仰望它。中國內地的田園風光,使中國人養成了熱愛現實生活的習慣,在藝術表現上,將“神”變成“人”,深深地打上世俗的烙印。
(三)社會歷史原因(時代)
貿易和航海業培養出希臘人機智靈活的應變能力和敢于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氣,城邦國家的奴隸制民主政治重視創造力,由此使人們有了發揮的機會和空間。正如古希臘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所說:“我們沒有忘記使疲勞的精神獲得休息,我們的生活方式是優雅的”“我們是愛美的人”。確實,假如沒有他關心自由民,善待奴隸,積極提倡文化藝術,雅典就不可能成為全希臘的藝術和教育中心,古希臘藝術也不可能進入全盛的古典時期,發式之美也就不可能有如此突出的表現,不可能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成為古希臘文明中具有高辨識度的視覺符號和傳播載體,印證著古希臘奴隸制文明的高度發達。而古代中國封建社會的君主專政制度,強調王權至上、尊卑有序的等級觀念,民眾自由發揮的空間有限,發式則具有較強的象征意義。
由此可見,中西古典雕塑發式的演變規律,驗證了丹納藝術觀的正確性:任何藝術形式都將受到種族、環境和時代的深刻影響。正因為古希臘人很早就從生活出發,肯定現實,贊美人性,賦予人的精神以崇高的理想,把“人”往“神”的方向去打造,才創造出許多美的范式,讓后人對反映理想美的優雅發式充滿“溫情與敬意”。而古代中國則注重王權,各種藝術大多服務于王權,發式創新亦是如此,大都展現出現實之美。本文之所以重申古典雕塑的發式之美,不僅在于梳理、總結中西方藝術差異,更在于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蘊,使藝術史的連續性得以彰顯,讓更多的雕塑愛好者站在傳統的基石上創新雕塑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