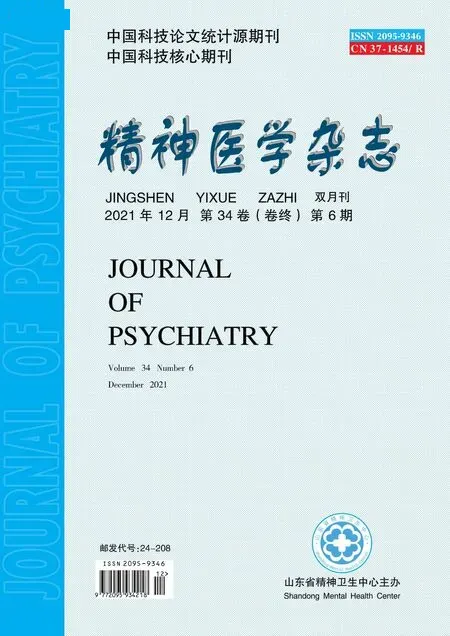綜合醫院精神科門診患者焦慮癥狀的網絡分析*
馬竹靜 任 壘 李逢戰 梁 偉 郭 力 張欽濤 苑會羚 張 良 陳 晨 楊 群
焦慮是日常生活中一種常見的情緒狀態,多種原因都可能引發焦慮。羅洛?梅認為焦慮是當人感到自己某種重要的價值受到威脅時產生的擴散性的不安[1]。主要表現為情緒不佳,同時可能伴隨有軀體不適,如心跳加速、呼吸加快、過度換氣等[2]。焦慮情緒具有可持續性,會給個人帶來明顯的主觀痛苦和功能受損。長期的焦慮如果一直不能得到解決就容易發展成焦慮癥、恐怖癥、強迫癥等精神疾病,而這些疾病也會引發不同程度的焦慮癥狀[3]。并且有研究表明若精神疾病在急性期治療后仍殘留有焦慮癥狀,就容易轉化為慢性和復發性疾病[4,5]。許多國家和組織還將焦慮列為自殺的重要危險因素(如美國自殺協會,2015;國家自殺預防生命線,2015)。因此,對焦慮癥狀進行早期關注和干預是十分重要的。
近年來,網絡分析模型被廣泛應用于精神病理學和心理學研究。與潛在變量模型不同,網絡模型不把潛變量作為觀測變量的共同因素,而是將觀測變量作為指標,由數據驅動從而對復雜變量間的關系進行分析[6,7]。在網絡中,變量為網絡的節點,邊代表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關聯。此外,與簡單的相關方法相比,網絡方法可以通過計算中心性指數來量化每個節點在網絡中的重要性程度。即高中心性的節點被激活時,更有可能通過連接更多的邊將激活傳播到整個網絡[8]。網絡分析為理解人類心理現象和精神障礙診斷中不同癥狀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近年來已廣泛應用于人格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精神病學等領域[9~12]。
精神科門診患者平均就醫診斷時間長,多屬于長期性焦慮,因此本研究以精神科門診患者中焦慮程度較高的患者為研究對象,通過計算加權網絡和預期影響探索門診患者焦慮癥狀網絡的特征和核心癥狀,以期為精神科門診患者焦慮的預防和干預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研究取樣于2014年10月23日~2019年5月17日就診于西北地區某綜合醫院精神科門診的25 574例患者。納入標準:年齡18~85歲;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評分≥60分(SAS中國焦慮評定的分界值為50分,分數越高,焦慮傾向越明顯。其中60~69分為中度;69分以上為重度,本研究納入的患者主要是中、重度焦慮傾向的患者)。排除標準:數據缺失、數據不完整或存在極端數據。經篩選后,共計納入樣本數8 748例。本研究對該樣本數據進行了分析。該樣本中患者平均年齡(37.47±16.94)歲。男性占36.19%(3 166例),本科及以上學歷占25.24%(2 208例),未婚占28.20%(2 467例)。本研究已通過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審批號:KY20202063-F-2號)。
1.2 方法
1.2.1 評定工具
1.2.1.1 一般情況調查問卷 該問卷用于收集被試的一般狀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等基本信息。
1.2.1.2 SAS Zung于1971年編制的用于評定焦慮狀態的自評量表。共由20個題目組成, 對每一題目被試依最近1周的主觀感覺按1~4評分。其標準為:1-沒有或很少時間;2-小部分時間;3-相當多時間;4-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我國焦慮評定的分界值為50分,分數越高,焦慮傾向越明顯。
1.2.2 網絡分析 使用圖形高斯模型(Graphical Gaussian Model, GGM)對數據進行擬合。GGM是無向網絡,邊緣表示兩個節點之間的相關關系,即在對網絡中其他節點進行統計控制后,兩個節點之間的凈相關關系[13]。通過使用圖形化套索算法得到一個更穩定且易于解釋的正則化偏相關網絡[14]。此外,將gamma設置為0.5來更好地平衡發現網絡真實邊的敏感性和特異性[15]。根據FR算法布局顯示網絡,具有較強連接的節點位于靠近網絡中心的位置,具有較弱連接的節點位于靠近網絡外圍的位置[16]。網絡中藍線表示正相關,紅線表示負相關。邊緣越厚,兩個節點之間的關聯越大,邊緣越薄,兩個節點之間的關聯越小。網絡使用R軟件qgraph包構建并可視化。
使用R軟件 qgraph包計算每個節點的預期影響。與傳統的中心性指標(例如接近中心性、介數中心性)相比,預期影響指標更適合同時具有正邊緣和負邊緣的網絡[17]。給定節點的預期影響是連接該節點的所有邊的權重之和(而不是絕對值之和)。節點的預期影響越大,該節點與網絡中其他節點的關系越緊密,其在網絡中的重要性程度越高。
1.2.3 統計學方法 使用R軟件bootnet包評估網絡的準確性和穩定性[18]。首先,使用非參數自舉法(1 000個自舉樣本)計算95%置信區間,以評估邊權值的準確性。其次,使用樣本下降自舉法計算相關穩定性系數以評估節點預期影響的穩定性。先前的研究表明,相對穩定性系數最好應高于0.50且不低于0.25[18]。最后,通過自舉法對邊權值和節點預期影響進行差異性檢驗來評估兩個邊權值或兩個節點預期影響之間差異是否有統計學意義(α = 0.05)。
2 結果
2.1 SAS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結果顯示,8 748例患者SAS總分為(68.76±7.58)分,男性總分為(68.23±7.23)分,女性總分為(69.07± 7.75)分,各項目評分和預期影響指數見表1。

表1 精神科門診患者SAS各項目評分的描述性統計
2.2 網絡分析結果
2.2.1 焦慮癥狀網絡 圖1描繪了精神科門診患者的焦慮癥狀網絡。網絡顯示,癥狀“我因為一陣陣頭暈而苦惱(A11)”和“我有暈倒發作,或覺得要暈倒似的(A12)”、“我手腳發抖打顫(A6)”和“我的手腳麻木和刺痛(A14)”、“我容易心里煩亂或覺得驚恐(A3)”和“我覺得我可能將要發瘋(A4)”以及癥狀“我因為頭痛、頸痛和背痛而苦惱(A7)”和“我因為一陣陣頭暈而苦惱(A11)”之間具有最強的邊連接,正則化偏相關系數分別為0.36、0.30、0.29、0.29。

注:藍線代表正相關;紅線代表負相關。邊越粗,兩個節點之間的關聯越大;邊越細,兩個節點之間的關聯越小。字母代表的項目如表1
2.2.2 節點預期影響 圖 2 顯示了SAS各癥狀的預期影響(Z分數)。根據中心性指數,癥狀“我容易心里煩亂或覺得驚恐(A3)”預期影響最高,其次是“我因為一陣陣頭暈而苦惱(A11)”,第三是“我覺得比平時容易緊張和著急(A1)”,預期影響最低的三個癥狀是“我的手腳常常是干燥溫暖的(A17)”、“我時常臉紅發熱(A18)”和“我的小便次數頻繁(A16)”。

注:字母代表的項目如表1
2.2.3 準確性和穩定性分析結果 圖3顯示了自助法得到的邊權值的準確性。黑線代表使用自助法評估的平均邊權值,紅線代表本研究樣本的邊權值,灰色區域表示95%置信區間。結果表明邊權值的評估是相對準確的。圖4顯示了預期影響的穩定性系數。本研究中,癥狀預期影響的相關穩定性系數為0.75,表明預期影響具有足夠的穩定性。

注:紅線代表原始樣本強度中心性與子樣本之間的平均關系

圖4 癥狀預期影響的穩定性
2.2.4 邊權值和節點預期影響的差異性檢驗 圖5展示了邊權值的差異性檢驗,可以看出,大部分邊權值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圖6展示了節點預期影響的差異性檢驗,可以看出,大部分節點預期影響之間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注:灰框代表兩個對應邊的邊權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黑色框代表兩個對應邊的邊權值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角線的彩色框代表變量網絡(圖1)中邊權值的顏色

注:灰框代表兩個對應節點的預期影響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黑色框代表兩個對應節點的預期影響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角線上的白色框中的數字代表節點的預期影響(原始值)。字母代表的項目如表1
3 討論
焦慮癥狀是精神科門診患者中最為常見的癥狀之一。目前,針對不同焦慮癥狀的研究已有很多,然而關于焦慮癥狀之間關系的研究很少。本研究采用網絡分析法對門診患者焦慮癥狀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究。網絡結構和預期影響結果可以提示哪些癥狀聯系最為密切以及哪些癥狀是門診患者焦慮網絡中的核心癥狀。這些結果可能對門診患者焦慮癥狀的預防和干預有一定意義。
網絡結果顯示癥狀“我因為一陣陣頭暈而苦惱(A11)”與癥狀“我有暈倒發作,或覺得要暈倒似的(A12)”之間具有最強的邊連接。這與焦慮癥狀的身心交互模型一致[19]。暈倒感或暈倒發作感是一種內感受性,當這種感覺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可能出現頭暈,反之,經常被頭暈所累也可能導致更強烈的暈倒感。這說明通過增加精神科門診患者對暈倒的感受性訓練可能有助于緩解患者的頭暈癥狀。癥狀“我手腳發抖打顫(A6)”與“我的手腳麻木和刺痛(A14)”和“我因為頭痛、頸痛和背痛而苦惱(A7)”與“我因為一陣陣頭暈而苦惱(A11)”也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這從數據驅動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焦慮癥狀中軀體癥狀往往是交互作用的(例如,失眠可引起頭痛,同時頭痛也能引起失眠)[20]。另外,本研究發現癥狀“我容易心里煩亂或覺得驚恐(A3)”和“我覺得我可能將要發瘋(A4)”之間也存在緊密相關。多數患者在就診精神科前往往到處檢查,當檢查結果顯示其無異常而患者身上的不適依舊存在時,患者的心理負擔會加大,這種不確定感會使患者更加煩亂和驚恐,當煩亂和驚恐加劇時就可能出現失控發瘋感。
中心性分析可以確定哪些癥狀在網絡中更為重要。預期影響結果表明精神性焦慮癥狀“我容易心里煩亂或覺得驚恐(A3)”是門診患者焦慮網絡中的核心癥狀,這從統計上表明該癥狀與其他癥狀有著最為廣泛緊密的聯系,也就是該癥狀的激活更有可能通過連接其他癥狀的邊將激活傳播到整個焦慮癥狀網絡。以往研究亦表明綜合醫院門診焦慮患者,主訴的情緒和精神癥狀更為突出[21]。因此,針對癥狀“我容易心里煩亂或覺得驚恐(A3)”的干預可能要比針對其他癥狀的干預能更有效降低焦慮癥狀的整體水平。另外,“煩亂與驚恐”的中心性程度高很大程度上與患者對疾病的擔憂和不確定性有關。一項針對此次疫情的研究發現,當人們在面臨不可控和不確定因素時,往往會產生煩亂或者驚恐的情緒反應,這種情緒反應與廣泛的心理問題相關,尤其是焦慮[22]。研究還發現癥狀 “我的手腳常常是干燥溫暖的(A17)”、“我時常臉紅發熱(A18)”和“我的小便次數頻繁(A16)”在網絡中的中心性程度最低,這表明這三個軀體性癥狀可能對整個焦慮癥狀網絡的影響很弱小,因此,以控制這些癥狀為重點的治療可能對門診患者焦慮的整體癥狀不能產生很大的影響。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用于構建門診患者焦慮癥狀網絡結構的橫斷面數據無法揭示癥狀隨時間推移如何出現,不能了解癥狀間的因果關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縱向追蹤以探究癥狀間的時間因果關系。其次,本研究中的網絡結構特定于門診患者,其中部分參與者并不完全符合精神障礙的診斷標準,因此結果不能推廣到臨床精神病學人群。 不過,雖然不同疾病之間焦慮的內容和觸發因素存在差異,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精神障礙的焦慮癥狀具有相似的核心潛在特征[23,24]。最后,本研究評估的是門診患者群體水平的焦慮癥狀網絡結構,這些結構可能與個體水平的焦慮癥狀網絡結構不同。
盡管存在上述局限,本研究的優勢在于將精神心理癥狀概念化為因果系統,為傳統精神障礙的分類和維度模型提供了一種補充方法。此外,本研究也是為數不多的使用網絡方法探索門診患者焦慮癥狀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之一,這為理解焦慮癥狀之間的作用關系以及特定癥狀的臨床意義提供了新的見解。具體來說,本研究發現癥狀“我容易心里煩亂或覺得驚恐(A3)”是焦慮癥狀網絡中最核心的癥狀。這提示,以該癥狀為核心靶點可能會更大程度上降低精神科門診患者整體焦慮癥狀的嚴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