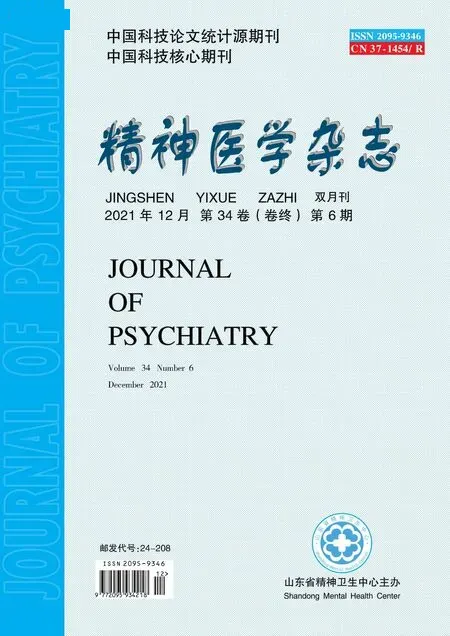焦慮性抑郁癥臨床研究進展*
趙冰驄 費宇彤 石 川 楊昕婧 姜會梨 圖 婭
抑郁障礙和焦慮障礙是臨床最為常見的兩類情感障礙。最新精神障礙調查顯示,我國抑郁障礙和焦慮障礙的終生患病率分別為6.8%和7.6%,12個月患病率分別為3.6%和5.0%[1]。薈萃分析發現所有類型的焦慮癥狀或焦慮障礙均能預測隨后的抑郁癥狀或抑郁障礙,反之亦然,提示抑郁和焦慮互為危險因素[2]。顯而易見,評估抑郁患者的焦慮程度具有重要意義。基于焦慮與抑郁的緊密聯系,學界提出了焦慮性抑郁癥(Anxious Depression)的概念,并認為其屬于一種嚴重的臨床抑郁亞型[3,4]。本文主要就焦慮性抑郁癥在診斷、患病率、臨床表現、神經生物學特征及臨床治療方面的主要發現和最新進展進行全面綜述。
1 診斷
此前研究者主要采用維度標準和綜合征性標準診斷焦慮性抑郁癥[3]。維度標準是指在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ICD-10)抑郁發作或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DSM-Ⅳ)重性抑郁障礙(MDD)診斷基礎上伴發高水平焦慮癥狀,如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焦慮/軀體化因子≥7分。綜合征性標準指在MDD診斷基礎上共病至少一種焦慮障礙。與后者相比,采用維度標準診斷焦慮性抑郁癥具有省時易行的優勢[4,5]。由于許多伴有顯著焦慮癥狀的抑郁患者未能完全達到焦慮障礙的閾值而無法被綜合征性標準識別,維度標準被認為更加貼合臨床實際[6]。
2013年發布的DSM-5手冊盡管未能將焦慮性抑郁癥明確歸屬于一類診斷學亞型,但提出了伴焦慮痛苦標注(anxious distress specifier),即在MDD或心境惡劣的大部分時間內存在以下至少2項癥狀:(1)感覺激動或緊張;(2)感覺異常的坐立不安;(3)因擔心而難以集中注意力;(4)害怕可能發生可怕的事情;(5)感覺可能失去自我控制。盡管仍有部分研究者對該標注的有效性持懷疑態度,這一臨床工具的推行勢必將促進學界對于焦慮性抑郁癥領域的深入認知。
從早期的維度和綜合征性標準到DSM-5手冊伴焦慮痛苦標注的提出,反映了臨床和科研工作者對于焦慮抑郁共病現象認知日趨完善的過程。然而,由于精神疾病之間存在廣泛而復雜的交織現象,基于患者臨床癥狀定義和分類的新版診斷標準仍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從長遠來看,建立以遺傳學和神經解剖學為主的、以神經生物學為基礎的框架將可能為焦慮性抑郁癥的診斷和治療帶來新的突破。
2 患病率
迄今為止最大型的前瞻性MDD臨床研究—抑郁癥序貫治療項目(STAR*D)采用維度標準發現美國MDD患者(n=2 876)中焦慮性抑郁癥患病率為53%[7]。我國MDD患者(n=375)中維度焦慮性抑郁癥患病率為70%[5]。采用綜合征性標準的研究中,世界衛生組織跨國精神健康調研(n=74 045)顯示,46%的終生MDD患者共病至少一種終生焦慮障礙,在12個月MDD患者中,52%共病終生焦慮障礙,42%共病12個月焦慮障礙[8]。當MDD共病不同種類焦慮障礙時患病率也有所差異,美國酒精和相關疾病流行病學調查III(NESARC-III)顯示MDD患者中最為常見的共病焦慮障礙是廣泛性焦慮,其終生和12個月患病率分別達到20.5%和19.9%,居于第二、三位的是創傷后應激障礙和特殊恐怖癥[9]。目前應用伴焦慮痛苦標注的流行病學研究仍較為有限。美加兩國聯合開展的國際情緒障礙協作項目發現MDD患者(n=830)中有56%達到了伴焦慮痛苦的標準[10]。NESARC-III研究中,美國終生MDD患者(n=7 432)和12個月MDD患者(n=448)中伴焦慮痛苦的比例分別達到75%和70%[9]。
由于診斷方法、調查人群和納排標準等異質性,不同研究中焦慮性抑郁癥的患病率波動在42%~75%之間,均處于較高水平,提示其確為一種不容忽視的重大抑郁類型。因此,有必要對焦慮性抑郁癥的臨床和神經生物學表現,以及不同干預措施的臨床療效開展深入研究。
3 臨床表現
采用不同診斷標準的研究中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特征也不盡相同,但與非焦慮性抑郁癥(Nonanxious Depression)患者相比均具有顯著差異。STAR*D項目較為全面地對比了焦慮性抑郁癥和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在臨床表現上的差異,發現前者以女性居多,通常年齡更大、抑郁程度更高、生活質量和受教育程度更低,更可能產生自殺想法、嘗試自殺行為、進入初級保健機構、出現憂郁或非典型癥狀特征,也更可能達到焦慮障礙的閾值[4,7,11]。此外,研究者還發現維度焦慮性抑郁癥患者通常具有更好的精神運動功能和認知功能,更明顯的疼痛和功能障礙以及更差的工作和社交適應能力[12~15]。病程方面,維度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當前抑郁發作的持續時間更長,但起病時間和抑郁發作次數與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相似[6]。研究者采用綜合征性標準發現,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的精神運動功能更好,抑郁癥狀、角色損害、傷害回避和自殺想法更嚴重,工作記憶、認知靈活性和信息處理速度更差,其雙親通常患有更加廣泛的情感障礙[8,12,16]。此外,共病不同焦慮障礙種類和數量的MDD患者臨床表現也有所差異,如共病社交恐懼癥和廣場恐懼癥分別多見于青年和門診MDD患者,共病廣泛性焦慮者抑郁癥狀更加嚴重[17]。共病焦慮障礙越多,患者預后越差,并且抑郁、焦慮和軀體癥狀的嚴重程度直至發病10年后仍顯著高于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18]。采用伴焦慮痛苦標注的研究則發現焦慮性抑郁癥患者住院次數和自殺意念更多,抑郁癥狀、認知損害和職場障礙更嚴重,生活質量更低[10]。
4 神經生物學特征
近年來,研究者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焦慮性抑郁癥有別于非焦慮性抑郁癥的神經生物學特征,包括更嚴重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功能紊亂和免疫激活,以及腦結構和功能異常改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神經生物學標記物將有助于推動焦慮性抑郁癥診療模式的革新。
HPA軸功能異常是MDD患者的重要特征。Menke A等[19]發現與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相比,維度焦慮性抑郁癥患者靜脈血糖皮質激素受體誘導的FKBP5 mRNA表達增強,皮質醇水平降低。在精神疾病領域,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近年來也日益受到關注。Baek JH等[20]發現與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相比,維度焦慮性抑郁癥患者靜脈血嗜堿性粒細胞計數顯著減少,分葉核嗜中性粒細胞顯著增多。Shim IH等[21]采用伴焦慮痛苦標注發現中-重度和重度焦慮性抑郁癥患者比輕-中度患者的C反應蛋白和單核細胞水平更高。Gaspersz R等[22]發現焦慮痛苦與先天細胞因子生成能力增加有關。Kircanski K等[23]發現心率變異性可作為預測維度焦慮性抑郁癥患者抗抑郁藥療效的生物標志物,心率變異性較高的患者預后較好。
神經影像學方面,研究者主要通過磁共振成像(MRI)技術從多角度分析了焦慮性抑郁癥患者與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及健康對照者腦結構和功能的異同。然而,受限于有限的樣本量、研究數量和患者異質性,現有結果仍缺乏較好的一致性。結構MRI研究相對共性的發現包括焦慮性抑郁癥患者前額區域灰質體積減小[24]、前額和顳部區域皮層厚度變薄[25]。功能MRI研究主要發現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皮層-邊緣網絡連接模式發生改變[26,27]。
5 臨床治療
盡管有研究發現焦慮性抑郁癥和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治療結局相似[14],更多研究提示焦慮性抑郁癥群體的療效和安全性結局更差[5~7],這可能源于其獨特的神經生物學特征,并且不同的診斷標準和患者特征也會影響治療結局。
目前焦慮性抑郁癥的主流療法是藥物治療。第二代抗抑郁藥中,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以及5-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NRIs)常被用于焦慮性抑郁癥的一線治療。然而,在STAR*D項目中接受西酞普蘭治療的MDD患者,維度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的療效和安全性均比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更差,痊愈率僅為22%[7]。有研究認為盡管SSRIs類、SNRIs類和三環類抗抑郁藥在治療起始階段對維度焦慮性抑郁癥均有療效,但無法維持應答或痊愈,且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發生的不良反應風險更高[28]。新型藥物治療方案中,Wang C等[29]發現重復靜注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拮抗劑氯胺酮對維度焦慮性抑郁癥患者效果顯著,然而作為K粉的主要成分,氯胺酮的安全性和遠期療效尚需驗證。Thase ME等[30]發現首個吲哚烷基胺類抗抑郁藥維拉唑酮治療焦慮性抑郁癥有效。聯合用藥研究發現,非典型抗精神病藥喹硫平、阿立哌唑、依匹哌唑、齊拉西酮作為抗抑郁藥的輔助用藥對焦慮性抑郁癥均有療效[31~34],臨床治療中應密切監測聯合用藥伴隨的附加不良反應。此外,苯二氮類藥物與SSRIs/SNRIs類藥物聯用有助于提高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的應答速度和總應答率[35],但長期使用時應警惕藥物不良反應和濫用等風險。
非藥物療法中,心理治療是一類常用的一線抗抑郁療法。在STAR*D項目第一階段中對于西酞普蘭無應答或部分應答的焦慮性抑郁癥患者在第二階段換用或聯用認知療法后,痊愈率僅為14%~21%,提示初始階段抗抑郁藥療效不佳的患者后續接受心理治療的效果也不理想[36]。重復經顱磁刺激(rTMS)療法此前也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用于MDD的臨床治療,Diefenbach GJ等[37]發現rTMS能夠顯著改善難治性MDD患者的抑郁和焦慮癥狀,并且焦慮性抑郁癥和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應答程度相仿。近年來,中醫針刺療法逐漸走向國際,Zhao B等[38]發現電針聯合SSRIs類藥物對于MDD患者焦慮癥狀的改善顯著優于單純SSRIs類藥物,療效與安全性的雙重優勢使得針藥聯合療法有望成為焦慮性抑郁癥患者又一治療選擇。
6 小結與展望
綜上,焦慮性抑郁癥患病率高,具有比非焦慮性抑郁癥更加復雜的臨床表現,通常病情更重、病程更長、生存質量更低、自殺風險更高。焦慮性抑郁癥患者的神經生物學特征也與非焦慮性抑郁癥患者有所差異,主要表現為更嚴重的HPA軸功能紊亂和免疫激活,以及情緒調節相關腦區結構和功能連接模式異常改變。治療方面,焦慮性抑郁癥患者往往表現出更差的治療結局,二代抗抑郁藥和心理治療療效均不理想,新型藥物和聯合療法等手段表現出較好的臨床療效。
盡管焦慮性抑郁癥已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嚴重抑郁類型,該領域的臨床研究仍存在明顯的局限性。首先,焦慮性抑郁癥診斷的多樣性使得不同研究間結果的相互比較、合并極為困難。第二,焦慮性抑郁癥的神經生物學研究仍較為有限,特別是缺乏對潛在療法的效應機制探索。第三,現有的焦慮性抑郁癥治療性研究多為事后分析,且樣本量普遍較小,無法證實干預措施與治療結局之間的因果關系。
有鑒于此,未來臨床實踐當中有必要采用維度標準或伴焦慮痛苦標注開展早期篩查,評估MDD患者的焦慮程度,并通過新型藥物或聯合治療等手段提高臨床療效,同時密切監測安全性風險。科研方面,未來研究應盡可能采用統一診斷標準減少異質性,通過分子生物學和神經影像學技術探尋具有臨床價值的生物標志物并將其轉化為實用可行的診斷指標和治療靶點,開展具有充足樣本量的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揭示潛在療法的治療效果和安全性,以期為這一重大抑郁類型提供更多治療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