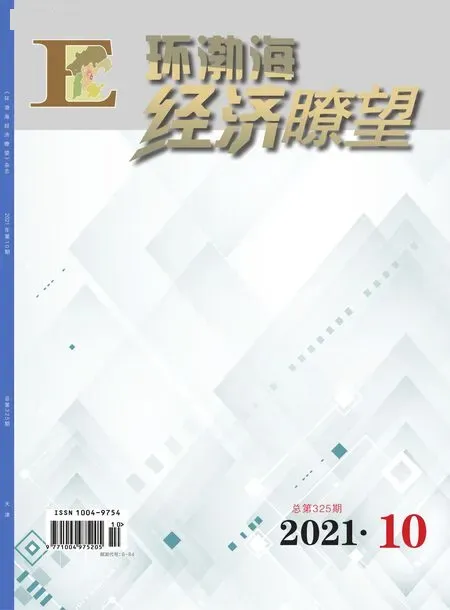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特征及經驗借鑒
韓 碩 徐成龍
一、前言
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和發展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作為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已成為拉動經濟的新動力、新方向。生產性服務業具有高度的產業相關性和較強的跨界服務性,與產業結構相比,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及其空間布局更具現實意義。
2014 年,國家在《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26 號)中提出,“要堅持集聚發展......因地制宜引導生產性服務業在中心城市、制造業集中區域、現代農業產業基地以及有條件的城鎮等區域集聚,實現規模效益和特色發展”。這將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這一舉措納入了國家戰略的范圍中。
二、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現狀
按照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生產性服務業具體包括“交通倉儲郵電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貿易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六大行業。2019 年,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以批發零售貿易業為主,占總增加值的43.72%,金融業和交通倉儲郵電業分別為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的第二大行業和第三大行業,其增加值占比分別為18.74%和16.31%,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行業均未超過10%。
借鑒已有研究,采用區位熵、專業化指數及多樣化指數對山東省各地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進行衡量,結果如表1 所示。

表1 2009 年和2019 年山東省各地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數
從區位熵指數來看,2019 年濟南市、青島市、煙臺市、東營市、日照市的生產性服務業區位熵指數均大于1,說明這些城市具有較強的專業化和集聚能力,具有區域比較發展優勢。其中,濟南市、青島市、日照市的生產性服務業有著較強的集聚能力,區位熵指數均值分別為1.49、1.43 和1.31;東營市和煙臺市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力處于第二梯隊,區位熵指數均值分別為1.04 和1.02。其他地級市的區位熵指數均小于1,尤其是棗莊市、德州市、濱州市、菏澤市的區位熵指數均小于0.7,與省內其他地級市相比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力較低。
從專業化集聚模式來看,2019 年濟南市和東營市的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程度最高,專業化集聚指數均值分別為3.29 和3.74,棗莊市、德州市、濱州市、菏澤市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程度最低,專業化集聚指數分別為0.69、0.89、0.81、0.68,可見,濟南市、東營市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主要體現在少數行業時,其結構相對較為單一。而棗莊市、德州市、濱州市、菏澤市的生產性服務業各行業集聚程度均不是很強,其結構相對較為均衡。
從多樣化集聚模式來看,2019 年煙臺市的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程度最高,多樣化集聚指數達34.45,濟南市、東營市、日照市、聊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多樣化集聚程度最低,多樣化集聚指數均值分別為8.54、8.5、8.09、7.19,可見,煙臺市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表現為:在生產性服務業的各行業中較為均衡地分布,產業結構也比較多樣化。而濟南市、東營市、日照市、聊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則恰好相反,從專業化集聚指數也可以得到一致結論。
三、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的問題
第一,產業層次較低。2019 年,部分產業有了較快增勢,從投資增長來看,2019 年,郵政、交通、倉儲增長23.2%,金融服務增長20.4%,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增長32.3%,軟件、信息傳輸和信息技術服務則增長19.2%,但仍與國際國內服務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有著一定的差距,發展進程中的痛點難點仍亟待解決,2019年全省僅有3 家企業進入2019 中國互聯網百強企業名單,處于價值鏈中高端環節的產業較少,部分產業未具有核心技術、自主品牌和高端領軍人才,仍需進一步充分發揮創新引領作用。
第二,集聚效應不強。生產性服務業仍然集聚于少數幾個城市,多數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力不足。2009-2019 年多數地市的區位熵仍然低于1,區位熵大于1 的城市數量基本沒變。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力雖有提升與發展,例如區位熵保持較高的濟南市、青島市、日照市,仍具備較強的集聚能力,煙臺市的區位熵指數也突破1,有了較大發展。但總體來看,仍存在各地市提升速度相對較慢的問題,像棗莊市、德州市、濱州市、菏澤市的區位熵指數均處于0.7 以下,發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山東省需要繼續推進產業的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因地制宜,促進各城市集聚能力的提升,推動生產性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第三,輻射帶動作用不明顯。生產性服務業中心城市地位不突出,以濟南為例,區位熵指數反而下降了。在十九屆中央第一輪巡視中,濟南和青島兩市存在于提到的 “引領帶動作用不夠”的多個副省級城市中,青島和濟南在2019 年的全國百強城市中僅分別位列第14、19位,且除此之外,前三十名中僅有煙臺位列第24 位,作為中心城市帶動周圍城市的優勢并不明顯。
四、借鑒國內先進地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經驗
(一)上海
近年來,上海在推動制造業服務業集聚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效。從產業集聚的角度來看,過去我國的發展相對滯后,起步較晚。20 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上海政府大力發展服務業,不斷優化產業結構,有效強化了生產性服務業在上海的集聚和輻射功能。進入21 世紀后,上海已開始實施一系列的產業集聚發展計劃。隨著集聚區的建設發展,越來越多具有優勢的企業被吸引過來,其市場競爭能力也在不斷增強,并逐漸成為上海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上海市政府鼓勵企業間的良性競爭,以助推發展。在探索研究中,著眼國際標準,認真研究更適合上海的理念和舉措。在具體推行和實踐中,上海市政府積極積累經驗,建立集聚區模式,以期不斷推進發展和完善。目前,上海市已經建立了多個產業集聚區,發展模式主要以以產業鏈主導型模式、產業融合發展型模式、產城融合型模式三種模式為主。
(二)浙江
與全國水平相比,浙江的集聚水平較高,生產性服務業是其經濟優勢的特色產業。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制造業結構不斷優化,產業融合和集聚度顯著提升。產業規模經濟也在不斷的增強。浙江省政府也注重合理規劃促進發展的專業化程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浙江制造業布局逐漸向投資環境良好、產業結構裝備完善的地區集聚。另一方面,浙江高度重視改善產業結構和轉型,強化生產性服務業在產業結構優化中的作用,使得行業的利潤增加值明顯,產業價值在穩步增長。浙江省根據產業發展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結合浙江省產業發展的特征,提出了一種具有地域特色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戰略,形成了產業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
(三)蘇州
蘇州是江蘇省的經濟重鎮,四十余集聚區在蘇州服務業的發展中有著重要的支撐,生產性服務業在蘇州市的轉型進程中占有重要支撐地位。首先,蘇州市成立了市服務業工作領導小組,加強統籌協調。2020 年,為了進一步提高企業優勢,促進集聚創新發展,蘇州政府又制定了參照國家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實施政策獎勵和實施生產性服務業高端人才貢獻獎勵兩項重點政策以及包括謀劃滬蘇地緣合作新機制、組建一批重點領域產業聯盟等在內的十項重點工作舉措,進一步加大對生產性服務產業的集聚作用。與此同時,蘇州市立足于自身優勢,在行業保持領先地位。集約式發展是蘇州市長期以來秉承的發展理念,以“建群”模式打造產業集聚區,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相結合,以不斷改進完善制造業結構為基礎,協同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蘇州市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主要采取“點對點”或“點對群”的相融合的發展模式。
五、促進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發揮服務型政府的作用,加強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政策引導
生產性服務在制造業轉型升級和出口競爭力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山東省政府應加強政策支持,積極制定相關政策,充分發揮服務型政府作用,促進生產性服務業集聚。
首先,政府要繼續加大對企業的支持力度,完善相關稅收政策,推動產業政策向綜合性、功能性轉變。其次,政府還必須明確各部門重要職責,切實履行好自身相關職責,積極構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工作體系,科學構建規劃和計劃,積極有序組織引導,穩中有快推進集聚發展,建立公平、公開的市場環境,積極推進山東省相關產業集聚發展。
(二)提高集聚影響要素水平,提高生產性服務業的經濟效益
首先,發展山東生產性服務業,要注重信息化進程和水平提升。就是要充分利用現有信息網絡資源,完善通訊和交通基礎設施,擴大服務覆蓋面,降低交易成本。其次,加大人力資源培養力度,提升知識外溢效應。生產性服務業具有高知識密集性,根據山東省發展現狀,針對不利于人才流通和引進的政策性、體制性障礙進行修改,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的經濟效益。最后,要更加關注相關產業的關聯,山東省可以鼓勵外包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同時尊重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促進產業的升級優化。
(三)借鑒先進地區集聚發展經驗,明確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空間布局
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必須要抓住產業結構的關鍵時期,明確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緊密融合已是不可避免之勢。山東省應以三大經濟圈為主,分別構建多中心、網絡化的發展模式,重點圍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推動省會、膠東、魯南三大經濟圈的一體化發展。同時,要充分發揮鄰近城市的位置優勢,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與其他城市的交流,促進區域間的合作發展,嘗試“建群”模式下的集聚區發展,協同合作,融合發展。
當前,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山東省也應做好規劃,以促進產業機構轉變和經濟增長,打造具有山東省本土特色的生產性服務業,進而不斷提高山東省省生產性服務業市場化程度與產業集聚。
(四)積極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吸引FDI 投向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
山東省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要把重點放在擴大生產性服務業開放度和優化投資環境上。為了更好地吸引山東省的FDI,必須制訂有針對性的政策。提高生產性服務的開放程度,持續優化省內經濟發展環境,鼓勵省內中小企業加入。要加強對山東省生產性服務產業結構的優化,提高其整體價值鏈水平。同時注重擴大生產性服務業FDI 引資的數量與質量,使得山東省生產性服務業積極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山東省濟寧市老年大學之歌